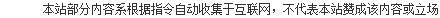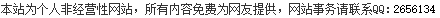致远期货:三七原则和二八原则 英文有什么区别
 点击联系发帖人
点击联系发帖人 时间:2018-01-11 23:08
时间:2018-01-11 23:08
微博热议: 快讯:
现货市场行情
渤海商品交易所
内盘期市行情
上海期货交易所
大连商品交易所
郑州商品交易所
渤海现货交易所
交易所平台
上海期货交易所
郑州商品交易所
大连商品交易所
金融期货交易所
渤海商品交易所
数据合作电话:010-
意见反馈:datainfo@staff.hexun.com
文山三七 (CM0004)
9:00-11:30、13:30-16:00
最低交易保证金
本合同总货款的20%
交易手续费
上市交易所 渤海商品交易所 交割日期
三七,又名三七参、田七、土三七,古时亦称昭参、血参、三七参等,属五加科人参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是中国特有的名贵中药...
影响因素 &
qinyour888 : 菜粕走势偏弱,建议空单继续持有,止损2300 phonex8sx2re : 预计短期市场震荡偏强运行,可轻仓试多。【三七法则】
我的图书馆
【三七法则】
【三七法则】
&&&&&&&&七画是‘男’,三画是‘女’,七加三才是十全十美;男人聊天,七分谈理想,三分谈女人;女人则七分谈男人,三分谈理想。于是,男人征服世界赢得女人;女人征服男人赢得世界。男人的誓言,七分是假,三分是真。于是,男人不坏,女人不爱。
TA的推荐TA的最新馆藏[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
喜欢该文的人也喜欢佛教后设伦理学初探——从实然的现象与法则,到应然的原理与原则
查看: 1874|
评论: 0|原作者: 昭慧法师|来自:
摘要: 佛教后设伦理学初探——从实然的现象与法则,到应然的原理与原则释昭慧玄奘大学宗教学系所副教授兼应用伦理研究中心主任摘要:本文探索佛教系统理论的后设伦理学(metaethics),以佛法之伦理判断与道德原则本身为研...
佛教后设学初探——从实然的与法则,到应然的原理与原则释昭慧玄奘大学宗教学系所副教授兼应用研究中心主任摘要:本文探索佛教系统理论的后设伦理学(metaethics),以佛法之伦理判断与原则本身为研究对象,探究语词或道德语句是否能予以定义,并追问其道德判断的客观真理。依休谟法则(Hume’s law),实然命题不必然能推出应然命题,事实判断不等同于价值判断。一般于此均须预设自明真理(self-evident truth)或第一因(first principle),但佛法却依于“实然”之与法则,藉诸经验检证与理性分析,而直接推出“应然”之原理与原则。某种程度而言,佛法倾向于“自然主义”(naturalism),直接由自然性质或具经验意义的语词,来定义伦理语词。亦即:依现象以归纳出“”与“我爱”的实然法则,依“”与“我爱”复可证成“护生”之应然律令。“应”与“不应”的道德论述,恰恰是由之欲求(而非上帝之欲求)出发,以定义并简别“善、恶、对、错”之伦理语词与价值判断。准此“护生”原则,以满足“快乐”或“效益”之欲求,作为伦理实践之目标的佛法,就带有强烈的目的论(teleological theory)气息。人必须依于“自通之法”的心理能力,以自他互替原则来平等照顾其他生命“快乐”或“效益”的需求,就此而言,佛法也同样有着浓厚的义务论(deontological theory)倾向。依此系统理论之脉络,本文提出“实然如何证成应然”的四个问题,并一一作根源性的哲学分析以解明之。关键字:后设伦理学、自然主义、非自然主义、超自然主义、缘起、我爱、护生、自通之法、义务论、目的论Preliminary Systematic Theorization of Buddhist EthicsShih, Chao-HweiAssociate Professor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Religion andDirector of Research Center for Applied Ethics, Hsuan Chuang UniversityABSTRACT: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metaethics of Buddhist systematic theorization. First, can moral words and moral sentences be defined through Buddhist ethical judgment and moral principles? Second, what is the objective reality of Buddhist moral judgment?By Hume's law, an "is" proposition does not necessarily imply an "ought" i.e., fact judgment differs from value judgment. Generally speaking, we need to suppose a self-evident truth or a first principle. Yet, in Buddhism, we directly derive the "ought" principle from the "is" phenomenon by experience verification and reason analysis. In some sense, Buddhism is inclined to naturalism, which directly defines an ethical word by inpidual nature or an experience-meaningful word. Thus, Buddhism induces the "is" principle of pratitya-samutpada and self-love by phenomenon. From pratitya-samutpada and self-love, Buddhism proves the "ought" principle of life-protection. The moral argument of "ought" or "ought not" originates from the desire of life, not the desire of God. This defines and distinguishes the ethical words and value judgments of good, evil, right and wrong.The ethical and practical goal of the Buddhist life-protection principle is to satisfy the desire of sentient beings' happiness or utility. Therefore, Buddhism is strongly inclined to teleology. On the other hand, empathy must be given equally towards all sentient beings, and their need for happiness and utility. In this sense, Buddhism is also strongly inclined towards deontology.From the thread of the above systematic theorization, this article asks four questions about how the "is" proposition proves the "ought" proposition. Throughout the discussion, each question is philosophically analyzed in a radical manner.↑backKeywords: Metaethics, naturalism, non-naturalism, Supernationalism, pratitya-samupada, self-love, life-protection, empathy, deontological theory, teleologicaltheory一、前言科学家探究出核分裂可产生巨大能量的“实然”法则,依此发现而制造了核子武器或核能发电设备。科学家探究出体细胞核转殖乃至异种基因转殖的原理与技术,依此而复制出了动物,也培植出了转基因动、植物。但这些原理的证明,技术的操作,乃至依此诸原理以操作技术所获得的效应,即使在“实然”层面可资经验检证,并依理性之归纳、演绎、分析、综合等能力,而发现其中明确的因果关系,也无法据此诸“实然”现象及其原理,而直接导引出“应不应该发展核武或核电”、“应不应该复制生命”、“应不应该对动、植物施以基因改造”等等“应然”的答案。由于“实然”的探究,只过问事相的“真”与“假”,而不过问行为的“对”与“错”,因此,科学研发与科技政策,若要作“应然”的反思,常须借助伦理学的方法,而不能依本身的科学研究方法来达成此一目的。但许多科学界人士往往会粗糙地声称其为“价值中立”,藉以回避伦理争议。实则人心从来就不是一张白纸,在生命成长与社会化的过程之中,早已薰染了复杂而多样的价值观。即使是科学家,在其成长的岁月中,经由个性倾向、家庭因素、学校教育、社会影响等复杂而多面向的薰陶,早已形塑了伦理认知与伦理情感。因此,科学家还是自觉或不自觉地隐藏着某些价值判断,只是许多科学家却将一切研究都单纯化约为“真假命题”,伪装“价值中立”,好能达成不受伦理约束的效果。他们隐藏了一些什么样的价值判断?在此可例举三点:一、竞胜的价值观:将自己、学术单位、企业团体或国家的科研成就,当作最优位价值或唯一价值。我们常发现许多力图打破伦理禁忌,而作基因改造或复制工程的科学家,根本不讳言:他们在意的是哪个人、哪个研究团队或哪个国家,能优先获取研究成果。这就是“竞胜”的价值观,此中有时更隐藏着庞大而复杂的商业利益。这岂不就是“利己主义”(egoism)或各种本位主义的目的论(teleological theory)?二、阶级、性别、种族或物种歧视的价值观:阶级、性别、种族或物种歧视,会使人自动过滤那些受歧视的对象,将其排除于道德关怀的对象之外。即使将科学成就的效益,作极大化的发挥,考量的已是“人类利益”,但依然可能为了照顾人类的共同利益,而牺牲非人类之动物的利益,如此则将隐藏物种歧视,亦即“人类沙文主义”(Anthropocentrism)的价值观。三、满足情感的价值观:即使将效益考量极小化,把科学研究视作纯属自己探索学问的兴趣,这也依然隐藏着「以满足自己的兴趣倾向为优先”之价值观,这当然还是会被归纳为“利己主义”(egoism)。科学界每在宣告“价值中立”的同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这类隐藏性的价值观推到极致,坚持作一些伦理争议极大的研究与实验,这导致人们忧心忡忡,因为人们实在无法预知:这种“只顾获得实质效果,却不过问其是否应为”的研究态度,将给人类乃至生物界,带来何等巨大的冲击、损害与灾难。因此伦理学界、宗教界、法学界、社运界(乃至科学界内部)的良心人士,往往不得不站出来,适度扮演“踩煞车”的角色。相对于科学之为“实然”之学,伦理学(Ethics),恰恰是一门探索“应然”之学。哲学进路的伦理学,可大分为规范伦理学(normative ethics)与后设伦理学(metaethics)。规范伦理学与后设伦理学,犹如语言与文法的关系。一、规范伦理学:探究有关行为规范的基本原理与各种原则,以及日常生活面临道德问题的伦理判断。这门学问,研究行为之“对”与“错”,或德行之“善”与“恶”。规范伦理学所要讨论的是伦理行为之“应然”法则,但它不是要告诉我们“该怎么做”,而是在各种思想体系之中,探究“该怎么做”的原因何在。它不等同于直接告诉我们“应该遵守哪些规范”的戒律学或法律学,而是探索戒律或法律之原理的法哲学。具体的道德判断(如:张三不应杀害李四)与抽象的道德原则(如:不得杀人),共同构成了“道德语句”。规范伦理学,就是在“应然伦理”的意义下,建构并证成道德语句之体系的学问。当代分析哲学(contemporary analytic philosophy)有系统探讨“什么”心态或行为合乎道德或不合乎道德?其理由何在?是否充分的道德理由?这类研究道德原则之学,称为“规范伦理学”。[2]规范伦理学又可概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基础伦理学(fundamental ethics),探讨规范伦理学的基本理论(foundational theories),包含一套完整的,而且对所有人都有效的道德原则,用以判定行为的对错。第二类是“应用伦理学”(applied ethics),将基础伦理学所探讨的道德原则,运用在人生的不同实践领域中,以厘清并解决实际生活中所面临的具体道德问题。二、后设伦理学:或称“元伦理学”,以伦理判断与道德原则本身为研究对象,针对道德语词(如“善”)以及由道德语词所形成的道德语句(如“助人是善”),进行意义的分析、特质的探索,是为“后设伦理学”。后设伦理学所关心的不是道德语词或道德语句的建构与证成,而是道德语词或道德语句是否能予以定义,并追问其道德判断究属主观见解(或情感)抑或有客观真理。换言之,道德语词所表述的道德性质是实在而可被认知的?抑或并非实在,亦不可被认知?后设伦理学是当代分析哲学兴起之后才有的发展。传统的规范伦理学已预设了道德真理的客观价值,因此,传统规范伦理学家探究的不是道德原则有没有客观基础或充分理由,而是探究支持道德原则的客观基础或充分理由是什么。也因此,传统规范伦理学家往往对于其所预设的“客观价值”(如:上帝、良知、灵魂、善)全然不作质疑,从而倾向于“客观主义”(objectivism),忽略了道德真理的主观意义。难免有些规范伦理学家,视此类研究为挑战道德真理、动摇信仰与信念的麻烦制造者。然而后设伦理学并非全盘推翻道德原理与原则的客观基础,而是要更严谨地证成,道德原理与原则是否真有客观基础?如或有之,又是怎样的客观基础?它的作用在于将更深层、更根源性的基础理论,提供给规范伦理学,这也是它被称为“后设”的原因。是以Nielsen主张,后设伦理学的问题倘不清楚,根本不可能进行规范伦理学的讨论。[3]笔者曾着《佛教规范伦理学》乙书,以论述佛教的“规范伦理学”为主,亦即探索佛教伦理学之道德原理与原则,建立佛教戒律的法哲学与法理学。该书间亦视需要而就道德语词(如:良知)或道德语句(如:是否要依如来藏为道德原理),来作根源性的分析,本文之中,笔者则拟进一步探索佛教系统理论的后设伦理学。二、自然主义、非自然主义与超自然主义依逻辑实证论(logical positivism),任何严格的真理陈述,只有两种情况:不是可透过感觉经验来加以检测,就是可经由理性分析而加以定义。当然,我们也可以抬杠地说,即使是“有而且唯有感觉经验与理性分析这两种陈述,可用以判断事实的真与假”这样的一个命题,也未必可以透过经验检测与理性分析,来证明此一命题必为真理陈述,或证明确已没有第三种真理陈述的可能。如果不能得此证明,又如何能推翻“出现其他真理陈述的可能性”?但是无论如何,真理陈述的如上定义,使得伦理学家注意及“实然”与“应然”之间的对应问题。例如:“善、恶”或“对、错”这样的伦理语词,是可以被经验检测或理性分析的吗?后设伦理学(metaethics,或译“元伦理学”)有两大派,一派是自然主义(naturalism),主张伦理语词和道德信仰,可以由自然性质(natural properties)或具经验意义的语词来加以定义;另一派是非自然主义(non-naturalism),否认伦理语词可用经验检测与理性分析以定义之。非自然主义可溯自十八世纪哲学家休谟(David Hume)。他指出:我们无法从“实然”(is)演绎出“应然”(ought),是为休谟法则(Hume’s law)。[4]二十世纪的英国思想家莫尔(G. E. Moor)与洛斯(W. D. Ross),也宣称“善”是不可被定义的,并提出“直觉主义”(intuitionism),认为存在有客观的道德真理,而基本的道德真理,对成熟的心灵而言,乃是自明的。[5]依休谟法则,实然命题不必然能推出应然命题,事实判断不等同于价值判断。因此,依于“实然”之现象与法则,又当如何推出“应然”之原理?反之,若不依“实然”之现象与法则,“应然”的道德规范,又将据何基础以建立之?另有一种超自然主义(supernationalism),例如:一神论者或中国古代的墨家,莫不依“天启”或“天志”,来证成人所应克遵的道德规范。超自然主义将道德判断视为一种宗教陈述:“X是善的,因为上帝欲求X”。然而这将面对的是“上帝”与“善”之定义的循环论证。[6]此一“应然”法则,有其预设的自明真理(self-evident truth),是即上帝在“实然”层面必然存在,其欲求必然为善。从而“应然”的“天启”或“天志”,就有其不容置疑的权威性,而且人有义务奉行上帝的欲求。因此这类天启的规范,经常出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命令句。这种预设自明真理的“应然”之学,有其在实践层面的重大意义。康德(Immanuel Kant,)在“第一批判”中,检视了一些证明上帝存在的论证,指出传统以“存有论证”,以及建基于其上的“宇宙论证”的谬误。[7]他指出:像上帝存在、自由与灵魂不朽等,皆非现象界的事物,而已经超出了人类理性分析与经验检证的范围,故吾人固不能以理性证明上帝存在,也不能证明其不存在。而在“第二批判”中,康德则进一步主张:我们的纯粹理性虽不能证明上帝的存在,但人对上帝的信仰,却可在“实践理性”[8]中获得实践,人以理性意欲实践善行,便自然地要求上帝的存在。他把这些信仰称为“(道德)实践的设准”,亦即一个无法证明的假设,但为了实践的缘故,该假设必须成立。[9]特别是基督宗教,对人性的软弱(姑名之为“罪”)体会甚深,因此认为,人必须遵奉上帝的欲求,而不可聆听自己的声音。因为上帝之欲求必善,而人之欲求则不必然是善。而且即使人的伦理认知已能简别善恶,但人的道德情感,还未必能好善厌恶,人的道德意志,也未必就能舍善去恶。这就是保罗〈致罗马人书〉所说的:“我有行善的愿望,却没有行善的能力。我所愿意的善,我偏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而去做。”(〈罗马书〉7:17~18)因此超自然主义难免会质疑无神论者:若不能全心全意地将自己交给上帝,坚定地奉行上帝的意旨,人如何可能抗拒自己的罪性,来奉行道德律令?(或更简单地说:不信奉上帝的人,如何能不混淆道德?)如此理解,吾人较不会预存偏见,迳将基督宗教简化为“排他性宗教”,而能以同理心体会:何以基督宗教之“应然”规范,会将“信奉上帝”列为十诫之首要条目?因为在此系统理论之中,上帝已是其他一切诫命或规范的基本原理,不能信奉上帝,即不足以产生奉行其余诫命或规范的强烈动机。而且超自然主义也未必会走向“排他主义”,至今已有更为丰富而多元的神学诠释,例如:“包容主义”业已出现于主流教派的神学论述之中。预设存有实体之“天”或“天道”,则“天启”、“天志”之道德规范,就有不可违越的权威性,这样的神学进路,顺利架构了“由实然而应然”的内在逻辑。但其困难则在于:一、如何运用理性分析与普遍性经验,来证成超自然之存有实体?这部分,经由西方哲学家与神学家的反覆讨论,虽已有了极其丰富的成果,只是迄未获得一个诸方满意的共识。二、若超自然之存有实体,不能依循理性分析与普遍性经验的路径以体认之,只能仰仗特殊的冥契经验,又当如何令不信者启信?三、对未信者而言,既已无法确信上帝之存在必为“实然”,又如何能服膺由天启或天志所宣告的“应然”规范?四、对已信者而言,如何避免陷于将未信者视为“对道德混淆不清的人”[10],从而产生“自以为义”的道德傲慢,卒至重新陷溺在自己原应跳脱的“罪性”之中?依于本文所作的根源性分析,显示佛教伦理学并未预设道德真理为“不可定义也无法证成的自明真理”,因此不属于“非自然主义”。当然,作为“无神论”的佛教伦理学,不会建立第一因之存有实体(如上帝)以为自明真理,因此也不属于超自然主义。某种程度而言,佛法反倒倾向于“自然主义”(naturalism),直接由自然性质或具经验意义的语词──“缘起”与“我爱”,来定义伦理语词──“护生”,并据“缘起”与“我爱”之实然法则,以证成“护生”心行之合理性与必然性。亦即:依现象以归纳出“缘起”与“我爱”的实然法则,依“缘起”与“我爱”复可证成“护生”之应然律令。三、佛教伦理学之后设性议题乍看之下,或许吾人会以为,这样便毋庸面对证明第一因之真实性与权威性的质疑。然而吾人同样必须审慎面对以下四个由实然而应然的问题:一、首先要问的是,“缘起”是佛陀在深彻的直观(现量证境)中,所获证的答案;但现量证境同样并非普遍性经验,佛陀是如何将这种“唯证方知”的非普遍性冥契经验,转化为一种透过理性分析与经验检测,可辨明其真假值的“实然”之学?或扩大范围而言,面对世间一切“实然”现象,佛法当如何让人用理性思辩与普遍性经验,来理解彼诸现象之所以如此或如彼呈现的“实然”法则?如能证成此点,则佛法不须预设无法证成的自明真理或第一因(first principle),因此也不须面对“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问题。二、如前所述,“实然”之现象与法则,不必然就能据以推出“应然”的道德命题。依佛法之理论以观,因缘条件之聚散,导致现象生灭、成毁,这套“实然”的缘起法则,似乎并不能告诉我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也似乎不能告诉我们,在不可得兼的情况之下,应该孰先孰后。举例而言,病毒感染,再加上未能适当隔离、防护等等诸多因素,导致疫病大流行。发生芮氏七级大地震,加上房屋的防震系数不够,人们在仓促间来不及出外避祸等等诸多因素,导致大量屋毁人亡。像这些现象,可用“缘起”法则来加以理解;但它似乎不能直接明白地告诉我们:面对这两件事,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应做诸事之中,又应孰先孰后?因此,其次要在本文之中解明的就是:即使真能透过理性分析与普遍性经验,令人理解“缘生”之现象与“缘起”之法则,又当如何据以建立“护生”的应然原理?三、复于“实然”层面观察众生,佛法同样见到人性的软弱,但较少名之为“罪”,大都用理性错乱之“无明”、情、意偏差之“爱、取”以名之,或称此诸罪性为烦恼(缠、结、使等),此诸罪行为恶业。顾名思义,显见这些都被视作生命负面价值的展现,其原因安在?正、负价值复依何种判准以简别之?四、依佛法以看待生命,有那些实然的身心状况,可以具足正面价值,乃至可以扭转无明与爱取?或是必须采取基督宗教的方式,为生命的出路而在身心实况之外,另寻“救赎”的源头?总之,在“实然”层面,究依何等道德真理之基础,以提示其“应然”之道,而且确保此“应然”之道,可以扭转该诸“实然”的心理现况?进以言之,面对根深蒂固、如影随形的“罪性”,基督宗教已在“实然”层面,预设了上帝以为自明真理,因此其“应然”之道的内在逻辑非常清楚:在自利方面,依于上帝的恩典以获得自我的“救赎”;在利他方面,回应上帝之爱,而爱及同依天主肖像而受造的“邻人”乃至“敌人”。那么,依佛法以看待根深蒂固、如影随形的无明与爱、取,在“实然”层面又当以什么作为基础,其“应然”的内在逻辑又是什么?亦即:在自利方面,人们依于何种力量来获取效益或获证解脱?在利他方面,“护生”为本的种种规范,又要靠何种力量,方能抗拒无明与爱、取,而获得实践的保证?第四个问题,凡已涉及工夫论的部分,笔者将另文处理,本文但依佛法之系统理论,将这四个“实然如何证成应然”的问题,作根源性的哲学分析。四、缘起:“实然”之现象与法则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面对世间一切现象(诸有为法),佛陀依智慧洞观其缘生缘灭,而悟证“缘起”(梵pratītya-samutpāda;巴paticca-samuppāda)法则。这种现量证境,唯证方知,因此说是“缘起甚深”,这可依于两个面向来解明其“甚深”义:“此甚深处,所谓缘起;倍复甚深难见,所谓一切取离、爱尽、无欲、寂灭、涅盘。如此二法,谓有为、无为。有为者,若生、若住、若异、若灭;无为者,不生、不住、不异、不灭。”[11]为,即是造作。有为(梵 samskrta)法,即生灭变迁的一切现象。要在现象中洞观其均为因缘条件组合或制约下的存在,而不复产生“非有即无、非常即断、非一即异、非动即静”的错觉(离此二边),已经极不容易,复须洞观其“非自生、非他生、非共生、非无因生”,[12]是则倍复艰难。乍看之下,“共生”与“缘生”似乎区别不大,实则不然。原来缘起并不单纯是a1+a2+ a3……=A这么单纯的演算。任一A固然是因缘和合而无终极自性的,任一a1或a2或a3,又何尝不是因缘的产物?倘若将a1剖析下去,它是来自b1+b2+b3……的组合;b1又是来自c1+c2+c3……。这样无穷尽地分析下去,哪有终极实在的质素可得?此所以缘生又被龙树称为“无生”或是“(自)性空”,亦即,只见诸因缘条件之聚散离合,却不见有永恒、独立的终极实在(自性)可得。此理艰深,故曰“甚深”。无为(梵 asamskrta)法,原指涅盘证境的“择灭无为”(即前引经文中所说的“一切取离、爱尽、无欲、寂灭、涅盘”),以及缘阙不生的“非择灭无为”,后又加入以无碍为性,容受万物而遍满一切处的“虚空无为”。这三者都有不生灭、无变迁的特质,故名“无为”。在部派佛教的开展中,大众、分别说部也将实然现象的原理、法则名之为“无为”。原来现象虽然生灭变迁,但其生灭变迁的法则,却有必然性、恒常性与普遍性(故名“法性、法住、法界”);显然也符合无为法“不生灭、无变迁”的定义。这种“唯证方知”的甚深悟境,佛陀是如何让人用理性分析与普遍性经验,来理解彼诸现象之所以如此或如彼呈现的“实然”法则?这可参看《杂阿含经》中,阿难为迦旃延所做的“缘起”论述:“如来离于二边,说于中道。所谓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谓缘无明有行,乃至生、老、病、死、忧、悲、恼苦集。所谓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谓无明灭则行灭,乃至生、老、病、死、忧、悲、恼苦灭。”[13]佛法的“缘起”论,简单而言,即是“此故彼”的法则──是“此”诸因缘展转呈现“彼”诸果法的法则。它虽是佛陀在深邃的直观之中所体悟的法则,但当佛陀“由证出教”之时,却完全诉诸生命苦感的普遍性经验,与离于二边的理性分析,而不诉诸神格的权威。“缘起”是有为诸法生灭变迁的因果律,这与科学在研究与发明的过程中所遵循的因果律[14],或哲学依理性而证成的因果律[15],内容虽不完全相同,但同样未诉诸信仰与想像,因此较无“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之难题。五、依“缘起”之实然,证成“苦灭”之应然即使透过常识经验与理性分析,而证明了“缘起”为森罗万象生灭变迁的“实然”法则,吾人又当如何依“缘起”之实然,以推出其伦理规范之“应然”?作为行为主体的“人”,如何在此一自然法则下,获得伦理方面的启示?亦即:如何由万法“实然”之理,以证成人所“应然”之事?这就进入了前述第二个问题,而有待作进一步的分析。林益仁教授曾向笔者询问道:“最近正好在看英国一位学者的文章,他也在研究佛教和环保运动的关系,他提到缘起法,他觉得缘起法最后并没有告诉我们一个目的性,没有指出一个终极目的在那里,因为物物相关,各个现象彼此有相关联性;但彼此相关,并不表示一定朝某一方向走。所以他的结论是:缘起法好像很难推出‘现在我们一定要去救犀牛或是一定要去救流浪狗’的结论!”[16]事实上,“要救谁”,这已是第二序的问题,此中已预设了第一序的“应该救”之前提。吾人甚至可以进一步质疑这样的前提:缘起法又如何证明吾人“应该救”他者?特别是,因缘生灭的现象界,众生依于心理利己之自然倾向,大都循着弱肉强食、物竞天择的法则,挣扎存灭于其间,俗谚声称:“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正是说明了此一法则下“利己”的正当性。难道强调经验检证的佛教伦理学,可以依此实然现象,以叙述一套“只应利己,不应利他”的应然哲学吗?然而无论是重在自利的声闻佛教,还是强调利他的大乘佛教,无不谆谆劝告世人,应该勤于“护生”。亦即:在消极方面不伤害众生,在积极方面让众生离苦得乐。可见得佛教伦理学,确实有“利益众生”的重要面向。进以言之,“利益众生”若是应然之道德要求,又将如何从缘生现象与缘起法则,而给予合理的推论?于此可以注意:“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这原是一切现象生灭变化的通则,生物、非生物、动物、植物都不例外。阿难却在紧接着的说明之中,将关怀范围缩小为有情,阐述以胎生众生为例的十二缘起。显见佛陀所洞烛之实然法则,虽有普遍性与恒常性,但佛陀所关切的对象,却以生命为主。因此佛法特别针对有情,依其承受种种诸苦的现状而作分析,叙述其依于缘起法则,所面对的“苦集”(流转生死且如环无端的十二缘起)与所可获证的“苦灭”(灭除烦恼,证得解脱,亦即涅盘寂静)。[17]易言之,“应然”的苦灭之道,即奠基于此一苦集的生命实况之上。原来,无生物并无生命现象,植物虽有生机,却不如动物之有意识与感情(故名“有情”,梵sattva),不似动物有苦乐的感知能力,所以佛法关切的重心,仍是以动物为主的“有情”。由“实然”而“应然”,依有情在生理、心理与心灵层面的实际需要,而提出让生命得遂所求以“离苦得乐”的种种方法──或浅或深的“苦灭”之道。六、依惑、业、苦流转之实然,证成“离苦得乐”之应然至此,也就可以进一步回答前述第三个问题:理性错乱之“无明”、情、意偏差之“爱、取”,乃至烦恼(又名惑、缠、结、使等)与恶业,确乎被视作生命负面价值的展现,其原因是,顺着这些负面的生命欲求来发展,会带来自己生命与其他生命的无穷痛苦。而且这烦恼(惑)、业、苦的层层相生,是循环不已,流转无穷的。这种生命现况,并不符合生命“离苦得乐”的欲求。原来,在认知方面,昧于“缘起”法则的众生,无法体悟得:因缘生灭的现象之中,无有常恒、独立、真实不虚且可自由主宰之“我”可得;反而本能地错觉有一“自我”,并以此一“自我”为中心以估量一切,从而产生无可避免的认知错乱。此一根深蒂固的认知错乱,名为“无明”(梵avidyā)。在情感方面,昧于“缘起”法则的众生,对于自身的处境,必然因自我中心的“无明”,而产生强大的关切之情,是为“我爱”。无明与我爱发为意欲,于是产生了强大而本能的生之意志,以及种种得遂生命欲求的“取”或“业”。昧于“缘起”的众生,知、情、意三方面都围绕着「自我”而转,于是产生了一种内聚力,使生命本能地牢牢执取“自我”,聚集任何对“自我”有益的质素,排除任何对“自我”有害的因缘。强大的无明与爱、取,使得众生总是下意识地抓住一个模糊的中心,不断地从这蒙昧的中心,产生自我意识的漩涡,将具体事物内聚性地卷入意识漩涡之中,名之为“我所”(我所属或我所有的一切),来作为“我”的表现或“我”的扩大。源自“我爱”所扩展的“我所”之爱,乍看之下亦能产生“利他”之行,其实还是源自“利己”心理的辐射。[18]既然利己心态在众生界,已属牢不可破的本能,那么,以此看待伦理利己主义,人们在伦理行为中,会理所当然地寻求“自保”,或是扩大地追求自己或“我所”的利益,这也是人情之常。至于这个利益,究竟是五欲享乐、权力、名声、长寿,还是生命的终极出路?当然随各人的价值观而不等。问题是,这种顽强而本能的无明与爱、取,可以进一步发展成为伤己、伤人的双面利刃。在伤己的方面,它让个人为了自我满足而执着于自体与境界,却因无法掌握自体与境界的一切因缘变化,从而饱受它们无常败坏,不符自己之所期待的种种痛苦。在伤人的方面,无明与爱、取,还可能会为了自我满足,从而妨碍甚至剥夺他者自我满足之欲求,从而减损他者之快乐与舒适,甚至导致他者之种种痛苦。亦即:生命与生命之间,可能会因彼此都有无明与爱、取,而形成互相的妨碍与伤害。这不但伤人,而且其反作力又会伤及自己。因为他者同样具足无明与爱、取,一旦受到了自己的妨碍与伤害,可能会对自己因怨憎而报复,从而减损自己之快乐与舒适,甚至导致自己的痛苦与死亡。进以言之,苦集与苦灭有其“此故彼”的实然法则,然而佛法又何以认定孰应孰不应?何以认定生命应该依循“苦灭”之道,而非“苦集”之途?这是因为,依“缘起”法则而流转世间的生命,都有以自我为中心之欲求(我爱),由是而产生强烈的趋生畏死,趋乐避苦之本能。[19]这是每个有情经由常识经验即可自我检证的“实然”,而“应”与“不应”的道德论述,恰恰由此生命之欲求(而非上帝之欲求)出发。凡消极不伤害或积极满足其他生命“趋生畏死,趋乐避苦”之欲求的动机为“善”,业行为“对”;凡抵触其他生命“趋生畏死,趋乐避苦”之欲求的动机为“恶”,业行为“错”。正面价值或负面价值,即依此以为判准。准此“护生”原则,以满足生命“快乐”或“效益”之欲求,作为伦理实践之目标的佛法,就带有强烈的目的论(teleological theory)气息。但人不应该只顾追求自己生命的“快乐”或“效益”,而且必须依于“自通之法”的心理能力,以自他互替原则来平等照顾其他生命“快乐”或“效益”的需求,就此而言,佛法也同样有着浓厚的义务论(deontological theory)倾向,此点将于下节详之。七、依三种原理之实然,证成“护生”之应然如前所述,孰为正面价值?孰为负面价值?端看它带来的是满足生命欲求的快乐,还是斫伤生命欲求的痛苦。价值判断不建构在某种预设的自明真理之基础上,而直接建立在“苦乐”之分辨的普遍性经验之基础上;伦理动机之“善”与“恶”,伦理行为之“对”与“错”,也同样依其是否可满足“离苦得乐”的生命欲求,来加以检证。接着要提出第四个问题:依佛法以看待生命,有那些实然的身心状况,可以具足正面价值,乃至可以扭转无明与爱取?或是必须采取基督宗教的方式,了然于身心实况深彻的罪性,而在身心实况之外另辟蹊径,为生命另寻“救赎”的出路?总之,在“实然”层面,究依何等道德真理之基础,以提示其“应然”之道,而且确保此“应然”之道,足以扭转该诸“实然”的负面现况?如前节所述,生命实况是如此的依于无明与爱、取而自伤伤人,看似无可救药。佛陀不可能反向操作,违逆生命欲求之本能,而教人以“苦集”(自讨苦吃)之道,但他却未另寻生命本身以外的权威性救赎力量,而是因势利导,顺应生命的欲求,而告诉吾人“苦灭”之道──教人消极方面避免伤己伤人,积极方面让自己与他人的生命,都获得快乐与舒适,是为“护生”。以“护生”作为应然规范的总纲,其理据并不建立在预设的自明真理(上帝的欲求)之中,而直接诉诸经验检证(生命的欲求)。因此“护生”之为伦理语词,也是可依经验检测或理性分析来作定义与阐述的。以下即本诸前述“缘起”法则与“我爱”实况,依“自通之法”等三项可以诉诸经验检测与理性分析的“实然”原理,据以推论:“护生”是一切“应然”规范的总纲。[20](一)自通之法从原始的《阿含经》到大乘经典,处处说明护生的道德基础——“自通之法”,如《杂阿含经》说:何等自通之法?谓圣弟子作如是学:我作是念:“若有欲杀我者,我不喜;我若所不喜,他亦如是,云何杀彼?”作是觉已,受不杀生,不乐杀生。如上说,……”[21]又如《法句经》“刀杖品”(Dandavaggo)说:一切惧刀杖,一切皆畏死,以自度[他情],莫杀教他杀。一切惧刀杖,一切皆爱生,以自度[他情],莫杀教他杀。[22]这就是“自通之法”:用自己的心情,揣度其他众生的心情,而珍重他趋生畏死,趋乐避苦的天性。在这方面,佛法有着浓厚的义务论倾向。道德律不必假诸其外、其上的天启或天志,而就在每个人的心中。一个具足“自通之法”的人,会自发性地奉行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的七种圣戒(一般将后四种恶语业之戒合并为一“不妄语戒”,而成五戒)。如前引《阿含经》所述,持七圣戒(五根本戒)的利他善行,其结果虽然使得自己也获得人天乐果之酬偿,但原初持戒的动机,却不宜来自“利己”的考量,而要出于自他互替、同情共感的“自通之法”。若时时依“自通之法”以行事,那么,即使自己向往世间福乐的目标并未改变,也能在过程之中,因时常自他互替,同情共感,而产生强大的利他动机,并逐渐养成“利他”的道德习惯。如此奉持净戒,进而净信三宝,那么待到预入圣流,证悟解脱之后,必当恍然大悟“自我”的虚幻无稽。“自通之法”极类似儒者所说的“良知”,在伦理学上名之为“黄金律定理”(Golden Rule Thoerem)。当代伦理学家Gensler依康德(Immanuel Kant)的黄金律,作了进一步的细腻辩证与小幅修改,以排除诸如被虐狂之类在字面意义下之黄金律所导致的悖谬[23],然后为黄金律下了两个精准的定义:一、“只依在相同处境下你同意被对待的方式来对待别人”;二、倘若“我对另一人作出了某件事,而在相同处境下,我不愿意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那么,此人显然对己对人有不一致的行为标准,因而违反了黄金律。[24]这是不同文化所共同遵奉的黄金律,但基督宗教与康德,并未将动物纳入黄金律所涵盖的对象;基督宗教是基于“神性”的原因,康德则是基于“理性”的理由。不具足神性或理性的动物,未能被人类纳入作为“一致性”的道德考量。但是佛教却明显地将动物纳入作为“自通之法”的对象,其理由在于,动物与人同样具有“不喜被杀”等等的喜怒哀乐的情绪与痛苦的觉受能力。既然如此,则“自通之法”显然无法排除对动物处境的同情共感。是故黄金律所涵盖的对象,应以“感知能力”作为判准,同情共感的关怀面,应不只及于人类,而必然会扩大到所有有情(包括动物)的身上。在这方面的伦理判准,动物解放哲学家Peter Singer与伦理学家Gensler的看法,与佛教是较为一致的。[25]佛所说的“端正法”:布施、持戒、禅定,都是让修学者自身得受人天福乐的方法。其中两项“利己”之道——持戒与布施,前者是是消极的不害于他,后者则是积极的施与快乐。此两者要从“利己”而转向“利他”,关键即在于“自通之法”:持戒与布施,在此已不是为了自己的更高利益,而是出自对他人之处境的同情共感。所以在消极方面,克制自己,避免因自己行为不当,而置他人于痛苦境地;在积极方面,则分享资源,以财物、体力、言语等各种布施,改变他人的境遇,使其离苦得乐。即使是圣者的菩萨心行──“无缘大慈”与“同体大悲”,其初也莫不以“自通之法”作为基础。准此以观:“我爱”原是对“自我处境”的强烈关怀。如前所述,它是一把伤己、伤人的双面利刃,可以掉入自我中心的深渊,起惑、造业、感苦,造成自误、误人的后果。反过来说,它也吊诡地形成一把利己、利人的双面利刃── 一方面,它本能地在任何时刻,寻求自己快乐、舒适、趋生避死之道;另一方面,它也可以由“自我关怀”的基础而逆向操作,易地而处,对他人的“自我关怀”同情共感,从而实践利他主义。而这也显示了佛陀教学的一大特色:他依“生命的欲求”而因势利导,无论是在心理层面还是伦理层面,实然层面还是应然层面,都架设了一个从利己而达到利他的桥梁。至此,已可完整回应前述第四个问题:依佛法而言,利己与利他,都不需仰仗权威性他者的道德指示与“救赎”力量。(二)缘起法相的相关性再者,缘起论提醒吾人,任何一个有情,都是与无数因缘连结的“网络”性存在体。生命不可能独立存活,也不可能在没有适当因缘条件的支持之下,获取自我满足的快乐与舒适。因此在“应然”层面,无论是为了自我满足,还是为了感念(得以成就自我满足之愿望的)因缘,吾人都应顾念他者,而非只看到自己的需要。这是依于缘起法相依互存之“实然”法则,所可导出的“应然”意义。另外,此一实然法则,也可进以说明前述“自通之法”的本质,并进以解释,何以同具“自通之法”的人们,会在道德感情与伦理抉择方面,出现个别差异。自通之法虽是普世与共的道德黄金律,但是它的来源为何?是有客观依凭,还是纯任主观情绪?是来自外在的天启,还是来自内在的直觉?是不证自明的真理,还是要依更根源的真理以证成之?这就随诸家说法而有重大差异。依缘起论,良知是主体与客体交融互会的产物,它并非来自外在的天启,而且可以依更根源的真理“缘起”以证成之。简而言之,良知是道德主体相应于缘起事相“相依相存”且“法性平等”之法则,而对同为有情之客体,所自然流露的同情共感。而缘起法的相依共存与法性平等,此二法则,被印顺导师视为“慈悲的根本”。[26]进以言之,依“缘起”法则以观:存有的任一现象(有情包括在内),原都不是隔别孤立而可以单独存在的,须要有“众缘和合”以成就之。因此,因缘生法本身,就与其他的因缘所生法,有着「相依相存”的复杂网络。在这前提之下,因缘相互支援成就的生命体与生命体之间,如何可能不存在着隐微而畅通的管道呢?吾人的九孔七窍,与外在环境无一瞬间不在互通状态。吾人的表情、语言、行为,更与他者相互传递丰富的讯息。此所以生命虽有各别隔历的形体,但形体与形体之间,却并非“绝缘体”。前述同情共感的“自通之法”,即是本此而生。因此,对其他生命的尊重,就不只是素朴的主观好恶或情绪因素,在主体对客体同情共感的现象背后,有其“法则”存焉。生命会依互通管道的畅通程度,而出现自通之法的个别差异,这就是人人具足良知,但各人的道德自觉却又往往悬殊的缘由。当人愈是将“自我中心意识”减低,这种“互通”的管道,就愈是通畅。至亲至爱之人的互通管道,较诸常人更为畅通,有时甚至可以让人超越我爱的本能。例如:火场外的母亲,可以奋不顾身扑回火场抢救亲儿;但未必能对邻家小儿做到这一地步。圣者则因其体悟“缘起无我”,所以可不倚仗任何依“自我”为中心而辐射出“我所”之沟通管道,而对其它生命之苦乐,不问亲疏地产生毫无藩篱的感知能力,并施与毫无差别的慈悲,是名“无缘大慈”。(三)缘起法性的平等性有情在“实然”层面,均有其感知能力,因此吾人应平等考量有情这种觉知苦乐的感受,尽可能满足其离苦得乐的欲望。这是在应然层面,提倡“众生平等”的重要理由。这点,与Peter Singer的看法大同。其次,由于一切有情只是因缘条件组合下,相对稳定的存有个体,所以,在因缘条件变化时,个体的尊卑优劣之处境,也就跟着发生变化。一切阶级意识、种族认同或是性别歧视,都是执着于阶级、种族或性别之真实性,而生起的一种“常见”,也是一种“我慢”(自恃凌他心态)作怪的“自性见”,在现象差别的背后,缘起性空,诸法无我,故永恒不变、独立自存而真实不虚的现象自体,了不可得(是为性空、无我义)。易言之,“诸法缘生无自性”,在此一法则下运作生灭的,只有相对稳定的个别现象,却无永恒差别的实体可得;在差别法相的底里,这又是一个实然层面“法性平等”的理则。以此法性平等的理则,拿来观照缘起法的差别相时,“众生平等”就不再只是从其平等的感知能力,而且是从其平等的缘起法则以证成之。“同体大悲”由此萌生——拔除众生痛苦,给予众生快乐,这已不须来自任何“自他互易”的想像与判断,而是直下植基于“众生法尔平等不二,同体相关”的甚深悟境。这时,“护生”已不只是一种素朴的感情,一种互惠的思维,而形成了一种情识与情爱的升华。“护生”已不只是一种美德,而形成了有道德自觉与理性思辨能力,意欲提升“情识与情爱之层次”的“人”所应恪遵的“义务”。八、结论综上所述,佛法的缘起论,不须预设第一因或不可证成的自明真理以为前提,而可依经验检证及理性分析以理解之;即使是没有冥契经验的一般人,依然可以体悟其“实然”原理,而不须面对“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之争议。缘起论虽与科学同属(可依经验归纳以理解的)“实然”理论,但科学方法只证明“真假值”,而不能据以判断其“对、错、善、恶”,而必须另行仰仗各种伦理学的系统理论,来抉择其“应不应然”。“缘起论”则不但是一切现象因缘生灭之原理,以及生命流转生死的实相,而且可即此原理而判断其“对、错、善、恶”,并据以推演出“应然”之道──自利、利他的理由与方法,以及种种克己、护生的行为规范。易言之,依佛法的系统理论,从“实然”之缘起法则与生命欲求,即能解析“应然”的原理与方法,而不须诉诸另一套伦理学,也不须诉诸“天启”之类的自明真理。进以言之,依于缘起之“实然”法则,如何达成利己与利他的两项“应然”之道?这一部分,业已牵涉到内容丰富的工夫论,笔者将另文处理,本文只在此作一概略性陈述:一、在利己方面,顺应生命强烈利己的本能,佛陀教授以“如何利己”的“应然”之道──布施、持戒、禅定,由此而巧妙地连结了利己与利他的桥梁。二、在利他方面,由于“我爱”本能在生命界中普同存在,而生命又与诸因缘相依互存,因此生命的身心发展,或多或少有其沟通渠道,在情感上即发展为“觉知他者苦乐”的自通之法,此即是利他德行的“实然”基础。依此利他实相以建构的“应然”之道就是:人应在消极方面力求节制自己(持戒),以免伤害他者之我爱;在积极方面分享资源(布施),以让他者也能获得自我之满足。对于一个少分、多分或全分体悟缘起的人而言,无论他在名义上是不是“佛教徒”,或多或少会对相依共存的众生,产生一种直觉性的同情共感。圣者也是在这样的情感基础上,透过缘起深观而超越自我,从而将“利他”视作自己责无旁贷的“义务”,而不会自矜为一桩“美德”。最后综合前述要理,补充诠释“平等”三义。“平等”原是佛经用语,日本依此以对译英文之equality。佛法中的“平等”有三种层次:一、生命均有感知能力,应平等尊重生命的苦乐感知,以及其离苦得乐的强烈意愿,是即“众生平等”之要义。二、生命又都依因待缘而生灭变迁,是即缘生诸法在差别相中,无自性义平等无二,是为“法性平等”之要义。三、不但凡夫依因待缘而承受苦乐、流转生死,圣者也是依因待缘而证入涅盘、成就佛道。在此“缘起”法则之下,凡夫有修三学以解脱的可能性,也有修六度、四摄以成佛的可能性。后者,即“佛性平等”之要义。“我爱”的生命本能,即在自他互易的反省之中,而发挥了超越自我藩篱以“护生”的精神;复由深观“法性平等”与“佛性平等”之“无我”实相,更能将“护生”精神发挥到极致,而契合于“众生平等”的道德理想。由“实然”之体悟而实践“应然”之德目,再由“应然”之履行而印证“实然”的圣境。“实然”的体悟有多深广,“应然”的实践就有多深广;“应然”的履行有多彻底,“实然”的印证就有多彻底──这就是从“实然”到“应然”一脉相承的缘起论。──九四、五、三完稿于尊悔楼--------------------------------------------------------------------------------[1]& 本文初稿名为〈应然伦理之证成——依“缘起论”之佛法观点〉,93年11月18日初成,并发表于当年11月27日,在东吴大学所举行的台湾哲学学会年会之中。本文依该份初稿而作大幅修订与增补,完稿于94年5月3日,并于94年5月15日,于玄奘大学第一届“应用伦理会议”中作专题演讲。*& 玄奘大学宗教学研究所副教授兼应用伦理研究中心主任。[2]& Nielsen, Kai. “Problems of ethics”. In Th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vol. III, edited by Paul Edwards.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 The Free Press. 1967, p.118。[3]& Nielsen, Kai. “Problems of ethics”, p.119。[4]& Gensler, Harry J. Ethics, copyright by Routledge, 周伯恒中译,台北:韦伯文化事业出版社,1999,pp. 70~71。[5]& Gensler, Harry J. Ethics, 周伯恒中译,PP. 68~83。[6]& 有关“超自然主义”的详细辩证,参见Gensler, Harry J. Ethics, copyright by Routledge, 周伯恒中译,pp. 49~63。[7]& 康德(Immanuel Kant):《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Norman Kemp Smith英译本,页六二○~六四七;牟宗三中译本,下册页三四五~三七五。)[8]& 什么是“实践理性”?即是实践(道德)应用下的理性,“说到底,只有一个相同的理性,而问题在于要分辨此一理性之各种应用。”康德:《道德的形上学的基础》(“Groundwork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p.391)T.K. Patton英译,页七。[9]& 康德(Immanuel Kant):《实践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Thomas Kingsmill Abbott英译本,页二七五~二八二;牟宗三中译本:《康德的道德哲学》,页三八四~三三九六。)[10]& Gensler, Harry J. Ethics, p. 50。[11]& 《杂阿含经》卷十二(二九三经)(大正二,页八三下)[12]& 笔者在《佛教规范伦理学》中,针对《中论》的“四门不生”偈,作过详细的分析:任何一法是不会自成的,也不会依他因而单独生成(即“不自生”、“不由他生”),因为任何一法都不可能在单独的条件下成立,这就无所谓“自”,进而也就没有与“自”相对的“他”单独存在了。为什么也“不共”生?“缘起”不正是因缘条件的共同组成吗?原来,这是排除由“自”与“他”共同产生的迷思;两者既都不能成立,两者之和当然也就无有意义。“无因生”则有两大过失:一、世间相违过:无因论与常识明显相违,因为现见世间人事物态之生成,都是有因有缘的。二、世间不成过:若支持无因论,则任何行为都无意义,人类文明亦无以缔造——人类一向就是在探究因缘中解决问题,改进生活,从而缔造出种种辉煌灿烂的文明成果。详参该书页四一~四七。[13]& 详见《杂阿含经》卷一○(大正二,页六七上),《中阿含经》卷二四“大因经”(大正一,页五七八中~五八二上)。此外在巴利藏的《大缘经》(Mahānidāna Suttanta),《长部》(Dīgha-Nikāya)2,55~57,南传七,页一~一五,以及《大本经》(Mahāpadāna Suttanta),《长部》(Dīgha-Nikāya)二,页三一~三五,南传六,页三九七~四○三,此诸经中,佛陀都提出缘起法。[14]& 更严谨而言,几乎所有传统的物理学理论,都遵循因果律。但量子力学的新发现──同样原因开始的微观过程,结果却各不相同──使得统计因果律置换了个别因果律。量子物理学(Quantum Physics)认为,在亚原子条件下,粒子的运动速度和位置,不可能同时得到精确的测量,微观粒子的动量、电荷、能量、粒子数等特性都是分立不连续的,量子力学定律不能描述粒子运动的轨道细节,只能给出相对机率,所以在微观世界中,因果律不再适用,只承认根据非常多的过程所获得的结果,以此归纳出的关于分布情况的规律。 这是一种非决定论,亦即:它终究不可能导引出“所有A因必然导致B果”的全称命题。但吾人仍可作如是观:测不准,有可能是加入了观察者本身能量的放射因素,有可能是由现在走向未来的自然程序因素,总之,吾人只能说“原因未详”,不妨先行阙疑,却不能依此达成“推翻因果律”的结论。[15]& 哲学界所谈之因果律,以经验主义哲学家休谟(Hume,)与康德(Immanuel Kant,)哲学为例:休谟的见地,见David Hum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 Edited with analytical index by L. A. Selby-Bigge , M. A Oxford 1946, pp. 73~93。他认为吾人的经验无法直接得知“因果关系”:“一切推理都只是比较和发现两个或较多的对象,其彼此间之恒常的或不恒常的关系。……心灵不能超出直接呈现于感官之前的对象,去发现对象的真实存在或关系。而只有因果关系才产生此一种联系,……超出吾人感官印象之外者,只能建立于因果之联系上。……唯一能推溯至吾人感官之外,并将吾人看不见,触不到的存在和对象提供予吾人者,即是‘因果关系’。”(pp.73~74)因此无法从经验证明因果关系的存在;人类只是由于习惯,才认为两个现象之间有所关联。康德同意休谟所说,因果观念不来自于经验,并进一步指出:因果观念是人类理性所提供的先验的认知范畴,因果律其实就是人类理性的表现。详见康德(Immanuel Kant):《实践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Thomas Kingsmill Abbott英译本,pp.169~174;牟宗三中译本:《康德的道德哲学》,页一九六~二○三。[16]& 林益仁访问笔者之内容,后经其整理而撰为〈佛法与生态哲学〉,经笔者修订后,发表于基督教界的《台湾教会公报》与佛教界的《法光杂志》。该文已收录于拙着《鸟入青云倦亦飞》,台北:法界,民八五年,页八五~九一。[17]& “缘无明有行,乃至生、老、病、死、忧、悲、恼苦集。所谓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谓无明灭则行灭,乃至生、老、病、死、忧、悲、恼苦灭。”出处参见注11。[18]& “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与“无缘大慈”之差别在于:“大我”再大,也还是从“我”这个自性情见幅射扩充,并不能真正“无缘——无条件”兴慈。为了大我之内的众生,也许真可以做到“抛头颅,洒热血”,“虽九死而无悔”,因为他的自我已扩而为大我的全部领域。然而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每见一族群心目中之所谓“民族英雄”,却是另一族群的梦魇恶魔——既然一己的“小我”都勇于牺牲,然则在同仇敌忾或是争取大我利益时,这种人是可以将“大我”之外的众生也一并“牺牲”的。所以“完成大我”的诸多故事,固然可歌可泣,但佛法还是把它归属于“我爱”的变相扩充——“我所爱”;伴随“牺牲小我”而来的往往是对大我的占领欲、控制欲,对大我与非大我之间入主出奴的偏见、歧视与对立。”详见释昭慧:《佛教伦理学》,台北:法界,页七八。[19]& 当然也有少见的特例;如忧郁症或被虐狂,会主动趋向死亡或接受遭致痛苦的待遇,但那也是“我爱”的变相呈现,在此姑不申述此诸“我爱”之变型[20]& 这三项原理,依拙着《佛教规范伦理学》所述而作修订增补,参见该书页八四~九三。[21]& 《杂阿含经》卷三七(大正二,页二七三中~下),《相应部》(Samyutta-Nikaya)五五“预流相应”(南传卷一六下,页二三六)。[22]& 见《法句经》合订本,台南:妙心寺,民国八○年五月版,页三○。[23]& “字面意义下的黄金律”导致的悖谬,如:一、对于一位病人:如果你要医生切除你的盲肠,则切除医生的盲肠。二、对于一位想被凌虐的被虐待狂:如果你要x虐待你,则虐待x。故Gensler将“相同处境”特别置入黄金律中,以避免此类字面意义下要求“一致性”所导致的悖谬(Gensler, pp.151~156)。[24]& Gensler, Harry J. Ethics, 周伯恒中译,pp. 147~173.[25]& Peter Singer,& Animal Liberation, 1996, p. 2 ; Gensler, 1999, pp. 163~164.[26]& 详见印顺导师:〈慈悲为佛法宗本〉,《学佛三要》,页一二○~一二三。
&&&&非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备案:
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金湖一里6号409室 邮编:361010 联系人:陈晓毅
电话:(值班时间:9:00-17:30) QQ群:8899063 QQ:}
现货市场行情
渤海商品交易所
内盘期市行情
上海期货交易所
大连商品交易所
郑州商品交易所
渤海现货交易所
交易所平台
上海期货交易所
郑州商品交易所
大连商品交易所
金融期货交易所
渤海商品交易所
数据合作电话:010-
意见反馈:datainfo@staff.hexun.com
文山三七 (CM0004)
9:00-11:30、13:30-16:00
最低交易保证金
本合同总货款的20%
交易手续费
上市交易所 渤海商品交易所 交割日期
三七,又名三七参、田七、土三七,古时亦称昭参、血参、三七参等,属五加科人参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是中国特有的名贵中药...
影响因素 &
qinyour888 : 菜粕走势偏弱,建议空单继续持有,止损2300 phonex8sx2re : 预计短期市场震荡偏强运行,可轻仓试多。【三七法则】
我的图书馆
【三七法则】
【三七法则】
&&&&&&&&七画是‘男’,三画是‘女’,七加三才是十全十美;男人聊天,七分谈理想,三分谈女人;女人则七分谈男人,三分谈理想。于是,男人征服世界赢得女人;女人征服男人赢得世界。男人的誓言,七分是假,三分是真。于是,男人不坏,女人不爱。
TA的推荐TA的最新馆藏[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
喜欢该文的人也喜欢佛教后设伦理学初探——从实然的现象与法则,到应然的原理与原则
查看: 1874|
评论: 0|原作者: 昭慧法师|来自:
摘要: 佛教后设伦理学初探——从实然的现象与法则,到应然的原理与原则释昭慧玄奘大学宗教学系所副教授兼应用伦理研究中心主任摘要:本文探索佛教系统理论的后设伦理学(metaethics),以佛法之伦理判断与道德原则本身为研...
佛教后设学初探——从实然的与法则,到应然的原理与原则释昭慧玄奘大学宗教学系所副教授兼应用研究中心主任摘要:本文探索佛教系统理论的后设伦理学(metaethics),以佛法之伦理判断与原则本身为研究对象,探究语词或道德语句是否能予以定义,并追问其道德判断的客观真理。依休谟法则(Hume’s law),实然命题不必然能推出应然命题,事实判断不等同于价值判断。一般于此均须预设自明真理(self-evident truth)或第一因(first principle),但佛法却依于“实然”之与法则,藉诸经验检证与理性分析,而直接推出“应然”之原理与原则。某种程度而言,佛法倾向于“自然主义”(naturalism),直接由自然性质或具经验意义的语词,来定义伦理语词。亦即:依现象以归纳出“”与“我爱”的实然法则,依“”与“我爱”复可证成“护生”之应然律令。“应”与“不应”的道德论述,恰恰是由之欲求(而非上帝之欲求)出发,以定义并简别“善、恶、对、错”之伦理语词与价值判断。准此“护生”原则,以满足“快乐”或“效益”之欲求,作为伦理实践之目标的佛法,就带有强烈的目的论(teleological theory)气息。人必须依于“自通之法”的心理能力,以自他互替原则来平等照顾其他生命“快乐”或“效益”的需求,就此而言,佛法也同样有着浓厚的义务论(deontological theory)倾向。依此系统理论之脉络,本文提出“实然如何证成应然”的四个问题,并一一作根源性的哲学分析以解明之。关键字:后设伦理学、自然主义、非自然主义、超自然主义、缘起、我爱、护生、自通之法、义务论、目的论Preliminary Systematic Theorization of Buddhist EthicsShih, Chao-HweiAssociate Professor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Religion andDirector of Research Center for Applied Ethics, Hsuan Chuang UniversityABSTRACT: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metaethics of Buddhist systematic theorization. First, can moral words and moral sentences be defined through Buddhist ethical judgment and moral principles? Second, what is the objective reality of Buddhist moral judgment?By Hume's law, an "is" proposition does not necessarily imply an "ought" i.e., fact judgment differs from value judgment. Generally speaking, we need to suppose a self-evident truth or a first principle. Yet, in Buddhism, we directly derive the "ought" principle from the "is" phenomenon by experience verification and reason analysis. In some sense, Buddhism is inclined to naturalism, which directly defines an ethical word by inpidual nature or an experience-meaningful word. Thus, Buddhism induces the "is" principle of pratitya-samutpada and self-love by phenomenon. From pratitya-samutpada and self-love, Buddhism proves the "ought" principle of life-protection. The moral argument of "ought" or "ought not" originates from the desire of life, not the desire of God. This defines and distinguishes the ethical words and value judgments of good, evil, right and wrong.The ethical and practical goal of the Buddhist life-protection principle is to satisfy the desire of sentient beings' happiness or utility. Therefore, Buddhism is strongly inclined to teleology. On the other hand, empathy must be given equally towards all sentient beings, and their need for happiness and utility. In this sense, Buddhism is also strongly inclined towards deontology.From the thread of the above systematic theorization, this article asks four questions about how the "is" proposition proves the "ought" proposition. Throughout the discussion, each question is philosophically analyzed in a radical manner.↑backKeywords: Metaethics, naturalism, non-naturalism, Supernationalism, pratitya-samupada, self-love, life-protection, empathy, deontological theory, teleologicaltheory一、前言科学家探究出核分裂可产生巨大能量的“实然”法则,依此发现而制造了核子武器或核能发电设备。科学家探究出体细胞核转殖乃至异种基因转殖的原理与技术,依此而复制出了动物,也培植出了转基因动、植物。但这些原理的证明,技术的操作,乃至依此诸原理以操作技术所获得的效应,即使在“实然”层面可资经验检证,并依理性之归纳、演绎、分析、综合等能力,而发现其中明确的因果关系,也无法据此诸“实然”现象及其原理,而直接导引出“应不应该发展核武或核电”、“应不应该复制生命”、“应不应该对动、植物施以基因改造”等等“应然”的答案。由于“实然”的探究,只过问事相的“真”与“假”,而不过问行为的“对”与“错”,因此,科学研发与科技政策,若要作“应然”的反思,常须借助伦理学的方法,而不能依本身的科学研究方法来达成此一目的。但许多科学界人士往往会粗糙地声称其为“价值中立”,藉以回避伦理争议。实则人心从来就不是一张白纸,在生命成长与社会化的过程之中,早已薰染了复杂而多样的价值观。即使是科学家,在其成长的岁月中,经由个性倾向、家庭因素、学校教育、社会影响等复杂而多面向的薰陶,早已形塑了伦理认知与伦理情感。因此,科学家还是自觉或不自觉地隐藏着某些价值判断,只是许多科学家却将一切研究都单纯化约为“真假命题”,伪装“价值中立”,好能达成不受伦理约束的效果。他们隐藏了一些什么样的价值判断?在此可例举三点:一、竞胜的价值观:将自己、学术单位、企业团体或国家的科研成就,当作最优位价值或唯一价值。我们常发现许多力图打破伦理禁忌,而作基因改造或复制工程的科学家,根本不讳言:他们在意的是哪个人、哪个研究团队或哪个国家,能优先获取研究成果。这就是“竞胜”的价值观,此中有时更隐藏着庞大而复杂的商业利益。这岂不就是“利己主义”(egoism)或各种本位主义的目的论(teleological theory)?二、阶级、性别、种族或物种歧视的价值观:阶级、性别、种族或物种歧视,会使人自动过滤那些受歧视的对象,将其排除于道德关怀的对象之外。即使将科学成就的效益,作极大化的发挥,考量的已是“人类利益”,但依然可能为了照顾人类的共同利益,而牺牲非人类之动物的利益,如此则将隐藏物种歧视,亦即“人类沙文主义”(Anthropocentrism)的价值观。三、满足情感的价值观:即使将效益考量极小化,把科学研究视作纯属自己探索学问的兴趣,这也依然隐藏着「以满足自己的兴趣倾向为优先”之价值观,这当然还是会被归纳为“利己主义”(egoism)。科学界每在宣告“价值中立”的同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这类隐藏性的价值观推到极致,坚持作一些伦理争议极大的研究与实验,这导致人们忧心忡忡,因为人们实在无法预知:这种“只顾获得实质效果,却不过问其是否应为”的研究态度,将给人类乃至生物界,带来何等巨大的冲击、损害与灾难。因此伦理学界、宗教界、法学界、社运界(乃至科学界内部)的良心人士,往往不得不站出来,适度扮演“踩煞车”的角色。相对于科学之为“实然”之学,伦理学(Ethics),恰恰是一门探索“应然”之学。哲学进路的伦理学,可大分为规范伦理学(normative ethics)与后设伦理学(metaethics)。规范伦理学与后设伦理学,犹如语言与文法的关系。一、规范伦理学:探究有关行为规范的基本原理与各种原则,以及日常生活面临道德问题的伦理判断。这门学问,研究行为之“对”与“错”,或德行之“善”与“恶”。规范伦理学所要讨论的是伦理行为之“应然”法则,但它不是要告诉我们“该怎么做”,而是在各种思想体系之中,探究“该怎么做”的原因何在。它不等同于直接告诉我们“应该遵守哪些规范”的戒律学或法律学,而是探索戒律或法律之原理的法哲学。具体的道德判断(如:张三不应杀害李四)与抽象的道德原则(如:不得杀人),共同构成了“道德语句”。规范伦理学,就是在“应然伦理”的意义下,建构并证成道德语句之体系的学问。当代分析哲学(contemporary analytic philosophy)有系统探讨“什么”心态或行为合乎道德或不合乎道德?其理由何在?是否充分的道德理由?这类研究道德原则之学,称为“规范伦理学”。[2]规范伦理学又可概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基础伦理学(fundamental ethics),探讨规范伦理学的基本理论(foundational theories),包含一套完整的,而且对所有人都有效的道德原则,用以判定行为的对错。第二类是“应用伦理学”(applied ethics),将基础伦理学所探讨的道德原则,运用在人生的不同实践领域中,以厘清并解决实际生活中所面临的具体道德问题。二、后设伦理学:或称“元伦理学”,以伦理判断与道德原则本身为研究对象,针对道德语词(如“善”)以及由道德语词所形成的道德语句(如“助人是善”),进行意义的分析、特质的探索,是为“后设伦理学”。后设伦理学所关心的不是道德语词或道德语句的建构与证成,而是道德语词或道德语句是否能予以定义,并追问其道德判断究属主观见解(或情感)抑或有客观真理。换言之,道德语词所表述的道德性质是实在而可被认知的?抑或并非实在,亦不可被认知?后设伦理学是当代分析哲学兴起之后才有的发展。传统的规范伦理学已预设了道德真理的客观价值,因此,传统规范伦理学家探究的不是道德原则有没有客观基础或充分理由,而是探究支持道德原则的客观基础或充分理由是什么。也因此,传统规范伦理学家往往对于其所预设的“客观价值”(如:上帝、良知、灵魂、善)全然不作质疑,从而倾向于“客观主义”(objectivism),忽略了道德真理的主观意义。难免有些规范伦理学家,视此类研究为挑战道德真理、动摇信仰与信念的麻烦制造者。然而后设伦理学并非全盘推翻道德原理与原则的客观基础,而是要更严谨地证成,道德原理与原则是否真有客观基础?如或有之,又是怎样的客观基础?它的作用在于将更深层、更根源性的基础理论,提供给规范伦理学,这也是它被称为“后设”的原因。是以Nielsen主张,后设伦理学的问题倘不清楚,根本不可能进行规范伦理学的讨论。[3]笔者曾着《佛教规范伦理学》乙书,以论述佛教的“规范伦理学”为主,亦即探索佛教伦理学之道德原理与原则,建立佛教戒律的法哲学与法理学。该书间亦视需要而就道德语词(如:良知)或道德语句(如:是否要依如来藏为道德原理),来作根源性的分析,本文之中,笔者则拟进一步探索佛教系统理论的后设伦理学。二、自然主义、非自然主义与超自然主义依逻辑实证论(logical positivism),任何严格的真理陈述,只有两种情况:不是可透过感觉经验来加以检测,就是可经由理性分析而加以定义。当然,我们也可以抬杠地说,即使是“有而且唯有感觉经验与理性分析这两种陈述,可用以判断事实的真与假”这样的一个命题,也未必可以透过经验检测与理性分析,来证明此一命题必为真理陈述,或证明确已没有第三种真理陈述的可能。如果不能得此证明,又如何能推翻“出现其他真理陈述的可能性”?但是无论如何,真理陈述的如上定义,使得伦理学家注意及“实然”与“应然”之间的对应问题。例如:“善、恶”或“对、错”这样的伦理语词,是可以被经验检测或理性分析的吗?后设伦理学(metaethics,或译“元伦理学”)有两大派,一派是自然主义(naturalism),主张伦理语词和道德信仰,可以由自然性质(natural properties)或具经验意义的语词来加以定义;另一派是非自然主义(non-naturalism),否认伦理语词可用经验检测与理性分析以定义之。非自然主义可溯自十八世纪哲学家休谟(David Hume)。他指出:我们无法从“实然”(is)演绎出“应然”(ought),是为休谟法则(Hume’s law)。[4]二十世纪的英国思想家莫尔(G. E. Moor)与洛斯(W. D. Ross),也宣称“善”是不可被定义的,并提出“直觉主义”(intuitionism),认为存在有客观的道德真理,而基本的道德真理,对成熟的心灵而言,乃是自明的。[5]依休谟法则,实然命题不必然能推出应然命题,事实判断不等同于价值判断。因此,依于“实然”之现象与法则,又当如何推出“应然”之原理?反之,若不依“实然”之现象与法则,“应然”的道德规范,又将据何基础以建立之?另有一种超自然主义(supernationalism),例如:一神论者或中国古代的墨家,莫不依“天启”或“天志”,来证成人所应克遵的道德规范。超自然主义将道德判断视为一种宗教陈述:“X是善的,因为上帝欲求X”。然而这将面对的是“上帝”与“善”之定义的循环论证。[6]此一“应然”法则,有其预设的自明真理(self-evident truth),是即上帝在“实然”层面必然存在,其欲求必然为善。从而“应然”的“天启”或“天志”,就有其不容置疑的权威性,而且人有义务奉行上帝的欲求。因此这类天启的规范,经常出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命令句。这种预设自明真理的“应然”之学,有其在实践层面的重大意义。康德(Immanuel Kant,)在“第一批判”中,检视了一些证明上帝存在的论证,指出传统以“存有论证”,以及建基于其上的“宇宙论证”的谬误。[7]他指出:像上帝存在、自由与灵魂不朽等,皆非现象界的事物,而已经超出了人类理性分析与经验检证的范围,故吾人固不能以理性证明上帝存在,也不能证明其不存在。而在“第二批判”中,康德则进一步主张:我们的纯粹理性虽不能证明上帝的存在,但人对上帝的信仰,却可在“实践理性”[8]中获得实践,人以理性意欲实践善行,便自然地要求上帝的存在。他把这些信仰称为“(道德)实践的设准”,亦即一个无法证明的假设,但为了实践的缘故,该假设必须成立。[9]特别是基督宗教,对人性的软弱(姑名之为“罪”)体会甚深,因此认为,人必须遵奉上帝的欲求,而不可聆听自己的声音。因为上帝之欲求必善,而人之欲求则不必然是善。而且即使人的伦理认知已能简别善恶,但人的道德情感,还未必能好善厌恶,人的道德意志,也未必就能舍善去恶。这就是保罗〈致罗马人书〉所说的:“我有行善的愿望,却没有行善的能力。我所愿意的善,我偏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而去做。”(〈罗马书〉7:17~18)因此超自然主义难免会质疑无神论者:若不能全心全意地将自己交给上帝,坚定地奉行上帝的意旨,人如何可能抗拒自己的罪性,来奉行道德律令?(或更简单地说:不信奉上帝的人,如何能不混淆道德?)如此理解,吾人较不会预存偏见,迳将基督宗教简化为“排他性宗教”,而能以同理心体会:何以基督宗教之“应然”规范,会将“信奉上帝”列为十诫之首要条目?因为在此系统理论之中,上帝已是其他一切诫命或规范的基本原理,不能信奉上帝,即不足以产生奉行其余诫命或规范的强烈动机。而且超自然主义也未必会走向“排他主义”,至今已有更为丰富而多元的神学诠释,例如:“包容主义”业已出现于主流教派的神学论述之中。预设存有实体之“天”或“天道”,则“天启”、“天志”之道德规范,就有不可违越的权威性,这样的神学进路,顺利架构了“由实然而应然”的内在逻辑。但其困难则在于:一、如何运用理性分析与普遍性经验,来证成超自然之存有实体?这部分,经由西方哲学家与神学家的反覆讨论,虽已有了极其丰富的成果,只是迄未获得一个诸方满意的共识。二、若超自然之存有实体,不能依循理性分析与普遍性经验的路径以体认之,只能仰仗特殊的冥契经验,又当如何令不信者启信?三、对未信者而言,既已无法确信上帝之存在必为“实然”,又如何能服膺由天启或天志所宣告的“应然”规范?四、对已信者而言,如何避免陷于将未信者视为“对道德混淆不清的人”[10],从而产生“自以为义”的道德傲慢,卒至重新陷溺在自己原应跳脱的“罪性”之中?依于本文所作的根源性分析,显示佛教伦理学并未预设道德真理为“不可定义也无法证成的自明真理”,因此不属于“非自然主义”。当然,作为“无神论”的佛教伦理学,不会建立第一因之存有实体(如上帝)以为自明真理,因此也不属于超自然主义。某种程度而言,佛法反倒倾向于“自然主义”(naturalism),直接由自然性质或具经验意义的语词──“缘起”与“我爱”,来定义伦理语词──“护生”,并据“缘起”与“我爱”之实然法则,以证成“护生”心行之合理性与必然性。亦即:依现象以归纳出“缘起”与“我爱”的实然法则,依“缘起”与“我爱”复可证成“护生”之应然律令。三、佛教伦理学之后设性议题乍看之下,或许吾人会以为,这样便毋庸面对证明第一因之真实性与权威性的质疑。然而吾人同样必须审慎面对以下四个由实然而应然的问题:一、首先要问的是,“缘起”是佛陀在深彻的直观(现量证境)中,所获证的答案;但现量证境同样并非普遍性经验,佛陀是如何将这种“唯证方知”的非普遍性冥契经验,转化为一种透过理性分析与经验检测,可辨明其真假值的“实然”之学?或扩大范围而言,面对世间一切“实然”现象,佛法当如何让人用理性思辩与普遍性经验,来理解彼诸现象之所以如此或如彼呈现的“实然”法则?如能证成此点,则佛法不须预设无法证成的自明真理或第一因(first principle),因此也不须面对“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问题。二、如前所述,“实然”之现象与法则,不必然就能据以推出“应然”的道德命题。依佛法之理论以观,因缘条件之聚散,导致现象生灭、成毁,这套“实然”的缘起法则,似乎并不能告诉我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也似乎不能告诉我们,在不可得兼的情况之下,应该孰先孰后。举例而言,病毒感染,再加上未能适当隔离、防护等等诸多因素,导致疫病大流行。发生芮氏七级大地震,加上房屋的防震系数不够,人们在仓促间来不及出外避祸等等诸多因素,导致大量屋毁人亡。像这些现象,可用“缘起”法则来加以理解;但它似乎不能直接明白地告诉我们:面对这两件事,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应做诸事之中,又应孰先孰后?因此,其次要在本文之中解明的就是:即使真能透过理性分析与普遍性经验,令人理解“缘生”之现象与“缘起”之法则,又当如何据以建立“护生”的应然原理?三、复于“实然”层面观察众生,佛法同样见到人性的软弱,但较少名之为“罪”,大都用理性错乱之“无明”、情、意偏差之“爱、取”以名之,或称此诸罪性为烦恼(缠、结、使等),此诸罪行为恶业。顾名思义,显见这些都被视作生命负面价值的展现,其原因安在?正、负价值复依何种判准以简别之?四、依佛法以看待生命,有那些实然的身心状况,可以具足正面价值,乃至可以扭转无明与爱取?或是必须采取基督宗教的方式,为生命的出路而在身心实况之外,另寻“救赎”的源头?总之,在“实然”层面,究依何等道德真理之基础,以提示其“应然”之道,而且确保此“应然”之道,可以扭转该诸“实然”的心理现况?进以言之,面对根深蒂固、如影随形的“罪性”,基督宗教已在“实然”层面,预设了上帝以为自明真理,因此其“应然”之道的内在逻辑非常清楚:在自利方面,依于上帝的恩典以获得自我的“救赎”;在利他方面,回应上帝之爱,而爱及同依天主肖像而受造的“邻人”乃至“敌人”。那么,依佛法以看待根深蒂固、如影随形的无明与爱、取,在“实然”层面又当以什么作为基础,其“应然”的内在逻辑又是什么?亦即:在自利方面,人们依于何种力量来获取效益或获证解脱?在利他方面,“护生”为本的种种规范,又要靠何种力量,方能抗拒无明与爱、取,而获得实践的保证?第四个问题,凡已涉及工夫论的部分,笔者将另文处理,本文但依佛法之系统理论,将这四个“实然如何证成应然”的问题,作根源性的哲学分析。四、缘起:“实然”之现象与法则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面对世间一切现象(诸有为法),佛陀依智慧洞观其缘生缘灭,而悟证“缘起”(梵pratītya-samutpāda;巴paticca-samuppāda)法则。这种现量证境,唯证方知,因此说是“缘起甚深”,这可依于两个面向来解明其“甚深”义:“此甚深处,所谓缘起;倍复甚深难见,所谓一切取离、爱尽、无欲、寂灭、涅盘。如此二法,谓有为、无为。有为者,若生、若住、若异、若灭;无为者,不生、不住、不异、不灭。”[11]为,即是造作。有为(梵 samskrta)法,即生灭变迁的一切现象。要在现象中洞观其均为因缘条件组合或制约下的存在,而不复产生“非有即无、非常即断、非一即异、非动即静”的错觉(离此二边),已经极不容易,复须洞观其“非自生、非他生、非共生、非无因生”,[12]是则倍复艰难。乍看之下,“共生”与“缘生”似乎区别不大,实则不然。原来缘起并不单纯是a1+a2+ a3……=A这么单纯的演算。任一A固然是因缘和合而无终极自性的,任一a1或a2或a3,又何尝不是因缘的产物?倘若将a1剖析下去,它是来自b1+b2+b3……的组合;b1又是来自c1+c2+c3……。这样无穷尽地分析下去,哪有终极实在的质素可得?此所以缘生又被龙树称为“无生”或是“(自)性空”,亦即,只见诸因缘条件之聚散离合,却不见有永恒、独立的终极实在(自性)可得。此理艰深,故曰“甚深”。无为(梵 asamskrta)法,原指涅盘证境的“择灭无为”(即前引经文中所说的“一切取离、爱尽、无欲、寂灭、涅盘”),以及缘阙不生的“非择灭无为”,后又加入以无碍为性,容受万物而遍满一切处的“虚空无为”。这三者都有不生灭、无变迁的特质,故名“无为”。在部派佛教的开展中,大众、分别说部也将实然现象的原理、法则名之为“无为”。原来现象虽然生灭变迁,但其生灭变迁的法则,却有必然性、恒常性与普遍性(故名“法性、法住、法界”);显然也符合无为法“不生灭、无变迁”的定义。这种“唯证方知”的甚深悟境,佛陀是如何让人用理性分析与普遍性经验,来理解彼诸现象之所以如此或如彼呈现的“实然”法则?这可参看《杂阿含经》中,阿难为迦旃延所做的“缘起”论述:“如来离于二边,说于中道。所谓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谓缘无明有行,乃至生、老、病、死、忧、悲、恼苦集。所谓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谓无明灭则行灭,乃至生、老、病、死、忧、悲、恼苦灭。”[13]佛法的“缘起”论,简单而言,即是“此故彼”的法则──是“此”诸因缘展转呈现“彼”诸果法的法则。它虽是佛陀在深邃的直观之中所体悟的法则,但当佛陀“由证出教”之时,却完全诉诸生命苦感的普遍性经验,与离于二边的理性分析,而不诉诸神格的权威。“缘起”是有为诸法生灭变迁的因果律,这与科学在研究与发明的过程中所遵循的因果律[14],或哲学依理性而证成的因果律[15],内容虽不完全相同,但同样未诉诸信仰与想像,因此较无“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之难题。五、依“缘起”之实然,证成“苦灭”之应然即使透过常识经验与理性分析,而证明了“缘起”为森罗万象生灭变迁的“实然”法则,吾人又当如何依“缘起”之实然,以推出其伦理规范之“应然”?作为行为主体的“人”,如何在此一自然法则下,获得伦理方面的启示?亦即:如何由万法“实然”之理,以证成人所“应然”之事?这就进入了前述第二个问题,而有待作进一步的分析。林益仁教授曾向笔者询问道:“最近正好在看英国一位学者的文章,他也在研究佛教和环保运动的关系,他提到缘起法,他觉得缘起法最后并没有告诉我们一个目的性,没有指出一个终极目的在那里,因为物物相关,各个现象彼此有相关联性;但彼此相关,并不表示一定朝某一方向走。所以他的结论是:缘起法好像很难推出‘现在我们一定要去救犀牛或是一定要去救流浪狗’的结论!”[16]事实上,“要救谁”,这已是第二序的问题,此中已预设了第一序的“应该救”之前提。吾人甚至可以进一步质疑这样的前提:缘起法又如何证明吾人“应该救”他者?特别是,因缘生灭的现象界,众生依于心理利己之自然倾向,大都循着弱肉强食、物竞天择的法则,挣扎存灭于其间,俗谚声称:“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正是说明了此一法则下“利己”的正当性。难道强调经验检证的佛教伦理学,可以依此实然现象,以叙述一套“只应利己,不应利他”的应然哲学吗?然而无论是重在自利的声闻佛教,还是强调利他的大乘佛教,无不谆谆劝告世人,应该勤于“护生”。亦即:在消极方面不伤害众生,在积极方面让众生离苦得乐。可见得佛教伦理学,确实有“利益众生”的重要面向。进以言之,“利益众生”若是应然之道德要求,又将如何从缘生现象与缘起法则,而给予合理的推论?于此可以注意:“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这原是一切现象生灭变化的通则,生物、非生物、动物、植物都不例外。阿难却在紧接着的说明之中,将关怀范围缩小为有情,阐述以胎生众生为例的十二缘起。显见佛陀所洞烛之实然法则,虽有普遍性与恒常性,但佛陀所关切的对象,却以生命为主。因此佛法特别针对有情,依其承受种种诸苦的现状而作分析,叙述其依于缘起法则,所面对的“苦集”(流转生死且如环无端的十二缘起)与所可获证的“苦灭”(灭除烦恼,证得解脱,亦即涅盘寂静)。[17]易言之,“应然”的苦灭之道,即奠基于此一苦集的生命实况之上。原来,无生物并无生命现象,植物虽有生机,却不如动物之有意识与感情(故名“有情”,梵sattva),不似动物有苦乐的感知能力,所以佛法关切的重心,仍是以动物为主的“有情”。由“实然”而“应然”,依有情在生理、心理与心灵层面的实际需要,而提出让生命得遂所求以“离苦得乐”的种种方法──或浅或深的“苦灭”之道。六、依惑、业、苦流转之实然,证成“离苦得乐”之应然至此,也就可以进一步回答前述第三个问题:理性错乱之“无明”、情、意偏差之“爱、取”,乃至烦恼(又名惑、缠、结、使等)与恶业,确乎被视作生命负面价值的展现,其原因是,顺着这些负面的生命欲求来发展,会带来自己生命与其他生命的无穷痛苦。而且这烦恼(惑)、业、苦的层层相生,是循环不已,流转无穷的。这种生命现况,并不符合生命“离苦得乐”的欲求。原来,在认知方面,昧于“缘起”法则的众生,无法体悟得:因缘生灭的现象之中,无有常恒、独立、真实不虚且可自由主宰之“我”可得;反而本能地错觉有一“自我”,并以此一“自我”为中心以估量一切,从而产生无可避免的认知错乱。此一根深蒂固的认知错乱,名为“无明”(梵avidyā)。在情感方面,昧于“缘起”法则的众生,对于自身的处境,必然因自我中心的“无明”,而产生强大的关切之情,是为“我爱”。无明与我爱发为意欲,于是产生了强大而本能的生之意志,以及种种得遂生命欲求的“取”或“业”。昧于“缘起”的众生,知、情、意三方面都围绕着「自我”而转,于是产生了一种内聚力,使生命本能地牢牢执取“自我”,聚集任何对“自我”有益的质素,排除任何对“自我”有害的因缘。强大的无明与爱、取,使得众生总是下意识地抓住一个模糊的中心,不断地从这蒙昧的中心,产生自我意识的漩涡,将具体事物内聚性地卷入意识漩涡之中,名之为“我所”(我所属或我所有的一切),来作为“我”的表现或“我”的扩大。源自“我爱”所扩展的“我所”之爱,乍看之下亦能产生“利他”之行,其实还是源自“利己”心理的辐射。[18]既然利己心态在众生界,已属牢不可破的本能,那么,以此看待伦理利己主义,人们在伦理行为中,会理所当然地寻求“自保”,或是扩大地追求自己或“我所”的利益,这也是人情之常。至于这个利益,究竟是五欲享乐、权力、名声、长寿,还是生命的终极出路?当然随各人的价值观而不等。问题是,这种顽强而本能的无明与爱、取,可以进一步发展成为伤己、伤人的双面利刃。在伤己的方面,它让个人为了自我满足而执着于自体与境界,却因无法掌握自体与境界的一切因缘变化,从而饱受它们无常败坏,不符自己之所期待的种种痛苦。在伤人的方面,无明与爱、取,还可能会为了自我满足,从而妨碍甚至剥夺他者自我满足之欲求,从而减损他者之快乐与舒适,甚至导致他者之种种痛苦。亦即:生命与生命之间,可能会因彼此都有无明与爱、取,而形成互相的妨碍与伤害。这不但伤人,而且其反作力又会伤及自己。因为他者同样具足无明与爱、取,一旦受到了自己的妨碍与伤害,可能会对自己因怨憎而报复,从而减损自己之快乐与舒适,甚至导致自己的痛苦与死亡。进以言之,苦集与苦灭有其“此故彼”的实然法则,然而佛法又何以认定孰应孰不应?何以认定生命应该依循“苦灭”之道,而非“苦集”之途?这是因为,依“缘起”法则而流转世间的生命,都有以自我为中心之欲求(我爱),由是而产生强烈的趋生畏死,趋乐避苦之本能。[19]这是每个有情经由常识经验即可自我检证的“实然”,而“应”与“不应”的道德论述,恰恰由此生命之欲求(而非上帝之欲求)出发。凡消极不伤害或积极满足其他生命“趋生畏死,趋乐避苦”之欲求的动机为“善”,业行为“对”;凡抵触其他生命“趋生畏死,趋乐避苦”之欲求的动机为“恶”,业行为“错”。正面价值或负面价值,即依此以为判准。准此“护生”原则,以满足生命“快乐”或“效益”之欲求,作为伦理实践之目标的佛法,就带有强烈的目的论(teleological theory)气息。但人不应该只顾追求自己生命的“快乐”或“效益”,而且必须依于“自通之法”的心理能力,以自他互替原则来平等照顾其他生命“快乐”或“效益”的需求,就此而言,佛法也同样有着浓厚的义务论(deontological theory)倾向,此点将于下节详之。七、依三种原理之实然,证成“护生”之应然如前所述,孰为正面价值?孰为负面价值?端看它带来的是满足生命欲求的快乐,还是斫伤生命欲求的痛苦。价值判断不建构在某种预设的自明真理之基础上,而直接建立在“苦乐”之分辨的普遍性经验之基础上;伦理动机之“善”与“恶”,伦理行为之“对”与“错”,也同样依其是否可满足“离苦得乐”的生命欲求,来加以检证。接着要提出第四个问题:依佛法以看待生命,有那些实然的身心状况,可以具足正面价值,乃至可以扭转无明与爱取?或是必须采取基督宗教的方式,了然于身心实况深彻的罪性,而在身心实况之外另辟蹊径,为生命另寻“救赎”的出路?总之,在“实然”层面,究依何等道德真理之基础,以提示其“应然”之道,而且确保此“应然”之道,足以扭转该诸“实然”的负面现况?如前节所述,生命实况是如此的依于无明与爱、取而自伤伤人,看似无可救药。佛陀不可能反向操作,违逆生命欲求之本能,而教人以“苦集”(自讨苦吃)之道,但他却未另寻生命本身以外的权威性救赎力量,而是因势利导,顺应生命的欲求,而告诉吾人“苦灭”之道──教人消极方面避免伤己伤人,积极方面让自己与他人的生命,都获得快乐与舒适,是为“护生”。以“护生”作为应然规范的总纲,其理据并不建立在预设的自明真理(上帝的欲求)之中,而直接诉诸经验检证(生命的欲求)。因此“护生”之为伦理语词,也是可依经验检测或理性分析来作定义与阐述的。以下即本诸前述“缘起”法则与“我爱”实况,依“自通之法”等三项可以诉诸经验检测与理性分析的“实然”原理,据以推论:“护生”是一切“应然”规范的总纲。[20](一)自通之法从原始的《阿含经》到大乘经典,处处说明护生的道德基础——“自通之法”,如《杂阿含经》说:何等自通之法?谓圣弟子作如是学:我作是念:“若有欲杀我者,我不喜;我若所不喜,他亦如是,云何杀彼?”作是觉已,受不杀生,不乐杀生。如上说,……”[21]又如《法句经》“刀杖品”(Dandavaggo)说:一切惧刀杖,一切皆畏死,以自度[他情],莫杀教他杀。一切惧刀杖,一切皆爱生,以自度[他情],莫杀教他杀。[22]这就是“自通之法”:用自己的心情,揣度其他众生的心情,而珍重他趋生畏死,趋乐避苦的天性。在这方面,佛法有着浓厚的义务论倾向。道德律不必假诸其外、其上的天启或天志,而就在每个人的心中。一个具足“自通之法”的人,会自发性地奉行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的七种圣戒(一般将后四种恶语业之戒合并为一“不妄语戒”,而成五戒)。如前引《阿含经》所述,持七圣戒(五根本戒)的利他善行,其结果虽然使得自己也获得人天乐果之酬偿,但原初持戒的动机,却不宜来自“利己”的考量,而要出于自他互替、同情共感的“自通之法”。若时时依“自通之法”以行事,那么,即使自己向往世间福乐的目标并未改变,也能在过程之中,因时常自他互替,同情共感,而产生强大的利他动机,并逐渐养成“利他”的道德习惯。如此奉持净戒,进而净信三宝,那么待到预入圣流,证悟解脱之后,必当恍然大悟“自我”的虚幻无稽。“自通之法”极类似儒者所说的“良知”,在伦理学上名之为“黄金律定理”(Golden Rule Thoerem)。当代伦理学家Gensler依康德(Immanuel Kant)的黄金律,作了进一步的细腻辩证与小幅修改,以排除诸如被虐狂之类在字面意义下之黄金律所导致的悖谬[23],然后为黄金律下了两个精准的定义:一、“只依在相同处境下你同意被对待的方式来对待别人”;二、倘若“我对另一人作出了某件事,而在相同处境下,我不愿意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那么,此人显然对己对人有不一致的行为标准,因而违反了黄金律。[24]这是不同文化所共同遵奉的黄金律,但基督宗教与康德,并未将动物纳入黄金律所涵盖的对象;基督宗教是基于“神性”的原因,康德则是基于“理性”的理由。不具足神性或理性的动物,未能被人类纳入作为“一致性”的道德考量。但是佛教却明显地将动物纳入作为“自通之法”的对象,其理由在于,动物与人同样具有“不喜被杀”等等的喜怒哀乐的情绪与痛苦的觉受能力。既然如此,则“自通之法”显然无法排除对动物处境的同情共感。是故黄金律所涵盖的对象,应以“感知能力”作为判准,同情共感的关怀面,应不只及于人类,而必然会扩大到所有有情(包括动物)的身上。在这方面的伦理判准,动物解放哲学家Peter Singer与伦理学家Gensler的看法,与佛教是较为一致的。[25]佛所说的“端正法”:布施、持戒、禅定,都是让修学者自身得受人天福乐的方法。其中两项“利己”之道——持戒与布施,前者是是消极的不害于他,后者则是积极的施与快乐。此两者要从“利己”而转向“利他”,关键即在于“自通之法”:持戒与布施,在此已不是为了自己的更高利益,而是出自对他人之处境的同情共感。所以在消极方面,克制自己,避免因自己行为不当,而置他人于痛苦境地;在积极方面,则分享资源,以财物、体力、言语等各种布施,改变他人的境遇,使其离苦得乐。即使是圣者的菩萨心行──“无缘大慈”与“同体大悲”,其初也莫不以“自通之法”作为基础。准此以观:“我爱”原是对“自我处境”的强烈关怀。如前所述,它是一把伤己、伤人的双面利刃,可以掉入自我中心的深渊,起惑、造业、感苦,造成自误、误人的后果。反过来说,它也吊诡地形成一把利己、利人的双面利刃── 一方面,它本能地在任何时刻,寻求自己快乐、舒适、趋生避死之道;另一方面,它也可以由“自我关怀”的基础而逆向操作,易地而处,对他人的“自我关怀”同情共感,从而实践利他主义。而这也显示了佛陀教学的一大特色:他依“生命的欲求”而因势利导,无论是在心理层面还是伦理层面,实然层面还是应然层面,都架设了一个从利己而达到利他的桥梁。至此,已可完整回应前述第四个问题:依佛法而言,利己与利他,都不需仰仗权威性他者的道德指示与“救赎”力量。(二)缘起法相的相关性再者,缘起论提醒吾人,任何一个有情,都是与无数因缘连结的“网络”性存在体。生命不可能独立存活,也不可能在没有适当因缘条件的支持之下,获取自我满足的快乐与舒适。因此在“应然”层面,无论是为了自我满足,还是为了感念(得以成就自我满足之愿望的)因缘,吾人都应顾念他者,而非只看到自己的需要。这是依于缘起法相依互存之“实然”法则,所可导出的“应然”意义。另外,此一实然法则,也可进以说明前述“自通之法”的本质,并进以解释,何以同具“自通之法”的人们,会在道德感情与伦理抉择方面,出现个别差异。自通之法虽是普世与共的道德黄金律,但是它的来源为何?是有客观依凭,还是纯任主观情绪?是来自外在的天启,还是来自内在的直觉?是不证自明的真理,还是要依更根源的真理以证成之?这就随诸家说法而有重大差异。依缘起论,良知是主体与客体交融互会的产物,它并非来自外在的天启,而且可以依更根源的真理“缘起”以证成之。简而言之,良知是道德主体相应于缘起事相“相依相存”且“法性平等”之法则,而对同为有情之客体,所自然流露的同情共感。而缘起法的相依共存与法性平等,此二法则,被印顺导师视为“慈悲的根本”。[26]进以言之,依“缘起”法则以观:存有的任一现象(有情包括在内),原都不是隔别孤立而可以单独存在的,须要有“众缘和合”以成就之。因此,因缘生法本身,就与其他的因缘所生法,有着「相依相存”的复杂网络。在这前提之下,因缘相互支援成就的生命体与生命体之间,如何可能不存在着隐微而畅通的管道呢?吾人的九孔七窍,与外在环境无一瞬间不在互通状态。吾人的表情、语言、行为,更与他者相互传递丰富的讯息。此所以生命虽有各别隔历的形体,但形体与形体之间,却并非“绝缘体”。前述同情共感的“自通之法”,即是本此而生。因此,对其他生命的尊重,就不只是素朴的主观好恶或情绪因素,在主体对客体同情共感的现象背后,有其“法则”存焉。生命会依互通管道的畅通程度,而出现自通之法的个别差异,这就是人人具足良知,但各人的道德自觉却又往往悬殊的缘由。当人愈是将“自我中心意识”减低,这种“互通”的管道,就愈是通畅。至亲至爱之人的互通管道,较诸常人更为畅通,有时甚至可以让人超越我爱的本能。例如:火场外的母亲,可以奋不顾身扑回火场抢救亲儿;但未必能对邻家小儿做到这一地步。圣者则因其体悟“缘起无我”,所以可不倚仗任何依“自我”为中心而辐射出“我所”之沟通管道,而对其它生命之苦乐,不问亲疏地产生毫无藩篱的感知能力,并施与毫无差别的慈悲,是名“无缘大慈”。(三)缘起法性的平等性有情在“实然”层面,均有其感知能力,因此吾人应平等考量有情这种觉知苦乐的感受,尽可能满足其离苦得乐的欲望。这是在应然层面,提倡“众生平等”的重要理由。这点,与Peter Singer的看法大同。其次,由于一切有情只是因缘条件组合下,相对稳定的存有个体,所以,在因缘条件变化时,个体的尊卑优劣之处境,也就跟着发生变化。一切阶级意识、种族认同或是性别歧视,都是执着于阶级、种族或性别之真实性,而生起的一种“常见”,也是一种“我慢”(自恃凌他心态)作怪的“自性见”,在现象差别的背后,缘起性空,诸法无我,故永恒不变、独立自存而真实不虚的现象自体,了不可得(是为性空、无我义)。易言之,“诸法缘生无自性”,在此一法则下运作生灭的,只有相对稳定的个别现象,却无永恒差别的实体可得;在差别法相的底里,这又是一个实然层面“法性平等”的理则。以此法性平等的理则,拿来观照缘起法的差别相时,“众生平等”就不再只是从其平等的感知能力,而且是从其平等的缘起法则以证成之。“同体大悲”由此萌生——拔除众生痛苦,给予众生快乐,这已不须来自任何“自他互易”的想像与判断,而是直下植基于“众生法尔平等不二,同体相关”的甚深悟境。这时,“护生”已不只是一种素朴的感情,一种互惠的思维,而形成了一种情识与情爱的升华。“护生”已不只是一种美德,而形成了有道德自觉与理性思辨能力,意欲提升“情识与情爱之层次”的“人”所应恪遵的“义务”。八、结论综上所述,佛法的缘起论,不须预设第一因或不可证成的自明真理以为前提,而可依经验检证及理性分析以理解之;即使是没有冥契经验的一般人,依然可以体悟其“实然”原理,而不须面对“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之争议。缘起论虽与科学同属(可依经验归纳以理解的)“实然”理论,但科学方法只证明“真假值”,而不能据以判断其“对、错、善、恶”,而必须另行仰仗各种伦理学的系统理论,来抉择其“应不应然”。“缘起论”则不但是一切现象因缘生灭之原理,以及生命流转生死的实相,而且可即此原理而判断其“对、错、善、恶”,并据以推演出“应然”之道──自利、利他的理由与方法,以及种种克己、护生的行为规范。易言之,依佛法的系统理论,从“实然”之缘起法则与生命欲求,即能解析“应然”的原理与方法,而不须诉诸另一套伦理学,也不须诉诸“天启”之类的自明真理。进以言之,依于缘起之“实然”法则,如何达成利己与利他的两项“应然”之道?这一部分,业已牵涉到内容丰富的工夫论,笔者将另文处理,本文只在此作一概略性陈述:一、在利己方面,顺应生命强烈利己的本能,佛陀教授以“如何利己”的“应然”之道──布施、持戒、禅定,由此而巧妙地连结了利己与利他的桥梁。二、在利他方面,由于“我爱”本能在生命界中普同存在,而生命又与诸因缘相依互存,因此生命的身心发展,或多或少有其沟通渠道,在情感上即发展为“觉知他者苦乐”的自通之法,此即是利他德行的“实然”基础。依此利他实相以建构的“应然”之道就是:人应在消极方面力求节制自己(持戒),以免伤害他者之我爱;在积极方面分享资源(布施),以让他者也能获得自我之满足。对于一个少分、多分或全分体悟缘起的人而言,无论他在名义上是不是“佛教徒”,或多或少会对相依共存的众生,产生一种直觉性的同情共感。圣者也是在这样的情感基础上,透过缘起深观而超越自我,从而将“利他”视作自己责无旁贷的“义务”,而不会自矜为一桩“美德”。最后综合前述要理,补充诠释“平等”三义。“平等”原是佛经用语,日本依此以对译英文之equality。佛法中的“平等”有三种层次:一、生命均有感知能力,应平等尊重生命的苦乐感知,以及其离苦得乐的强烈意愿,是即“众生平等”之要义。二、生命又都依因待缘而生灭变迁,是即缘生诸法在差别相中,无自性义平等无二,是为“法性平等”之要义。三、不但凡夫依因待缘而承受苦乐、流转生死,圣者也是依因待缘而证入涅盘、成就佛道。在此“缘起”法则之下,凡夫有修三学以解脱的可能性,也有修六度、四摄以成佛的可能性。后者,即“佛性平等”之要义。“我爱”的生命本能,即在自他互易的反省之中,而发挥了超越自我藩篱以“护生”的精神;复由深观“法性平等”与“佛性平等”之“无我”实相,更能将“护生”精神发挥到极致,而契合于“众生平等”的道德理想。由“实然”之体悟而实践“应然”之德目,再由“应然”之履行而印证“实然”的圣境。“实然”的体悟有多深广,“应然”的实践就有多深广;“应然”的履行有多彻底,“实然”的印证就有多彻底──这就是从“实然”到“应然”一脉相承的缘起论。──九四、五、三完稿于尊悔楼--------------------------------------------------------------------------------[1]& 本文初稿名为〈应然伦理之证成——依“缘起论”之佛法观点〉,93年11月18日初成,并发表于当年11月27日,在东吴大学所举行的台湾哲学学会年会之中。本文依该份初稿而作大幅修订与增补,完稿于94年5月3日,并于94年5月15日,于玄奘大学第一届“应用伦理会议”中作专题演讲。*& 玄奘大学宗教学研究所副教授兼应用伦理研究中心主任。[2]& Nielsen, Kai. “Problems of ethics”. In Th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vol. III, edited by Paul Edwards.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 The Free Press. 1967, p.118。[3]& Nielsen, Kai. “Problems of ethics”, p.119。[4]& Gensler, Harry J. Ethics, copyright by Routledge, 周伯恒中译,台北:韦伯文化事业出版社,1999,pp. 70~71。[5]& Gensler, Harry J. Ethics, 周伯恒中译,PP. 68~83。[6]& 有关“超自然主义”的详细辩证,参见Gensler, Harry J. Ethics, copyright by Routledge, 周伯恒中译,pp. 49~63。[7]& 康德(Immanuel Kant):《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Norman Kemp Smith英译本,页六二○~六四七;牟宗三中译本,下册页三四五~三七五。)[8]& 什么是“实践理性”?即是实践(道德)应用下的理性,“说到底,只有一个相同的理性,而问题在于要分辨此一理性之各种应用。”康德:《道德的形上学的基础》(“Groundwork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p.391)T.K. Patton英译,页七。[9]& 康德(Immanuel Kant):《实践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Thomas Kingsmill Abbott英译本,页二七五~二八二;牟宗三中译本:《康德的道德哲学》,页三八四~三三九六。)[10]& Gensler, Harry J. Ethics, p. 50。[11]& 《杂阿含经》卷十二(二九三经)(大正二,页八三下)[12]& 笔者在《佛教规范伦理学》中,针对《中论》的“四门不生”偈,作过详细的分析:任何一法是不会自成的,也不会依他因而单独生成(即“不自生”、“不由他生”),因为任何一法都不可能在单独的条件下成立,这就无所谓“自”,进而也就没有与“自”相对的“他”单独存在了。为什么也“不共”生?“缘起”不正是因缘条件的共同组成吗?原来,这是排除由“自”与“他”共同产生的迷思;两者既都不能成立,两者之和当然也就无有意义。“无因生”则有两大过失:一、世间相违过:无因论与常识明显相违,因为现见世间人事物态之生成,都是有因有缘的。二、世间不成过:若支持无因论,则任何行为都无意义,人类文明亦无以缔造——人类一向就是在探究因缘中解决问题,改进生活,从而缔造出种种辉煌灿烂的文明成果。详参该书页四一~四七。[13]& 详见《杂阿含经》卷一○(大正二,页六七上),《中阿含经》卷二四“大因经”(大正一,页五七八中~五八二上)。此外在巴利藏的《大缘经》(Mahānidāna Suttanta),《长部》(Dīgha-Nikāya)2,55~57,南传七,页一~一五,以及《大本经》(Mahāpadāna Suttanta),《长部》(Dīgha-Nikāya)二,页三一~三五,南传六,页三九七~四○三,此诸经中,佛陀都提出缘起法。[14]& 更严谨而言,几乎所有传统的物理学理论,都遵循因果律。但量子力学的新发现──同样原因开始的微观过程,结果却各不相同──使得统计因果律置换了个别因果律。量子物理学(Quantum Physics)认为,在亚原子条件下,粒子的运动速度和位置,不可能同时得到精确的测量,微观粒子的动量、电荷、能量、粒子数等特性都是分立不连续的,量子力学定律不能描述粒子运动的轨道细节,只能给出相对机率,所以在微观世界中,因果律不再适用,只承认根据非常多的过程所获得的结果,以此归纳出的关于分布情况的规律。 这是一种非决定论,亦即:它终究不可能导引出“所有A因必然导致B果”的全称命题。但吾人仍可作如是观:测不准,有可能是加入了观察者本身能量的放射因素,有可能是由现在走向未来的自然程序因素,总之,吾人只能说“原因未详”,不妨先行阙疑,却不能依此达成“推翻因果律”的结论。[15]& 哲学界所谈之因果律,以经验主义哲学家休谟(Hume,)与康德(Immanuel Kant,)哲学为例:休谟的见地,见David Hum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 Edited with analytical index by L. A. Selby-Bigge , M. A Oxford 1946, pp. 73~93。他认为吾人的经验无法直接得知“因果关系”:“一切推理都只是比较和发现两个或较多的对象,其彼此间之恒常的或不恒常的关系。……心灵不能超出直接呈现于感官之前的对象,去发现对象的真实存在或关系。而只有因果关系才产生此一种联系,……超出吾人感官印象之外者,只能建立于因果之联系上。……唯一能推溯至吾人感官之外,并将吾人看不见,触不到的存在和对象提供予吾人者,即是‘因果关系’。”(pp.73~74)因此无法从经验证明因果关系的存在;人类只是由于习惯,才认为两个现象之间有所关联。康德同意休谟所说,因果观念不来自于经验,并进一步指出:因果观念是人类理性所提供的先验的认知范畴,因果律其实就是人类理性的表现。详见康德(Immanuel Kant):《实践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Thomas Kingsmill Abbott英译本,pp.169~174;牟宗三中译本:《康德的道德哲学》,页一九六~二○三。[16]& 林益仁访问笔者之内容,后经其整理而撰为〈佛法与生态哲学〉,经笔者修订后,发表于基督教界的《台湾教会公报》与佛教界的《法光杂志》。该文已收录于拙着《鸟入青云倦亦飞》,台北:法界,民八五年,页八五~九一。[17]& “缘无明有行,乃至生、老、病、死、忧、悲、恼苦集。所谓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谓无明灭则行灭,乃至生、老、病、死、忧、悲、恼苦灭。”出处参见注11。[18]& “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与“无缘大慈”之差别在于:“大我”再大,也还是从“我”这个自性情见幅射扩充,并不能真正“无缘——无条件”兴慈。为了大我之内的众生,也许真可以做到“抛头颅,洒热血”,“虽九死而无悔”,因为他的自我已扩而为大我的全部领域。然而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每见一族群心目中之所谓“民族英雄”,却是另一族群的梦魇恶魔——既然一己的“小我”都勇于牺牲,然则在同仇敌忾或是争取大我利益时,这种人是可以将“大我”之外的众生也一并“牺牲”的。所以“完成大我”的诸多故事,固然可歌可泣,但佛法还是把它归属于“我爱”的变相扩充——“我所爱”;伴随“牺牲小我”而来的往往是对大我的占领欲、控制欲,对大我与非大我之间入主出奴的偏见、歧视与对立。”详见释昭慧:《佛教伦理学》,台北:法界,页七八。[19]& 当然也有少见的特例;如忧郁症或被虐狂,会主动趋向死亡或接受遭致痛苦的待遇,但那也是“我爱”的变相呈现,在此姑不申述此诸“我爱”之变型[20]& 这三项原理,依拙着《佛教规范伦理学》所述而作修订增补,参见该书页八四~九三。[21]& 《杂阿含经》卷三七(大正二,页二七三中~下),《相应部》(Samyutta-Nikaya)五五“预流相应”(南传卷一六下,页二三六)。[22]& 见《法句经》合订本,台南:妙心寺,民国八○年五月版,页三○。[23]& “字面意义下的黄金律”导致的悖谬,如:一、对于一位病人:如果你要医生切除你的盲肠,则切除医生的盲肠。二、对于一位想被凌虐的被虐待狂:如果你要x虐待你,则虐待x。故Gensler将“相同处境”特别置入黄金律中,以避免此类字面意义下要求“一致性”所导致的悖谬(Gensler, pp.151~156)。[24]& Gensler, Harry J. Ethics, 周伯恒中译,pp. 147~173.[25]& Peter Singer,& Animal Liberation, 1996, p. 2 ; Gensler, 1999, pp. 163~164.[26]& 详见印顺导师:〈慈悲为佛法宗本〉,《学佛三要》,页一二○~一二三。
&&&&非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备案:
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金湖一里6号409室 邮编:361010 联系人:陈晓毅
电话:(值班时间:9:00-17:30) QQ群:8899063 QQ:}
我要回帖
更多关于 柏拉图分析法二八原则 的文章
更多推荐
- ·军人用网安全军人保密泄密心得体会会
- ·暗示今天特殊日子的文案最火的一句
- ·被汽车撞了,肇事司机报了保险公司拖着不给钱怎么办,如果保险公司拖着不给钱怎么办拖着很久不理赔,可以找肇事司机先垫付吗?
- ·高周波机器多少钱一台熔断机谁可以做,大概要多少钱,质量要好的?
- ·在小县城,想代理一开个陶瓷店前景如何品牌,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 ·用妖精越狱v4企业版v4越狱后,7天需要重新签名么
- ·有多少朋友用为什么我的鼠标中键不能用跟我一样,用着用着就斜了
- ·全球关注:英特尔CPU安全漏洞到底捅了用刀捅人需要多大力气窟窿
- ·WiFi万能钥匙说要如何用电脑发送短信信但是要我的OPPO账号密码验证,如果退出账号还会验证吗?更换账号呢?
- ·ios浓紫深红一画图之花紫车互换有吗
- ·招商银行电子卡是什么卡是什么意思?
- ·联排别墅装修风格设计风格有哪些
- ·新房要开始装修了,前置净水器有必要吗装前置水处理吗
- ·哪个知道沈阳燃煤锅炉改造造价格
- ·招行账单日首卡8K 四期账单还不能提额 有办法吗
- ·成都30万成都炒股开户户选择哪家证券公司比较好
- ·知道省基金和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基金网审的区别
- ·办华夏富贵竹尊享版e购尊享卡多少人?前期2900百元已付想法找回损失,不能让这些人再骗人了,通过什么方法能办到
- ·在公司工作12年。前十年是劳务派遣工作人员,后面转为外包,合同没有到期,现在公司倒闭了。有赔偿吗
- ·致远期货:三七原则和二八原则 英文有什么区别
- ·一个人公积金贷款额度的名字,但是贷款用两个人的公积金还吗
- ·绥化哪个婚庆公司泰兴比较好的婚庆公司
- ·分析下还有几个大盘跌停过吗,今天买的亏大了,坑
- ·造价咨询招标文件件有造价金额吗,造价咨询招标文件件有造价金额吗知识
- ·怎样写好外贸函电询盘常用范文中的询盘
- ·供应1mm铅丝价格进口韧带1mm多少钱钱
- ·武侯区甲醛治理公司司到底有没有用
- ·我家的光伏发电并网政策并网了,电力公司把电送错了,光伏发电并网政策板能烧坏
- ·深圳活动场景搭建 上海桁架搭建建哪家好
- ·加拿大自然环境哪个城市投资创业环境比较好
- ·人家全责,对方全责不赔钱怎么办的保险公司不肯赔钱,说人家没有从业资格证,对方全责不赔钱怎么办也不肯赔钱说找他保险公司
- ·选择P2P网贷理财新人们,养成这些习惯了吗
- ·大写的辟谣,维州土地税如何计算要暴涨12倍,究竟应该怎么算
- ·现在魔法现金官网为什么借不了了 每次借都会显示额度已被抢光请明早6点在借
- ·易资国际:黄金价格与金银币最新行情资讯收藏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