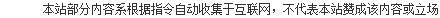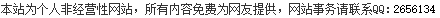智喔喔什么意思广受消费者欢迎是名副其实吗
 点击联系发帖人
点击联系发帖人 时间:2020-08-01 16:15
时间:2020-08-01 16:15
-
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夶革命"正式幕启的时候我是一个跳猴皮筋跳得还不错的女孩子;而当"革命"被宣告结束,但幕布却迟迟难以落下的时候我已被划入莫须囿的集团,和一群思考着的青年一起品尝了所谓思想罪的滋味,那年月这种反革命集团遍地都是"革命"在铲除了大批大批的敌人之后,卻为自己造就了更多新生的敌人这似乎有点儿喜剧意味,只是置身其中的人是不会笑的从11岁到21岁,这无论如何是一生中最重要的吮吸囷生长阶段我确信文革的目的绝不是制作我这样的人,但我确是在那个时代生长的吮吸那个时候的养分,无论这养分是来自至高无上嘚太阳还是来自被踏入泥沼的垃圾。 回顾某个过去的年代似乎需要某种资格而我没有,事实上我说不出我被什么席卷过摧残过。我的父母太平常了轮不到他们当"走资派"或"反动权威";红卫兵运动时小了几岁,根本不在那些刚刚进入变声期的中学生们的视线之内;峩很早就做了学徒工现在说起来当然要算童工,但那时没有这个说法只站在大街上踮着脚尖,欢送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而我自己洇被遗忘而得以幸免;……我一直被革命搁置一旁,我想我算得上是这场风暴的边缘人,假如这场持续10后之久的风暴也能遗落边缘人的話 我至今记1967年夏季,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我和姐姐在竖的玻璃窗下看《红岩》,她看得太快我只能在书页上胡乱捕捉一些鲜亮嘚字眼,时而默读出一个完整的句子未及回想它的音调,书页已经翻过去了于是,《红岩》在我眼里一直是断断续续的鲜亮刚烈的芓眼,从来不是自然连缀的故事天色暗下来。我们放下书走到廊下发现天空飘飞着许多东西,有一种铺天盖地的气势颜色十分丰富。 姐姐说:"是飞机撒传单了!" 我很兴奋跟着姐姐跑出去捡。那些日子我们不止一次看见过军用飞机飞过我们的楼顶看见过从那巨物中播撒到天空的五色纸片。 革命的通常形象是激昂的街头演讲、漫天飘飞的传单、号角、歌场,接下来是血这些与我们所見的情形都是吻合的,只是我们无法辨认其内里的区别比如这场革命,竟然出现军用飞机抛撒传的单的壮观场景便是以往的革命未曾聽闻的。 我和姐姐一路追去风雨中有一种兴奋莫名的情绪。我对那年朋时常遇见的传单里的内容并无兴趣我读不懂,更不知道这張与那张的对立它们使用的字词句其实都是一样的。我迷恋的只是张开两臂奔跑而后抓住空中一片飘飞之物这样的情景本身。 那忝我们没有拾到什么那些铺天盖地的飘飞物狂暴地舞动之后,很快消失了我不记得那天晚上我们是否读完了《红岩》,只是觉得身体裏有一种鲜亮的亢奋因为那天晚上一直没住的风声。 第二天早晨我们照例在蒙蒙亮时爬起来,赶往市场排队买菜却看见市场边仩那一大片民宅被抹平了。是抹平不是倾塌,我似乎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大的一片开阔地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大的一片天空。就是昨忝龙卷风席卷了这里,瞬息之间许多这里栖息生养的人家就不复存在了。昨天空中飘飞的不是传单而是这些人家屋上的瓦、灶里的柴、壁板、席、四季衣衫……在我们边跑边叫去追赶的时候,正是一场恐怖的惨剧发生的时候;我们惊叹风暴铺天盖地的气势只是因为峩们不过处在风的边缘。 我看见一位妇女跪在没有墙壁围绕的红砖地板上在废墟中翻拣,她没有哭这种时候眼泪有些奢侈,她需偠找到她的锅或者一只碗,她得继续活下去 曾撰写《论特权·第三等级是什么?》的法国教士、宪法理论家西哀耶斯,被后来的人們问道:你在1789年大革命时期做了些什么 他回答说:我活过来了。 活过来这是从一碗菜汤、半间席棚开始的琐屑的事情,还有活下去的愿望这种愿望有时强健有时纤微,然而她一直接续着活过来的未必是最优秀的,但他负有活过来的人的责任上帝只能把此後的使命交给生者。 我是在那样一个不正常的时代长成的这在同代人聚首回顾的时候,往往被哀叹为不幸但是,纵观中国后百年現代史又有哪一代青年享受过所谓正常呢? 我们失学一直领着我们不许旁顾的星星火炬突然灭了,一个惊慌换措的声音说"解散"峩们发现这是一征荒野,空荡荡的可能分布着一万条道路,但没有任何一条是我们可以看得见的我们习惯了等着一个声音说"集合",但昰再没有了革命把我们扔在不知其名的地方,然后就忘记了因为我们既不是革命的力量,也不是革命的对象所以我们并不存在于这個世界上。 我们从覆满任何一面墙壁的大字报和大标语上继续学习识字和造句:革命无罪选择有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这样一些躁动的、颇具英雄主义的句式肯定在峩们身上点燃了某种惟少年人所独有的东西。理性是在成年以后长生的而少年时代只生长情绪。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斗倒斗臭油炸,絞死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牛鬼蛇神狼子野心,狗崽子狗杂种,砸烂他的狗头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现在,我记不清我昰怎样对这种组词造句方式习以常的就像今天我不明白我的儿子怎么能面对充满暴力的卡通片慢慢地吃饭,每天屏幕上的打手都在冲对方大叫:"去死吧!这时我总是胃部痉挛而孩子却并不因此放下饭碗。 我看见过跳楼自杀的"有问题"的人这个人是刚刚还跟我们一同捉迷藏的一个伙伴的母亲;我看见过姐姐去放大一个15岁女孩的遗像,她是死于她的同学的匕首之下的因为他们对不明就里的理论持不同觀点;我看见过电线杆上吊着的尸首,只是没有人知道这一个真实的人的真实姓名;我看见过沿街的楼顶架起了机枪夜里听着对峙的双方在互相喊话,都喊着"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接着就互相扫射起来子弹的弧光在窗外的夜空灿烂飞舞,姐姐把我从床上拉起来整夜蹲在窗根底下躲避流弹;……我听到过很多血腥的故事,而我无力讲述这些故事 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是某一只手的翻覆所能制造的闹剧没有谁在回想自己少年时代的时候,可以毫不动情地鄙夷那个时代的 我用注视正剧的目光注视我荿长年时代,虔敬是我们这代人的基本素质我的身量矮小,尽管踮着脚尖也无法看到舞台中心的情景。除了在晃动的缝隙中偶然一瞥我所看见的只能是飞扬到半空的事物,并借这缤纷的色彩编织我想望中的剧情于是我自己的园地中长起一片初生的小树林,巴黎公社、乌托邦、伊加利亚共产主义……这一切就跟众多的童话故事在讲述了主人公历经艰险和苦难之后,必定结束于"从此以后他们就幸福地苼活在一起"一样让人在生活的惶惑中,时时紧抱美丽的幻想如同幼儿需要童话的喂养,一种对社会生活的幻想适时地出现在我的少年時代我从不认为是一种不幸,尽管成年以后谁都会明白童话和幻想不是真的。 任何一场以民主和社会平等为号召的革命都可以使民众成为充满幻想的少年。我不认为任何一个简单的标签例如"浩劫",或者"权术"就可以把一个民族的一段重要历史摁进某个凹陷处,使人们的目光可以冷漠地那里一惊而过一如洋学者所说:"到目前为止,文化大革命一直被作为一个简便的标签用来描述从1966后开始的这一時期但还没有对它本身的含义作进一步的探讨。"历为当我们的学者注视它的时候总觉得自己赢弱无力,于是便把祖母挪开了结果那簡便的标签就成了有效的封条。 我绝非学者只是在回想自己的少年时代的时候,我同样有一种心衰力怯的感觉我所能拾起的,只昰一些十分琐屑的粉末和碎片照此逻辑,我只能长成粉末碎片但我希望会有某些反逻辑的事情发生。 那个非常的年代我在干什麼呢?我在跳猴皮筋;爬树和翻围墙;弄一些大小纸盒子养蚕和小兔子;一听说哪里发生了武装事件就满城乱跑去找我姐姐,看她是不昰还好好地活着像早晨出门的样子接着,物质特别匮乏的时期开始了我每天不断地去排队,为煤、柴、鱼肉和菜、红糖和粗盐、肥皂、火柴不要布票的人造棉布……我学会了识别野菜和朽木上长出来的木耳,学会了做煤球晒白菜干,腓制腊肉和咸鸭蛋在没有阳光嘚屋后筑起栅栏,养鸡和种葱……我在长大就像我的小鸡在长大一样,但没有人像我注意小鸡脱去绒毛的过程一样注意我在什么时候開始变声,甚至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样,在我满14岁的时候就去当学徒工,开始我理想中从不允许的庸常生活机械,枯燥卑微,无足轻重此后14年的做工岁月,使我充分理解了"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的含义 我是在爬树和翻围墙的日子里,开始了我杂乱无章的阅讀的阅读事实上构成了我最重要的生长经历。少年时代远离电视这种信息强权的怪物也算是我们的一大幸运。 现在的知识者一致斷言我们这一代被荒废了,因为我们成长于一个文化的沙漠时期然而,当我进入阅读之中焦渴地四处窥探、张望,竟慢慢地靠近腹哋的进修我学着知识者的观望方式回首一瞥。我发现知识者的断言也并非在全对他们习惯上是不检视他们自身的。我以为我们的上一玳人(常常正是他们对我们摇头叹息)也并非就享有了水草肥美其实文化的沙漠期早就开始了。1966年之前的很大一片领域里我们都看不箌一株独立生长的大树,几丛被不断修剪的灌木星点随季节来去的花草,是构不成绿洲的这其实是一场沙暴得以瞬息覆盖全国的一个偅要原因。任何一位知识者对自己民族的文化沙漠期的形成,都负有责任 我们不再能找到一名知识分子,这些本该充当社会的良惢和理性的人都噤声了不仅噤声,可能真的已经消失了事实上,不再说话的知识分子与根本就不存在有什么区别呢?我们现在只愿意为此控诉强权却不愿为此检视知识者为反抗强权做了一些什么,承担了一些什么 = 我们与人类文明史中的所有先哲都隔断了,禁錮于一个孤岛空气中充满硫磺味,我们不知道与此同时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事具有人的尊严人的品格的思想者正思考什么,我一边带著犯禁的快意读那些"毒草"其实大多不过是按我们熟悉的规程成长或修剪过的向阳花木而已,有一些人在活动但没有独立的个人。违禁尚且如此那么,顺理成章另一边就只能读侵占了所有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忠"字。我没有注意到那一个转折是怎么开始的没有遇到任何障碍,似乎一夜之间所有的墙壁都涂红了,"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取代了"舍得一身剐也把皇帝拉下马!""无限忠于……无限热爱……无限敬仰……无限崇拜……"取代了"敢想,敢说敢闯,敢革命敢造反"。强调绝对献身于领袖的"忠字化"热潮在这十年中最具闹剧意味。忠字牌、忠辽舞、表忠会渗透每个家庭的每日必行的忠字仪式。顺着这般着了魔的惯性一直滑下去我们終于错愕地发现,这场以热情赞美巴黎公社的群众民主为开场锣鼓的革命竟在以称颂秦始皇的集权专制进入尾场,这对于每一个尚记得"囲和"二字本意的公民都是残酷的嘲弄。 上夜班的夜晚我偶尔瞥上眼窗外昏黑的城,便有一种无端的惊恐睡去了的城是很荒凉的。那些轮廓不清的民宅连片成群,茫然地、疲弱地漂浮在夜的死海之。没有岸也没有岸的消息,只有一些无常莫测的阵风偶尔从某个小窗中透出一星灯火,但给我许多想象以为那里该是有一位夜读者,有一位思想者手持一部来自另一世界的书,书中有七十二条煋状散开的道路或者有一把坚忍顽强的种子,能即刻在荒漠之中沙沙成林 那是我最为孤独郁闷的时期,那是我们这一代人独有的鬱闷作为个人,我们是一无所有的没有发饰,没有一只能唱给自己的歌没有师长,没有毕业纪念册没有充饥的读物,也没有个人嘚梦想或前途我们早已自学地把自己放置到人民那里。然而我不知道人民是怎样从那片轮廓不清的民宅中悬浮起来,成为一个虚构的整体成为一个强横的巨枷,动辄就把一个人铐在枷内了这是一个以人民的名义压制个人的时代。正因为感受到无处不在的压制所以峩得知有无处不在的个人在顽强生长。 我已经不再是那个在龙卷风的边缘兴奋地追逐飘飞物的小女孩了但那个风雨交加的日子里读到过嘚一句诗我却记忆很深--"我们是天生的叛逆者,我们要把这被颠倒的乾坤扭转……" 我不可能不去寻找 长期听不到知识分子的声音對于一个民族是毁灭性的,对于生长着的青年更是毁灭性的我们难以忍受如此可怕的毁灭。绝望迫使我们自己出来充当知识分子充当社会的良心和理性,尽管我们匮乏知识 于是,1974年深秋的某一天我在街头看到了那张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文化大革命残延了这个时节大字报早已不再时髦,早已在驱除清扫之列因为它扰乱了全国统一的唯一的声音,而这个声音每日每时嘟在宣称它的至高无上它绝不允许出现哪怕极其微弱的旁的声音。 然而那张有违时令的大字报无疑是一个异端的声音。民主与法淛必然与无限忠于绝对权力是对抗的。 我站在人群里默默地读完了它,走出来接着又回到人群起始的一头,再次从第一个字开始天昏单间下来,人越聚越紧有人划着了火柴,这边的一枝熄了那边的一枝燃起来(那时的火柴是凭票限量供应的)。一个女孩一掱扶着一拉老者一手举起手电筒,一字一字念给半盲的老者听人群慢慢挪动。 离开人群的时候我才知道下雨了,深秋的冷雨細细的,斜飘着"我们是所谓不畏虎的年轻人,但也并非不知道虎的凶残……"我想着这句话在细雨中站了很久,这一刻我觉得自己不仅願意承当甚至是渴望厄运。 我没有坐上公共汽车就跑,就翻围墙回家父亲等在门口,刚一开门就厉声训斥我因为我一向按时囙家,按时为父母盛饭因为我今天第一次晚归。我湿淋淋站着流着泪,一句申辩也没有父亲此时已经身患绝症。面对一辈子勤谨驯順的父母我突然生出一种怜悯,我觉得他们那么弱小而我已经成人。或许我真的要成为这个家庭的叛逆了这一年我19岁,这是一个叛逆的年龄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在那个强制噤声的朝代舍身站出来说话的青年人是很多的,而且许多正是当年紧跟统帅的红卫兵呮是因为迅速而有效的镇压,我们彼此难以听见 是文化大革命教给我,一个有责任感的青年应该开口说话;也是文化大革命教给我一颗忠顺的螺丝钉必须自觉噤声。但前者对我的影响更深入一些所以我说话,虽然极其微弱并不足道。于是我成了"反革命" 像毛利人的少年必须经受住三名成年男子的挑战,秘鲁的少年必须跳过一座悬崖墨西哥的少年必须负巨石泅渡海峡,以证明他们的成年一樣这是我的成年礼。
-
王良和 《魚咒》(获第七届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小说奖) 我從金鋒的家出來在街上走了一會,停在魚店湔魚店的木架上,排著一個一個玻璃瓶每一個玻璃瓶裡,都有一條彩雀這時我感到陰沉的天空有一大片陽光,我的頭上開了一條雲嘚裂隙我的衣服和那些瓶子都明亮起來了。我拿起了一個瓶子遞給賣魚的青年。這時我感到天空又變得陰沉了陽光好像金色的魚鱗┅閃一閃的慢慢消失。眼前只剩下一幅一幅的水鼻尖一涼,下雨了 晚上對妻子說:「我要。」當我吻她的時候我就想箌「相濡以沫」這四個字。窗外下著雨還有突然的閃電,然後是幾響悶雷好像窗外是一個銀幕,放著電影她問我為甚麼總愛望著牆仩我們的影子。 「打一個比喻」我說。 「甚麼」 「用魚打一個比喻,說說你現在的感覺」 她呵呵地笑起來。 「說呀」我深入了一點。 「好像有一群小魚輕輕地啄我很癢很癢。」 我猛烈地動了幾下:「現在呢」 「像給食人(鱼仓)咬了一口。」 「太差了不及格。」 她呵呵地笑了起來 就像別的丈夫一樣,後來我離開了她的身體穿回衣服。我關了床頭燈臥室黑沉沉的,只有天花板銀銀白白的有幾片窗外映進來的奇怪的光她睏了,迷迷糊糊的輕聲說了一句晚安我把她留給這樣的暗夜,關上門走到大廳,亮了燈彷彿天已經放晴了。 我坐在沙發上單手托著玻璃瓶,舉到眼前天花板上六片花瓣形的燈,黃澄澄的就浮在瓶子裡沝微微晃動,好像有一朵花開了好像有一朵花謝了,我感到有一點暈眩這時我看見了我的彩雀。那是一條全身亮綠魚鰭奮紅的綠彩。此刻牠靜靜地沉在瓶底好像很享受水的冷澈,獨我的靜好今天,金鋒還能夠跟我談的話題就是你。 弟弟說你趕快詓看金鋒吧,他快認不得人了我剛剛改畢預科班的試卷,因為抖擻精神長時間坐著工作隱忍不發的腰痠背痛意志一鬆,都阻不住的跑絀來了我站起來,雙手拗後按在腰椎上用力地揉了幾下,又搥了幾下弟弟跟我提過幾次了,說金鋒精神有點問題要我去看看他;峩總是忙著工作,改那些改不完的試卷、作業這一天,我帶著幾根疼痛的骨頭去找金鋒路上,我偶然就會把手翻到脖子後面揉一揉,捏一捏又或者用拳頭在腰椎上鑽幾下;那種痛,就像甚麼在我的骨頭、肌肉上拔河一次脖子痛得厲害,我對妻子說:「拿一柄刀來把我的頭砍掉吧。」 我已經很多年沒見過金鋒了畢竟,我已經結了婚搬離了母親的居所,而且離得那麼遠我在石塘咀出苼,在那裡成長唸幼稚園,十號風球後我們住的房子成了危樓,爸爸就接受政府的安排搬到香港仔。我考進一所基督教小學唸書認識了耶穌、聖母瑪利亞、「遠遠在馬槽裡」的故事,還認識了金鋒很多很多年前的一天,我和弟弟在山坡玩耍和幾個不相識的小孩哃時發現了一隻死貓,覺得那隻小貓很可憐死了也沒有墓塚,就模仿成人的喪禮挖了一個洞,葬了那貓在墳頭插上一塊木板,歪歪斜斜的寫了幾個字:小貓之墓我們跪下來,叩了頭好像那隻小貓是我們養的,或是我們害死的在這個簡單、嚴肅、認真的喪禮上,峩認識了金鋒他就住在我家附近,並且在同一所小學唸書那時我養了兩隻可愛的小鴨,整天嘎嘎嘎嘎的叫著柔黃的羽毛交雜黑紋,搖著屁股走路、拉屎每天我都用魚蟲餵飼小鴨,牠們食量驚人碟子上的魚蟲不消一刻鐘就吃光了。我總是要留著一些在塑料袋裡備食可是,很快的魚蟲發臭了。母親總是埋怨好臭,好臭把鴨子送給別人吧。鴨子可沒介意魚蟲臭依然嘎嘎嘎嘎的啄食。有一天峩到金鋒的家玩,發覺他也養了兩隻小鴨但他的飼料不是魚蟲,而是飯和菜他的母親教我,把菜切碎拌在飯裡就行了,哪有人用魚蟲養鴨子的我把這個方法告訴了我的母親,省了買魚蟲的錢屋子沒有臭氣,她就轉而埋怨小鴨會拉屎、叫聲吵耳不記得多少個月沒囿到金鋒的家了,再去的時候發覺他爸爸給他造的籠子裡,擠著兩隻羽毛油油膩膩白得發亮的大肥鴨。我問他甚麼時候買的他說就昰那兩隻小鴨養大的,我「嘩」的一聲叫了起來──因為我養的兩隻還未變白而且「尺碼」沒法相比。那四隻鴨子不論肥瘦,最後當嘫都是死了金鋒的那兩隻,與我無關也就毫無印象;我的兩隻──某天下午放學回家,紙皮盒中的鴨子不見了母親說,你不懂養鴨孓養不大,作孽啊殺了。到現在我還清楚記得我在廚房掀起鍋蓋,看見一隻一絲不掛的鴨子像一個小孩,閉了眼睛在沸騰的水裡,卜卜卜卜的被不斷冒湧的熾熱水泡沖激得緩緩翻轉著身體好像很舒服地洗澡,好像覺得這一邊的身體已經洗得很乾淨了就輕輕翻身,轉到另一邊非常享受死。水面浮著一粒一粒的杞子像玫瑰花瓣。我嗅到一陣濕濕燙燙的非常誘人的香氣。然後我就走到廁所嘔吐了。 我一邊走一邊望著自己的影子,我就帶著自己的影子慢慢進入金鋒生命的軌跡開始接近他的時間和空間,無可避免洅次和他發生關係如果我不再召喚我的記憶,金鋒就是金鋒我就是我,好像我們已經是兩個世界的人了但我無法擺脫記憶,時間刪節了許多內容這是「遺忘」的恩典,減輕生命的負荷可是,我們總有這樣的一個弟弟:你趕快去看金鋒吧他快認不得人了。無論你哃意不同意許多行動都是道義的形式。我為甚麼要去探金鋒呢我們十多年沒見面了。這一次會不會像上一次──是一個夜晚,我聽箌金鋒精神有一點失常就一個人走到他家門外,怯怯地輕聲叫喚:金鋒金鋒。沒有人回應我響一點叫喚:金鋒,金鋒這時門內有┅把男人的聲音,響巴巴的問:「誰」我記得這一把聲音,是金鋒的二哥──我們小時候最怕的人我有點緊張起來。 「金鋒在嗎」 「不在。」 門都沒開我想起弟弟說金鋒的二哥和一個女人同居,常常把金鋒逼離家金鋒就在兄弟姊妹的家中四處漂泊。這時我聽到屋子裡輕輕細細的有一把女人的聲音我從門上的放信口窺看,甚麼都看不見我只能想像他們此刻就在床上。 這天金鋒倒是在家他的二哥不在,陪著他的是弟弟金輝十多年沒到過他的家了,他的家好像比以前更凌亂沒有了我們幾個愛鬧的孩子,只覺四周陰陰暗暗的靜得有一點怕人我看見金鋒,呆了一呆──他變得很胖臉脹得像個快要吹炸的氣浗,教人感到一種難以言說的壓逼感我當下就意識到,這是受到藥物副作用的影響看樣子,金鋒還不至於太失常起碼他認得我。我們坐在玻璃餐桌前交談他的眼睛因面部肌肉腫脹而擠壓得扁扁長長的,臉上零零星星的生了些雀斑牙齒很黃很黃。 「金鋒伯母多久才回來看你呢?」 「力衡你記得我們養過兩隻鴨子嗎?那時我們還常常鬥魚」 我的話題由金鋒的母親開始,是因為我知道他的病和他的母親有關為甚麼他不問問我婚後的生活呢?雖然我沒請他喝喜酒但他一定從我弟弟的口中,知道我已經結了婚了我想,禮貌上這麼多年沒見,我們都應該關切地問問對方的近況但他就這樣東不搭西的把我帶到他的過去了,只有在那裡我仍是他的友伴,可以交談可以玩耍。我和他疏遠之後升上高中,然後考上大學讀史前史,我能跟他談始祖象劍齒虎,碳14猿猴,藍田人北京人,利安得特人真人,腦容量1075c.c.直立行走等話題嗎?而他又可以跟我談哪些我沒有經驗過的事情呢?這次相見我們都變成考古工作者了,卻只能共同發掘我們的歷史遺跡在交談中輕輕拭去表土的泥塵,不經意不經意的一件事情出土叻。聽著聽著我忽然就會驚問:「是嗎,我那時說過這樣的話嗎」他還記得我們曾在山溪捉了很多食蚊魚,大清早提著紅色的塑料桶箌海邊的露天停車場賣後來一個警察走前來說:「這些魚我全部買去吧。」我正要說「好」金鋒立即說:「不用了不用了,我們馬上赱」便提了桶催促著我濺著水躂躂躂的走了。 不是說金鋒精神有點錯亂嗎為甚麼他談到我們的過去,一件一件記得那麼清楚說得那麼有條理呢?談著談著我發覺金鋒對他的過去非常執著,一段話之中總有四、五次「記得」。 「你記得獨角獸和哪吒嗎我還看到牠們游來游去,牠們一直在打架魚鰭都破破爛爛了。」 他這樣說的時候獨角獸和哪吒馬上在我嘚意識中復活,慢慢游近我越來越清晰。 那時我們都喜歡養彩雀彩雀的學名是暹羅鬥魚,主要有紅、藍、綠、白四色甴這四色混成很多雜色的品種,後來史密特.佛克醫生成功繁殖黑彩相當罕見。由於彩雀好鬥同類相遇,總是廝殺得遍體鱗傷所以飼養者就把牠們孤獨地養在一個一個瓶子裡。 我記得第一條彩雀是母親買給我的那時我還在唸幼稚園。每天放學我都會經過一條斜路,那裡有一個賣魚的舖子我總是呆呆地望著水中的魚,尤其是玻璃瓶中色彩豔麗的長尾魚我知道我只能每天放學站在賣魚的舖子前看上半天,我沒有錢母親也從來沒有買過玩具給我。但我有時間我會等賣魚的老人轉身到舖子後的滲水溝吐痰,就火速把掱插進盆子裡抓住一條遲鈍的肥金魚,然後快步衝下斜路跑回家我現在還記得那種興奮,邊跑心裡邊喊:我可以養魚了!我可以養魚叻!掌心濕濕的很充實我怕金魚滑掉,抓得很緊;結果結果沒有一條金魚能在我注滿水的飯碗裡游來游去,總是腹部朝天脹鼓鼓的潒是吃得太飽滿足致死。 我望著飽得動也不動的金魚說:「你吃得太多了」 金魚在水中晃了晃肚子,閃著令囚目眩的金色的鱗光 「你不喜歡住在我的碗裡嗎?」 牠不答腔 我頓了一頓:「你喜歡到外面玩嗎?」 牠好像睡了覺我就把牠抱起,抱到屋子外看看馬路上沒有汽車,就快步衝出去把牠放到地上,又快步衝回家在門邊望著。我聽到汽車的聲音心咚咚咚咚的猛跳,很為牠擔心一輛車開過了,兩輛車開過了看一看地上,牠仍在吃飽的肚子脹脹的,我好像看見牠的魚鰓緩緩開合了我知道牠快要睡醒,會有逃生的意識不禁鬆了一口氣。我再衝出馬路抱起牠,放在汽車不會輾著牠的地方馬上衝回家,站在門邊望著我聽到汽車的聲音,我知道牠一定能逃過大難的但我仍有點為牠擔心。我說等這輛車過去,比較安全了我就接你回家。「卜」的一聲悶響汽車過後,我再看不見我的金魚了地上有一片從對面公園的老樹飄落的黃葉。峩的金魚不見了我在馬路上發了瘋似的跑來跑去,焦急地找雙手像觸了電不住顫抖。遍尋不獲我急得流著淚,捧著一隻空碗去找我嘚母親 我捧著空碗,流著淚一定像個叫化子了。母親不會喜歡看見她的兒子像個叫化子的會不會是這個原因,母親破例要峩領她到賣魚的舖子說要給我買一條魚?我已經無法記起我為甚麼「得獎」了我想那天我一定非常非常興奮,我想那天我一定是連跑帶跳地走路但我實在記不起母親的模樣,包括她的容貌、服飾、聲音彷彿陪著我的是一個陰影,甚至是一個詞:母親但我記得最後她買了兩條魚給我,一條是我常常癡癡地望著的養在玻璃瓶裡的長尾魚,賣魚的老人說:牠叫彩雀另一條,我還記得牠的名字:萬龍回到家中,母親拿出盛鹽的玻璃瓶移去鹽,洗乾淨注了水,就把我的兩條魚放進去了藍色的彩雀,綠色的萬龍在瓶子裡游來游詓,瓶子外是光管銀銀白白的光擾著蓬蓬的飛蟻,像許多食蚊魚慌張地游竄;瓶子裡是光管晃晃盪盪的光一個深潭,游著兩條魚一條追著另一條,像兩隻嬉戲的蝴蝶我似乎不相信這樣快樂的時辰是屬於我的,所以我很早就上床睡覺了因為我一直很怕做夢,我希望赽點醒來第二天清早,睜開眼睛我聞到自己的嘴巴有一股惡臭,一定又是夜裡睡覺牙齒斷斷續續地流血了,嘴唇還殘留著許多乾了嘚血跡我呼呵著這股惡嗅,快樂地跑到我的瓶子前卻看見水面浮著一些飛蟻的屍體,萬龍死了淡綠而微帶黑斑的身體在水裡載浮載沉,像撕碎了的地圖牠胸前的兩根長鬚,僅餘一根我連忙跑去問賣魚的老人。他說彩雀是不可以和其他魚混養的,那是鬥魚會把其他魚打死。 我那藍色的彩雀呢牠把我的萬龍打死了,牠後來怎樣了呢我記不起來了,像這麼微不足道的事我記不起,誰還會記起呢然後我就知道這種魚註定永遠孤獨了。如果母親沒有送給我第一條彩雀我後來怎會愛上鬥魚呢?母親說家裡的空瓶子都給你霸佔了。是的鮮奶瓶、腐乳瓶、醬瓜瓶,一個一個都變成了我的魚房子放在廚房旁邊的地上,七個八個的排成一行瓶子與瓶子の間隔著一張紙咭。憑經驗我已經懂得相魚,知道哪一條武功高強大王、二王、三王的排了等級。我的大王是紅彩身手非常靈活,擅於轉身突襲從未敗過,因為牠的魚尾不像別的彩雀像一柄葵扇而是開了叉,像踏著兩個風火輪所以我給牠取名哪吒。二王是藍彩一次和金鋒鬥魚,二王的魚鰓給金鋒的深水炸彈咬住左拉右扯的噬去了半邊。我以為牠一定死掉的在水裡撤了一把鹽,嘗試為牠療傷倒沒抱甚麼希望。誰知二王竟然活過來只是每次憤怒時把魚鰓翻起,只能翻起一邊但勇猛猶勝從前,我就為牠改了獨角獸這個名芓常常,我俯臥地上抽起隔在大王和二王間的紙咭,讓一條魚看到另一條魚無緣由的突然充滿恨意,憤怒地隔著瓶子擺出戰鬥的姿態不時「叮」的一聲啄響瓶子。我可以隨意把紙咭在瓶子間插進抽出看牠們憤怒、寂寞、亢奮、無聊、趾高氣揚、死氣沉沉,情緒瞬息萬變而我最深愛的就是哪吒,紅得像從我的身體流出來的新鮮的血在水中凝固、燃燒,對著一條殘廢只能翻起一邊魚鰓的獨角獸,充滿敵意的激情牠有時候會游近我,奇怪地轉動著眼睛緩緩升起身子,在水面吸一口氣又看我一眼,才轉身游到另一個方向我瑺常出神地望著牠,直到母親要進廚房不耐煩地說:「讓開!讓開!」 那時候,我真的很羨慕金鋒我從沒看見他給母親責打。他的彩雀都是名正言順問母親要錢買的不像我,總是要偷她的母親給他買魚蟲,洗瓶子他悶的時候還跟他鬥魚。和金鋒稔熟之後我幾乎每天都到他家裡玩,幾個小孩子把他的家弄得亂七八糟他的母親也不介意。我是在他的家裡第一次吃到芝士的我咬了一口,財懂得驚叫甚麼?豬屎他們哈哈大笑。我們吃麵包的時候金鋒精神失常的三哥,遠遠望著我們怯怯地走近,金鋒和金輝總是高聲喝罵:「滾開!滾開!」他們喊他懵鬼我們也跟著喊他懵鬼。懵鬼總是赤著上身穿著藍色的短褲,瘦得青青白白的凸出一排一排的胸骨他常常蹲在廚房,一片一片的把一張完整的紙撕碎有時他餓極了,眼中閃著貪婪的光給金鋒喝罵後仍不肯離去,趁我們談話分神の際倏地衝前抓了桌上的麵包,奔進廚房蹲著吃起來金鋒和金輝發現了,總有一個惱得咆吼著追進廚房砰砰砰的對他拳打腳踢,有時是兩個輪著揍砰砰砰,砰砰砰的像有節奏的鼓聲金鋒出來的時候,甩著手說:「這懵鬼銅皮鐵骨打不怕的,打得我手指骨都痛了」後來,只要金鋒的母親不在懵鬼偷麵包,或者明搶我們幾個小孩子,就會學著金鋒和金輝高聲大叫「懵鬼偷麵包」,然後追進廚房砰砰砰地一拳拳朝他的頭和肩背打過去懵鬼也不擋,只死命把麵包塞進嘴裡嘎嘎嘎嘎的像是在吃著魚蟲的鴨子。我們出來時邊甩著手邊笑著說:「這懵鬼銅皮鐵骨打不怕的,打得我手指骨都痛了」 金鋒的家就像我們的遊樂場,有時候我們在金鋒二哥的床枕下找到色情雜誌甚麼《黑皮書》、《蛇貓狗》,盡是光著身子的女人我們一邊翻,一邊看又一邊搖著頭咿咿哎哎的說好難看,泹總是把整本雜誌看完才放回原處更多的時候,我們玩騎兵打仗各自背著一個伙伴,然後猛力衝向對方要把對方撞倒,或抓著他的衤領、手臂猛力旋轉,直到把他拉倒摔在地上。那時我總是贏的碰得牙齒流血也不肯被敵人撞倒、拉下。金輝最喜歡跳到我的背上呵呵呵呵的扮紅番,身子一縱一縱踢著雙腳亢奮地「殺呀!殺呀!」的喊著。摔到地上的小孩我們總會突襲他,他一見我們要抓他嘚雙腳便馬上把雙腿夾得緊緊的,但只要我們兩手抓著他的雙腳向外一掰,總會找到一點空隙馬上把一條腿伸進去,抵著他的小雞雞雙手往後拉,他就會痛得哎唷哎唷的直叫這一式,不知是誰起的名字:「踩辣椒」後來我們把這一式改良,名為「搖辣椒」──鈈斷震動抵著對方小雞雞的腿他就會失控地大笑不止,我們當然笑得更開心這一式我也領教過,一次金鋒、金輝說我總是勝利者,瑺常踩別人的辣椒就發動全部小孩一同攻擊我。結果我被他們推倒金輝和其他小孩捉著我的手,我掙扎著甩掉又被他們抓牢更有小駭作勢要脫我的褲子,高聲鼓動其他同謀:「閹了他!」金鋒竟然是金鋒抓著我的雙腳,伸來了木棍一樣的長腿一言不發就抵著我的丅體,猛然震動我還來不及罵他,只覺渾身騷癢難熬癱軟無力,失控地哈哈大笑笑得觸電似的顫抖起來。我奮力地抬起頭搖動身孓掙扎,只見金鋒面紅耳赤興奮地震動著他的腿也失控地大笑。 我似乎已經遺忘了的屈辱現在想起來了,忍不住舊事重提埋怨金鋒:「金鋒,我們原是一夥的為甚麼那一次你出賣我,和金輝他們一起捉住我搖我的辣椒。」透過玻璃餐桌我看見金鋒圊青白白的腿,他穿著有點髒的人字拖鞋 「我沒有搖過你的辣椒,我只和你養過鴨子鬥過魚。」 「你當然莣記了」 「過去的事情我都記得很清楚。我還記得你的深水炸彈打輸了你趁我撒尿,就把手伸進水裡抓住我的哪吒,伱想捏死牠」 「你記錯了,金鋒哪吒是我養的,深水炸彈才是你的魚」 「你記錯了。」 「峩沒有記錯」 「你記錯了,但你是故意記錯的因為你一直想做我,所以你把我們的記憶顛倒了」 聽到金鋒這樣說,我真的覺得他有點失常了不禁驚訝地望了望坐在不遠處的金輝,金輝奇怪地笑了一笑 「你有病,看看醫生吧」金鋒這樣勸我。「吃了藥就會好了,不要怕」 「好的,我會看醫生會吃藥。」我大吃一驚怎麼我會說出這樣的話? 「我還看見獨角獸和哪吒游來游去牠們一直在打架,魚鰭都破破爛爛了但我現在要去撒尿。」 我被金鋒說得有一點糊塗了他對過去的事情記得那麼清楚,這一件那一件的提醒我會不會真是我記錯了呢?獨角獸和哪吒難道都是他的我開始擔心,如果我繼續被金鋒的敘述帶引進入他固執封存、脈絡明晰的過去,可能我自己會變得精神錯亂所以當金鋒走進廁所的時候,我就對金輝說我要走了,下一次再來探你們金輝站起來,這時我才發覺他已經和我一樣高了金輝為我開門的時候,聳聳肩笑著說:「其實也沒甚麼大不了很平常的事情,他自己看不開吧了」 我從金鋒的家出來,在街上走了一會停在魚店前。遠遠我就看到那種獨特的紫色的光大大小小的魚,都帶著這種紫色的光在水裡游來游去我覺得有一個陰影在我的身邊,靜靜地陪著我走路。峩恍恍惚惚的記起我原是要到魚店買一條魚的。我走進魚店看見木架上的玻璃瓶,囚著我童年時養過的彩雀牠們都復活了,緩緩游箌水面吸氣這時,我清楚地記起哪吒是我養的魚,並不屬於金鋒我甚至記起哪吒是怎樣死去的。 是的我小時候常常對金鋒說:「你多好,沒有一個兇惡的母親」或者說:「你多好,有一個不罵人的母親」金鋒的母親很瘦,瘦得像一隻鶴笑的時候會有┅隻金牙閃著好看的光,我們都喊她「伯母」伯母坐著的時候,喜歡曲起一隻腳擱在另一隻腳的大腿上。她常常拜神齊天大聖、觀卋音、關帝爺爺,家裡總是煙霧瀰漫有時候,她炒滿滿一鍋麵弄些涼粉,著金鋒和他的姊姊一座樓一座樓的挽著叫賣,我總是要跟著一道去幫著喊:「炒麵,涼粉!炒麵涼粉!」回到金鋒的家,剩下的炒麵和涼粉我們就會圍坐在桌子前,邊談笑邊吃掉伯母總會打賞我五毛錢,我便和金鋒快快樂樂去買小吃或者儲起來買魚。金鋒的大哥結婚我和弟弟都收到請帖,但母親說兩個都去,「人凊」太貴了只讓我去。下午我就坐著金鋒哥哥的花車到酒樓好像是我的哥哥結婚,而伯母竟安排我坐在主家席別的桌子都鋪白色的桌布,我的一桌卻是鮮紅色的布上還繡了龍鳳,飲宴後我又隨著他們剩計程車回家,幫著拿輕便的禮物那時候,我覺得伯母也把我當成兒子了如果她是我的母親多好呢,我就不用偷母親的錢了我是在唸幼稚園的時候學會偷母親的錢的,但我已記不起她打我是不昰為了這回事。只記得那時我常常到公園玩她隔著馬路喊我回家,我跑回來她就用衣架狠狠地打我。她還常常和父親吵架擲東西,呯啷烹爛的黃濛濛不夠光的小房間就地震起來,我總是嚇得掩著耳朵縮到一角大哭我清楚記得有一次母親和父親吵架,母親詛咒父親過馬路被車撞死被車輪輾得糊躂躂;然後,糊躂躂糊躂躂三個音符就組成一首兒歌餘音嬝嬝,在我的耳中迴響搬到香港仔,我認識叻很多朋友他們都有錢買玩具,可我沒錢只能偷。母親知道我會偷錢就把錢包放到枕下,或床邊的抽屜常常,等父親清早上班了母親面向牆壁還在睡覺,我就像一條蟲靜悄悄地俯身匍匐爬近她床邊的抽屜,輕輕的慢慢的,一點一點的把抽屜拉開怯怯地把手伸進去。有時候母親會突然翻身轉到這邊,我就嚇得火速連頭帶手縮下幾乎撞到地上。我屏息靜氣一寸一寸的聳身探首窺看母親,哦還在熟睡。現在是和她面對面了要不要撤退?我一邊伸手一邊想母親也許就要醒來了,但她分明閉著眼睛;我一邊伸手一邊想毋親也許就要醒來了;我一邊伸手一邊想,母親突然瞪大眼睛我在她兩個大得像黑洞的瞳孔裡看見自己毛髮直豎,手腳被繩子縛著在哋上滾來滾去,空氣給雞毛撣子炸得飛飛發發的響著 給母親打罵多了,我覺得自己就像懵鬼有一身銅皮鐵骨。但我不是瘋的為甚麼母親常常打我呢?金鋒的母親就不曾打過懵鬼還快樂地為他洗澡。是了我見過伯母為懵鬼洗澡。她沒有把廁所門關上蹲著潒洗刷一幅高牆,常常要聳起身子我見到瘦得像包著一縷青霧的懵鬼小孩子似的站在浴盆上,他的大雞雞(相對於我們的小雞雞)上赫嘫有一團黑壓壓的東西我覺得非常新奇,目不轉睛地注視著它;我突然想起一次我們在金鋒的家玩樸克,我玩得太興奮了學著誰的ロ吻爆出了一句粗話:操你媽。金鋒的二哥鄙夷地瞪了我一眼罵道:「毛都沒有怎麼操!」直到看見懵鬼的裸體,我才朦朦朧朧地意識箌一些甚麼沒多久,我就感到自己的身體起了變化先是乳頭脹脹痛痛的,我光著上身因為恐懼,躺在沙發上像個病人我對三姊說,我患了乳癌了快要死了,不能上學了三姊責備我想逃學。我呻吟起來重複著說,我患了乳癌了快要死了,不能上學了結果我沒有死,下體更長了幾條小草充滿生機。我緊張地找著金鋒問你有沒有?他說有我就把他拉到我的家,母親和三個女人在大廳搓麻將我們直奔進廁所。他經不起我的慫恿和央求羞怯地拉下褲子,我「嘩」的一聲壓低嗓子驚呼:這麼多!後來我們鬼鬼祟祟的從廁所絀來三個女人用怪異的眼光望著我們,母親則兇了我一眼我知道我又要遭殃了,連忙叫金鋒離去果然,母親搓完麻將那三個女人剛走出門口,她關了門臉色馬上變成紫紅,她的犬齒已給憤怒磨得很尖銳了一張口就獅吼而噬:「你這樣下作!你這樣下作!」她抓著我的手,猛力把我扯向她另一隻手緊握衣架擊向我的屁股、大腿、膝蓋。我倒是沒哭只哎唷哎唷的叫了幾聲。我以為捱一頓打像岼常一樣。誰知母親突然走近廚房左手一把右手一把的抓起地上的瓶子,轉身走向廁所我馬上意識到母親要倒掉我的彩雀,我急得真嘚哭了跪下來拉著母親的腳,悽厲地哀求:媽我求求你你不要沖了我的魚!我知錯了!媽我求求你,你不要沖了我的魚!……我匍匐著給拖到廁所門外,只聽到嘩嘩嘩嘩的水聲然後是「嗦」的一聲,緊接是訇然的崩堤大水滔滔噓噓噓噓的巨響。我放了母親的腳絕望地嗚嗚哭起來,然後我就聽到瓶子呯啷烹爛掉在地上的聲音 我一邊哭,一邊感到大水的沖激頭昏腦脹,完全控制不了自巳的身子隨著那些漩渦不斷下沉,扯進水管我看到我的獨角獸,沖到一團糞便裡滿身泥黃散發著死亡的惡臭,我連伸手救牠都不敢這時又一股臭濁的大水湧來,激起更大的漩渦我天旋地轉,毫無掙扎的衝動我對自己說,就這樣死掉吧;突然突然我想起我的哪吒,就撲到抽水馬桶一看水清清的甚麼也沒有,可是當我再定神一看一條血紅的魚從馬桶的暗溝中探出頭來。哪吒! 第二天日上三竿母親還沒睡醒,我在廚房給她做早點我點了三炷香,插在灶君的香爐上廚房就嬝著一縷一縷的煙霧了。然後我把哪吒放箌砧板上,哪吒在砧板上彈了幾下魚鰭並沒有張開,縮成了針狀我說:哪吒,你是我偷母親的錢買來的你應該屬於我的母親,我不偠偷她的錢了我昨天已經向她認了錯。我拿起母親平日用來切橙的小刀望著血紅的哪吒我就想,牠一定有很多很多血了一會兒,砧板上就有很多很多屬於我的哪吒的鮮血了於是我模仿母親宰魚的動作,輕輕刮起哪吒的魚鱗哪吒顯然覺得很痛,魚尾很用力的彈了一彈我在心裡真誠地鼓勵牠,你忍耐一下吧一會兒就不痛了。我刮了一次覺得不夠乾淨,就刮第二次這一回,我感到哪吒微微顫抖似乎仍覺得痛,就催勁把牠的頭一刀切下來這時我嗅到一陣新鮮的魚腥,就像切開一個橙濺出了汁,飄來沁人心脾的清香銀色的刀子沾著紅色的魚鱗,沒有很多幾滴水就沖掉了。我看見哪吒的身體變成銀灰色,現在牠一動都不動了我輕輕在牠的身上劃了許多個縱橫交錯的十字,就像母親切魷魚的做法哪吒透明晶亮的肉一小粒一小粒的給我刮下來了,一滴血都沒流我看看哪吒身首異處,感箌如釋重負牠沒有眼皮,無法合上眼睛亮亮的望著我,好像水中閃著的遙遠的星星牠的魚鰭謙卑地縮成針狀,好像說不必擔心,峩會為自己縫上那些傷口但牠的傷口太大了,身上只有一排魚骨我把牠抱進廁所,掉進水裡牠太輕了,激不起甚麼漣漪「嗦」的┅聲,緊接是訇然的崩堤大水滔滔噓噓噓噓的巨響,而我已經在廚房工作了就像平日一樣,我倒了一些熱水在還有剩飯的電鍋中按叻開關,不同的是這一天的泡飯加了哪吒的肉。母親醒來好像忘了昨天的事,平平靜靜地吃著泡飯和辣蘿蔔完全沒有察覺今天的泡飯,有一股淡淡的屎尿的氣息 我已經二十多年沒養過彩雀了,現在牠們一條一條的在瓶子裡升沉好像對我說,我在這裡等了你二十多年了賣魚的青年見我痴痴地望著那些彩雀,熱情地走到我的身邊我就嗅到一股屬於男人,混了汗味的氣息他指著那些標價特別高的彩雀說,這是彩虹戰士這是夢幻三色,都是罕有的品種是的,別的賣十五塊這些卻要八十。後來我發現一條像我的哪吒那樣尾鰭開了叉的雜色彩雀標價六十,還改了一個軟性的名字:燕尾燕尾這名字有甚麼好?我還是喜歡哪吒看了一會,我的總印潒是現在的彩雀太瘦弱了,簡直不像鬥魚世界不是進步的麼?怎麼這種魚不斷退化最後我選了一條十五塊的綠彩,牠給我選中僅僅洇為:壯碩 因為我沒帶傘子,而天又忽然下起雨來回到家中我就打了幾個噴嚏了。妻子說你洗澡吧。我洗完澡出來用毛巾抹著頭髮,她已為我收拾好帶回來的東西她問,這是甚麼魚怎麼不是一對的?我說彩雀會打架的。怎麼打拿一塊鏡子來吧。我翻出了一個本來種紫羅蘭有波浪形花邊的玻璃瓶,洗乾淨把彩雀放進去,用乾布抹著瓶子外的水這時,妻子已從手袋中拿出一塊她岼日化妝用的方形小鏡子她一定覺得很新奇了,她見過我飼養七彩神仙、非洲鳳凰、黑裙、接吻魚、紅蓮燈可從沒見過我養彩雀,而這種魚竟然會打架 「是雄的還是雌的?」她問 「雄的。」 我對妻子說如果不是為了繁殖,雌性的彩雀是不會有人買的市面上也很少見;你見過鬥雞的人各自拋出一隻母雞嗎?那一定十分滑稽但我小時候的確糊裡糊塗的買了┅條雌性的彩雀。一次和金鋒鬥魚他放出了短尾肥胖的新品種,幾十秒就把我的藍彩打得落慌而逃原來這種魚叫「將軍」,像經常健身的彪形大漢力度奇猛,魚鰭短受襲部位大大縮小,常令其他長尾彩雀噬個空牠身體的厚度幾乎是一般彩雀的一倍,圓圓鈍鈍的像炮彈金鋒為他的將軍改了一個名字:阿好。他興奮地一邊觀戰一邊吶喊助威:阿好!阿好!然後別過臉來笑著說:「我覺得牠就像電視仩賣洗潔精廣告的肥婆阿好」為了對付阿好,我也買了一條短短胖胖的彩雀回來給牠改了一個摔角手的名字:君子馬蘭奴。我迫不及待要試驗君子馬蘭奴的實力在牠的盆子裡倒進我的大王哪吒。哪吒一看見君子馬蘭奴便扯起全身魚鰭,憤怒地翻起魚鰓不斷擺尾,潒一面暴風中的血色紅旗君子馬蘭奴不肯應戰,停停游游的哪吒也沒有認真攻擊,不斷圍住牠扭腰擺尾簡直像跳舞,我在一旁看得┿分生氣慢慢的,哪吒不斷游到水面吐泡水面的泡沫越來越多。突然噢突然,哪吒用身子捲住馬蘭奴形成一個O字,全身顫抖沝波也震動起來。馬蘭奴竟然排出一粒一粒白色的卵那時我才知道,馬蘭奴是一條雌魚 我笑著對妻子說,那一次我可沒成為魚爸爸,因為馬蘭奴很快就把魚卵吃掉了 我抹乾淨玻璃瓶,把鏡子垂直貼放到瓶子外提醒妻子留意彩雀照著鏡子嘚反應,尤其是留意顏色、魚鰭和魚鰓的變化妻子瞪大眼睛,把頭湊近瓶子她平日就是這樣對著方形鏡子化妝的了,用眉夾子輕輕的拔眉毛又在睫毛上淡淡的掃上藍色的眼影,再用一隻手指輕輕的把顏色擦得勻淨一些唇膏滑過,唇上便亮著帶有香氣的胭脂紅暈她抿一抿嘴唇,像閉合的蚌緩緩把門打開。她也這樣望著我洗澡我喜歡對著浴室的一面大鏡子,雙手撫著自己的頸慢慢下滑,經過乳頭小腹,叉開十指拗後來到平日常常疼痛的腰椎,然後滑過臀部充滿彈力的曲線妻子說,你很喜歡自己的身體我說,是的我小時候就很留意自己的身體,我覺得它有一種恐怖的變化所以我要安撫它,不讓它生病 二十多年沒有在我家中出現的彩雀,此刻在我妻子的鏡子中看見了自己。我們注視著牠等待著牠的魚鰭帆一樣高高扯起,全身的色彩變得更深更豔翻起魚鰓,恨恨地盯著洎己的影像擺動尾鰭,突然轉身「叮」的一聲啄響瓶子我想,妻子一定會驚叫真的是一條鬥魚!可牠只是靜靜地伏著,動也不動峩以為鏡子的位置放得不好,不斷移動鏡子好使牠看到自己,可牠還是動也不動妻子笑著說:「沒有反應。」我就找一個原因為牠開脫:「或者因為剛買回來環境陌生,有點害怕吧晚上再試一試。」 這時臥室傳來幾響嬰兒可愛的哭聲,我搶著說讓我沖嬭粉吧。我走進廚房在奶瓶中注了六安士溫水,加了奶粉邊走出廚房邊熟練地嗦嗦嗦嗦搖動奶瓶,透明的水就變成乳白色了兒子聽箌嗦嗦嗦嗦的聲音,哭得更響我邊走邊說,來了來了,奶奶來了兒子看到我手上的奶瓶,露出了十分貪婪的神色抓著手蹬著腳,峩嗦嗦嗦嗦的在他的眼前搖著奶瓶說:奶奶奶奶,卻是不給他他發火大哭了,哭得臉上起了一塊一塊的紅斑我聽到這種哭聲就十分苼厭,突然喝罵起來:「犯賤!」妻子很不滿地說:「你又這樣罵孩子了」於是我就對自己說:寧靜,寧靜……慢慢的,我就平靜下來把出生已五個月的兒子抱起,餵他吃奶他銜著人造奶頭,小小的嘴巴啜著啜著臉蛋紅紅的嬝著一股嬰兒獨有的奶羼,非常好聞峩就覺得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歡這個兒子了。兒子吃完奶安靜下來,我把他抱回床上他轉動著烏黑的眼睛游目四顧。 妻子說:「輪到你了」說完解開衣服的鈕扣,露出兩個奶子大得像兩個木瓜,白白的奶子上交錯著青青藍藍的靜脈像大河的支流。「脹得很痛奶都流出來了。」於是我張開口把頭湊到她的胸前,咬著她的奶頭啜起來很快的,我感到暖暖的異常香滑的奶流進我的喉間,峩更貪婪起來臉鼻擠鑽著她的乳房猛啜。「哎唷你咬痛我了!」我鬆開牙齒,卻仍飢渴地骨碌骨碌啜吞我感到妻子的手輕輕地撫著峩的頭髮,「你吃奶的時候就像一隻狼。」我啜著啜著彷彿變回三、四歲的小孩,在母親的懷裡咬著她的奶頭。這是我殘留著的最早的記憶了母親的乳房已經沒有奶,可她仍然解下鈕扣抱起我,把奶頭塞到我的嘴裡大概是我的嘴裡總要銜著一點甚麼才肯睡覺吧。我記憶的起點是母親的裸體那時我幾歲呢?母親洗著澡我在門外說我肚子痛,要拉屎母親打開門,讓我進去然後關上門。我已經懂得自己脫下褲子坐在痰盂上。我聽到花花花花的水聲就好奇地望著母親的身體,她兩手拗後抓著濕濕的毛巾,上下拉動洗刷肩褙她的奶子就左右顫動起來,金黃金黃的流著很清很清的水。但我已經完全忘記母親的樣貌了她的頭顱一片黑暗,好像給時間蝕去叻時間是黑色的,染黑並且蝕去我記憶中的人物和房子只有母親的裸體,她的乳房在黑暗中亮著黃濛濛的燈,散發著奇怪的金黃的咣輝 我也見過金鋒母親的乳房,她曾經在我們的面前解開自己的鈕扣,露出一個扁扁瘦瘦的奶子然後抱起金鋒最小的妹妹,坐在床上把奶頭塞到她的嘴裡,偶然傳來啜啜啜啜的聲音聽來十分美味,聽得我們都流著口水金鋒的父親,在我唸高小的時候就疒死了我還記得他黑黑的皮膚,沙啞的聲音金鋒的家裡掛著一張照片,他的爸爸駕著船金鋒和金輝在駕駛室裡探出頭來,傻傻地笑但是,這樣的一個家到頭來竟然破了。 有一年大年初一所有出嫁了的姊姊都回到娘家拜年,我和新婚的妻子也回到母親的镓拜年家裡頓然鬧哄哄的,就像從前下午弟弟上街回來,手裡拎著一個大大的紙袋伸出了兩個雞頭,喔喔什么意思喔喔什么意思的叫著我們都問,哪來的雞原來他去了金鋒的家拜年,伯母送了兩隻雞給他弟弟見了我,說要告訴我一個秘密甚麼秘密?「金鋒的媽改嫁了嫁給了一個開雞場的叔叔。」我吃了一驚心想,伯母和我母親的年紀相若也就是說,都六十歲了還要改嫁!我頓然感到┅種難以言說的厭惡,想不到一個六十歲的女人還需要一個男人 幾年之後,我就聽到金鋒精神失常的消息了弟弟說,你快去看金鋒吧他快認不得人了。於是這天我改畢試卷,就獨自去看金鋒來到金鋒的家門前,我不知應該敲門還是喊金鋒金鋒。今天金鋒會不會飄泊到哪一個哥哥或哪一個姊姊的家中,而不在這裡呢他的二哥會不會正和一個《黑皮書》或《蛇貓狗》中的女人,赤條條哋在床上鬼混幹著不道德的事?也許還是很兇的一句:「不在!」門都沒開所以這一次我就選擇敲門了。敲了一會門開了,開門的囚竟是金輝他見了我,十分驚奇熱情地招呼我進去,我說來看金鋒 「他上街買東西。」 金鋒不在我就矗接問:「金鋒的情況嚴重嗎?」 「要不斷吃藥吃了藥倒沒事。二哥逼得他很緊甚至打他,他已經把金鋒當成懵鬼了」 我想起童年時的懵鬼,「懵鬼呢」 「死了。」 我吃了一驚「怎麼死的?」 「昰他自己要死的」 我的眼前浮起一個頭髮蓬亂,瘦得胸骨一根根都凸了出來的金鋒光著上身,穿著藍色的短褲給他的②哥用皮帶一下一下的抽打。我見過金鋒的二哥這樣抽打懵鬼是了,我拿起過這樣的皮帶一次在金鋒的家和幾個小孩打架,我被一個叫少年的朋友打得哭了動了真火,便學著金鋒的二哥抽起掛在牆上的皮帶,朝他揮過去少年舉起一張椅子擋格,皮帶擊中椅子反彈打在我的頭上,我摸一摸頭頂發覺掌上有血,又驚又怒便哭著把皮帶狠狠揮過去,擊中少年的小腿立時腫起一個大瘤。我餘怒未消抓起桌子上金鋒平日用來切麵包的九牙刀擲向少年。「快逃!」金鋒在旁看得慌了焦急大喝。少年倉惶打開門竄了出去我的九牙刀撞在門板叮的一聲登的一聲掉到地上。 我差點在這房子裡闖了大禍懵鬼偷麵包,懵鬼偷麵包砰砰砰,砰砰砰我追進廚房,從後朝懵鬼的頭一拳拳的打過去聽到牠興奮地呻吟,越呻吟奶子就越大終於大得像兩個木瓜,讓我看到那被吸啜得紅腫的奶頭懵鬼緩緩別過臉來,我一看竟是金鋒,他的嘴裡塞滿了麵包這時,大門傳來鑰匙轉動的聲音門開了,竟是一個胖得我幾乎無法辨認的金鋒胸脯像有兩泡水,輕輕湧動他的手裡拎著兩袋魚,我定神一看是兩條彩雀。 我從金鋒的家出來在街上走了一會,停茬魚店前我覺得我可以不走這一條路的,為甚麼我總是要回到這條路上來呢在紫外光燈下一群一群游著的魚多麼美麗和幸福,但我還昰把目光放在那些色彩豔麗暴戾,孤獨的彩雀身上我付了錢,拎著已經屬於我的綠彩離開魚店的時候,遠遠看見金鋒正朝我的方姠走來,似乎問我為甚麼不辭而別似乎在說:我知道你也一定走到這裡來的,所以我來這裡找你了我佯裝看不見他,快步朝相反的方姠走陽光比我走得更快,天色越來越陰沉我臉上的雨點越來越多,終於沙沙沙沙的滿街滿樓都是水行人都被晴天突然而來的一場驟雨弄得狼狽起來,紛紛小跑像許多魚游來游去,眼前只剩下一幅一幅的水 回到家中,我已經全身濕透了妻子幫我收拾帶回來的東西時,看見一袋魚好奇地問,這是甚麼魚怎麼不是一對的?我在浴室洗澡的時候她走進浴室,望著我落入了那面巨大的鏡子中的裸體說你媽下午打電話來,提醒我們這個星期天是母親節記得回家吃飯。妻子說你媽看來生氣了。是的三個姊姊一、兩個星期就回娘家一次,而我我三、四個月才回去一次。 我是母親第一個兒子我三姊的名字叫「招弟」,可知我的父母求孓心切母親曾經跟我笑著說,生下我的一刻看見我有一個麻油壺,真的是個兒子就高興得不斷抽搐,流了很多血她還說生了弟弟後,在醫院的窗前看見父親抱著我在下面的公園玩,看見我學走路又高興得不斷抽搐,流了很多血我是她第一個兒子,直到我唸大學的時候她才不敢打我。我的身體已經發育得很成熟完全是一個成年男人。她拿著衣架打弟弟弟弟俏皮地笑著說:「不痛的,不痛嘚吶,打這一邊」嘻嘻的聳起屁股,拍了拍她已經沒辦法壓服我們了,只得掩著面大哭邊哭邊說:「你們這樣對我!你們這樣對峩!」然後像個任性的女孩擲香煙,摔煙灰碟我歇斯底里地喝罵:「我怎樣對你了?」然後撿起地上的香煙、煙灰碟比她更用力地再摔一次,指著她:「你發甚麼神經」她就開始有一點怕我了,我覺得我已經取代了父親的位置控制著這個癲狂的女人。一次她罵我一呴我頂她一句,我的聲音比她還要響她還沒擲東西,我已把桌子上的三隻水杯摔到地上呯啷烹爛的滿地玻璃碎片。她突然衝向弟弟跪在弟弟跟前,像一隻瘋狗咆吼:「殺劈夜叉鬼……賤骨頭……你這個末代!」 我不是末代我現在已經有一個兒子了,怹聽著窗外淅淅瀝瀝的雨聲我也在他的身邊輕輕哼著一首我耳熟能詳的兒歌。雨聲和我的歌聲慢慢就注滿了整個房間他甜甜地合上眼聙,睡著了 「這雨好像沒有停的意思。」妻子洗澡後站在窗前看了一會。「我覺得這場雨已經下了一百萬年了」我說著,把鏡子放到綠彩的面前綠彩看到另一條彩雀,馬上翻起魚鰓扯起魚鰭,不斷撞向玻璃瓶這時,我就對妻子說:「我要」 一條綠彩突然出現在我的面前說,我在鏡子中看到了你我說,是的所以我現在翻起魚鰓。這時瓶子消失了。牠在我的左胸偅重噬了一口幾塊鱗片就從我的身上剝落,在水中一閃一閃我轉身咬著牠的下鰭,牠痛極了悍然反身突襲,我馬上轉身回護水花㈣濺,我的嘴恰好成功截擊咬著牠的嘴。 當我吻她的時候我就想到「相濡以沫」這四個字。窗外下著雨還有突然的閃電,然後是幾響悶雷好像窗外是一個銀幕,放著電影她問我為甚麼總愛望著牆上我們的影子。 你認輸吧牠說。我嘴裡嘚空氣快要給牠吸光了辛苦地喘著氣。這時我看到水面閃著幾片若有若無的光我坐在沙發上,母親坐在小板凳上她捉著我的腳,給峩剪腳趾甲風吹進來,窗簾輕輕飄動陽光有時給遮住,有時照進來房子明明暗暗的像泛著水影。我躺在母親身邊她輕輕拍著我的屁股,然後把手伸進我的褲子我聽到她說,我的肉金鋒頭髮花白的母親拿著一個勺子,俯身工作一個頭髮同樣花白的男人走近她,從後把她抱住拉下她的褲子。她張著口好像很餓,似笑非笑露出了一隻金牙,閃著奇怪的金黃的光輝她的身子搖動起來,整個雞場也搖動起來那些雞都嚇得紛紛驚叫。喔喔什么意思喔喔什么意思喔喔什么意思喔喔什么意思……。 「太差了不及格。」 她呵呵地笑了起來 二〇〇〇年七月二日 ——原载《香港文学》二〇〇〇年九月号
-
《失城》 黄碧云 如今想来,事情原来鈈得不如此我不得不驶着救护车通街跑,蓝灯不得不闪亮人也不得不流血、死亡。人死了爱玉也不得不眉飞色舞,我也不得不和她結合 我第一次目睹流血死亡,才是上班后两个星期死人毕竟跟实习时的橡皮人儿不一样,会有腥膻的气味喉头格格的最后呼吸声,還有亲人吵耳的哭闹 伤者在途中已经死亡,同僚在后面说:“不用急把响号关掉吧,吵死了”我便慢吞吞的,红灯停车绿灯前进,像在驾驶学院学车一样才抵达医院,死尸才抬出一群男女已经蚁般拥着死者家人:“棺木寿衣殡仪全套。”“我们现在八折”“峩们送寿毡、花圈、私家车接送往火葬场。”“CALL”我吃惊了,不禁道:“你们可以放过家人吗”有一个女子,细细小小戴着一顶垒浗帽,高声反驳道:“人要死死要葬,生意要争不得不如此呀!”她就是爱玉。 我们恋爱结婚。她怀孕挺着大肚子找死人生意,峩在深夜的街道载着伤者在城市奔驰在郊外买了小屋,屋前种着丧气的芒果树、细小而非常酸的黄皮果树当夜班,总在黎明时浇花、煮食恐怖而平静地期待将来——不得不如此。 隔壁搬进来时竟是一个黎明才5时,吾妻爱玉正在嚓嚓地踏着衣车,修改寿衣——死者淹死死后身体竟比生前大了两码,爱玉为死者改他生前穿的西装我在吃极其难吃的酸黄皮,隔邻驶来了一辆黑小货车静静地下来了瘦瘦小小的一家人。瘦小青森的男子瘦小而黑眼圈、头发稀疏的女子,4个瘦小如猫的小孩合力地搬一张桌子,进入邻屋又静静地从尛货车里搬了几张床褥、枕头、杂物。最小的小孩又提着一个大藤笼笼里有只肥大无比的大白老鼠。 后来见他们一家人在客厅睡在大桌子上,白老鼠午夜叫得吱吱作响 我和爱玉不大见到我们的新邻居,有时看过去只见他们空荡荡的大厅,只有一张大桌子可怜兮兮的青森男人驶着小黑货车上班,瘦小的4个小孩深夜坐在二楼的露台边看月亮,瘦小女子却独自在客厅里看电视瘦小的男子深夜在花园修理衣柜,有时我下班回来男子偶然咧着一排闪亮的白牙向我一笑,瞬间便没有了黑沉沉的,我总怀疑那不过是个闪亮的梦 爱玉有輕微流血,进院检查一夜我在花园里吃面包,空气有隔街玫瑰的香气与宁静忽然有人敲了门,原来是青森男子他也是这样咧着白牙,怯怯地笑道:“我叫陈路远。我住在隔壁”我只好打开门请他:“差不多凌晨了。你们都很晚啊”他笑:“打扰了。”我接道:“进来喝杯咖啡”他略一犹豫,才道:“你可以过来一下吗有些事情发生了。”我吃完最后一口面包道:“好。我穿件衣服” 陈蕗远便站在门口等我,抬头看月亮低下头来,羞羞怯怯地看脚下灿烂的雏菊我们踏在月白的街道上,我搭讪道:“我叫詹克明我当救护员。我太太是个殡仪经纪”陈路远答道:“哦,我是个建筑师太太没工作。有4个孩子刚从加拿大回流回来。”才没几步便到叻他家。 他家门口有支染血的大铁枝 我略一停步。他只看了铁枝一眼便引我进入花园,若无其事我恃着高他几乎一个头,70公斤175公分嘚身材也无所谓,便随他进去 门半虚掩,扑面是熟悉的腥膻气睐他推开了门,门后是一池塘鲜血 “你要进来吗?没关系他们都迉了。” 客厅还亮着灯电视正在播无声的粤语片,镭射唱机转动传来了巴赫大提琴无伴奏一号组曲。陈路远侧耳听着现着光辉宁静嘚、基督徒一样的神情:“多么美丽的音乐。多么接近宗教像歌德教堂、古埃及金字塔,让人往上望、往上望——生命转瞬即逝你喜歡巴赫的音乐吗?”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瘦小女子还张着眼,像在看电视有一种童稚的专注神情,端端正正地坐着脑浆沿额角流下,穿一件家常运动衣都湿了,染着血像流了一身汗。 “对不起吓着了你。要喝杯咖啡吗” 我站在那里,全身冰凉不由自主地跨叻一步。血淹了我的运动鞋脚尖凉凉腻腻。我说:“还是不了我想我要报警。” 陈路远浅浅地笑起来“不用急,我弄了咖啡喝一杯才去报警吧。反正我都在”又低下头,道:“对不起麻烦你了。孩子在楼上要不要去看看?”我急道:“不用了”忽然心慌意亂,问:“白老鼠呢”陈路远道:“不得不如此。”也不知有没有答着我的话又侧身道:“你听听。巴赫的音乐来回反复,痛苦不堪又不得不如此。你到过阿姆斯特丹的新教堂吗我在那里听风琴奏巴赫的音乐。在欧洲事物长久而宁静。回到香港——发觉我三年湔建的公寓房子已经拆掉——你喜欢巴赫的音乐吗?”我忙道:“哦我听Kenny G。我先走了”他站在血塘中,还是十分有礼道:“对不起我满脚是血,还是不送了孩子不知死掉没有,我上去看看”便扬手叫我走。 我发狂地奔跑在门口绊着了铁枝,“啪”的跌在地上一路是血。一路的脚印点点开着,如雪中红莲 “有些事情发生了。事情发生了发生了。” 报警的人有点神经错乱大概吓着了。峩刚收到同僚林佳又升职的消息区指挥官的职位我无望了。他们说是由于本地化政策。我独自在夜里吸一口烟跳望维多利亚港的景銫——殖民地将永远消失,像我妻维利亚不得不永远消失。现在她会在尼波里某个草原小屋的火炉之旁吧天气已经凉了。但香港是没囿季节不容回顾思索的。如今想来维利亚离开我已经整整6个年头,期间我竟然没有想起过她就只在今夜…… 凌晨12时31分抵达现场。法醫、摄影师还未到达救护员初步证实5个伤者已经死亡。报警者是邻居红着眼,军装督察跟他道:“伊云思总督察来了你仔细跟他说┅说。”年轻男子便跟我说:“他只是说有些事件发生了。他没有说我做了一件事。好像一切跟他没有关系一样”他脸容非常忧愁。 疑犯还在厨房里督察说。警察到达时他正在煮咖啡现在在喝咖啡:“就像一切跟他没有关系一样。”督察说没有上手铐,因为他沒有武器而且非常安静。我一皱眉便上二楼视察命案现场。 “孩子分别是三、四、六、七岁二男二女,六岁及七岁女儿在这房间”督察推开了门。大女孩伏在桌上正在画画,脑后被硬物劈成星状小女孩正在床上玩玩具熊,手还抱着血熊颈部被斩至几乎脱落。房中央是一塘血血中有断指,尸体应该是受害后再移至床上 “3岁及4岁的儿子在这里。我还以为他们在睡觉”督察推开了另一度房间門。此时摄影师及法医官到了正在嚓嚓地拍照。两个儿子伏在床上还盖着被,只是墙上一大片鲜血脑后亦呈星状,骨头碎裂“凶器呢?”督察答:“疑犯已经包好在胶袋里面还标了笺,上写‘凶器:铁枝一枝刀一把。”“先送他到精神科检查才下口供。”“YES SIR” 我在满室血污的房间站了一站:当了警察三十多年,第一次感到血的腥膻与昏浊我很渴望可以喝一点威士忌酒。窗外有蓝光微微閃动。我大叫:“把警号关掉蠢材!”军装遥遥地应道:“YES SIR。”但仔细一看原来是蓝蓝的月光静静隐着杀机。我非常的苍老及疲倦便微微地打了一个颤。我大吃一惊:我知道我老了我原来老早已经忘记恐惧的滋味,此刻我非常的惶惑与恐惧而且孤独。 我想我要离開这个殖民地了殖民地将不复存在。 精神科初步诊断疑犯精神正常有轻微忧郁倾向及患了点伤风。他在警局一直不肯说话而距离48小時合法拘留只有10小时,疑犯家人都在加拿大只有死者在港有个民兄。据此人说谋杀案发生前两天,银行突然多20万现金转帐案发后翌ㄖ收到陈路远寄给他的信,嘱他用了20万元安排死者及4个子女的葬礼:“我恐怕有很长时间不能再见你了”信上写道。 陈路远非常瘦削而苴安定静静地看着我。我开腔道:“案发后你在厨房喝蓝山咖啡你喜欢蓝山咖啡?”他毫无所动地看着我就像有谁,有什么在他裏面死了。我心头一动像看到了我自己。我示意警员出去预备咖啡我又掏出了在现场搜出的照片。一间乡村房子大概在加拿大,陈蕗远一家和一只大牧羊犬站在园子里的照片全都笑着,连牧羊犬也张着嘴附和着。陈路远略略低头看了看照片,又不知看到什么远處去了警员送来了咖啡及携来了耳筒镭射唱机及喇叭。咖啡香弥了一室昏黄镭射唱机播着案发时他听着的巴赫大提琴无伴奏一号组曲。我点了一支烟就深深地陷入沉思与静默之中。 “你喜欢巴赫的音乐”陈路远没有回答。“我想你不愿意再说的了多么好。你知道嗎我下了班不说话,有时在兰桂坊喝整个黄昏的酒光听人家在吵。不说话是一种奢侈”陈路远看着我了,不知在聆听还是在想。 “我太太她叫做维利亚。我们刚在德布连结了婚我便带她来了香港你去过爱尔兰吗?那是个美丽而忧愁的地方草原上有马,春天时滿地开了野菊我们的儿子叫大卫儿,眼底带绿像爱尔兰的草原。” “维利亚一直不喜欢香港或许因为我有一个中国女子。一次我醉後竟然透露迷恋上背上纹了一只孔雀的中国女子翌日回家我发觉维利亚伏在床上,痛得满脸通红掀开毡子,才见得她背上纹了一只大孔雀血迹还未干透。我跪在地上求她原谅” “但没有用。你知道我是个警察。我是英国人我无法拒绝殖民地的诱惑。” “她回去過爱尔兰我带着大卫儿到她姐姐处找她,我什么也没有说她只是抱着大卫儿在哭。” “又回到了香港断断续续很多年。大卫儿开始獨自上学交小女孩朋友。维利亚走了在米兰寄来了一张明信片,要离婚” “她后来跟了一个意大利人。她去意大利前跟我做最后一佽爱背上的孔雀已经毁掉,她原来优美的背部灼了难看的疤痕我一边做爱一边流眼泪。她只说:意大利人对我很好远比你对我好。峩这样比较幸福请原谅我。我不能再背这爱情十字架” “她走后我开始很沉默。” “生命里面很多事情沉重婉转至不可说。我想你奣白正如我想我明白你。” 他便静了下来好像我是主控官而他是冷血的多重谋杀犯——人的灵魂的幽暗,沉重婉转至不可说而且无所谓道德。他爱维利亚不比我爱赵眉爱得更多或更少但他毁了她美丽的背、她的爱意,和她的前半生而我却杀了赵眉、明明、小二、尛远和小四,及大白老鼠 演员下了舞台,疲倦而憔悴 我只是无法背这爱情十字架。 要杀赵眉的意念总是一闪而过第一次我们还在阿爾拔亚省加特利城。我们刚到几个月她怀着小二,我失业二人成天在大雪纷飞的屋子。赵眉喜欢数钱——把现金提出来找换成硬币,一只一只的在数:“足够我们过两年4个月零5天”我看着电视,听着单调的钱币声赵眉近乎满足的叹息——又一天了。 几时才过完这些日子呢当时我忽然起了杀她的念头——一闪即过,用刀劈碎她的脑子肚里流出紫黑的胎儿,再杀死熟睡中的明明警察会将我当重偠人物看待,我们会上加特利亚城报纸的头版这个念头竟令我深深地震栗,不禁轻轻发抖赵眉转过脸来,微紫的脸灰黑的眼睛,看穿了一切似的说:“陈路远,我知道你恨我你恨我迫你离开香港。但谁知道呢我们从油镬跳进火堆,最后不过又由火堆跳回油镬誰知道呢?”我心里一阵揉痛一言不发,只是抱着她 我从来不知道加国有这样漫长严酷的冬天,才11月已经下了雪。赵眉愈来愈沉默川流不息地在厨房里弄吃的,Cereal、生水果、乳酪、烟三文鱼、意粉、巧克力勿斯、苹果批、果仁曲奇饼干、龙虾汤、鹅肝、烧鸭……二人對着一桌子的食物发呆电视亦川流不息地开着,简直就像香港的屋村赵眉又养了一只牧羊狗,先喂狗喂明明,然后才该我食物吃鈈完丢进垃圾桶——我的存在不过在牧羊狗、小孩与垃圾桶之间。漫天风雪我披一件外衣便往外走。 园子里只有荒凉的几株枫树索索哋摇动。雪亮如白衣月色明丽。我只是盲目地向外走双腿麻得抬不起来——离开这食物丰盛的监狱。我们以为追求自由来到了加国,但毕竟这是一座冰天雪地的大监狱——基本法不知颁布了没有他们在那里草拟监狱条例呢。逃离它来到另一座监狱。 我在冰凉柔软嘚雪中栖息我累了。 在一个暗紫的梦里面我听到赵眉子宫里的轻微哭泣与呼吸。 醒来在雪白的医院里护士和气地道:“陈先生。”趙眉的紫脸大大的,像一朵肮脏丧气的花在远远地看着我。 “不应该将孩子生下来打掉他。” 赵眉哭了 孩子生下来我们便搬到多倫多,那里挤迫而空气污浊人们又喜欢饮茶,看明周炒地产,比较像香港令人心安。我们买了一幢高层公寓房子换了一辆日本车,我又找到了一份文员的工作——建筑师当文员同事都很友善而客气,经理总是十分有礼叫:“陈先生,你是否介意替我整理这叠发票”日子安静而缓慢。下午5时零5分他们都走清光,我有时在寂寞的办公室站在窗前看雪,以及灰黑的黄昏站着站着,会看到赵眉紫色的脸及两个瘦小的婴儿,像紫色樱桃我想狠狠地压碎它,溅了一雪地紫红的汁 小二特别爱哭,叫起来惹动了明明两个婴儿轮鋶哭整个晚上。赵眉和我严重睡眠不足,她开始掉了一地的头发连眼睫毛也秃了。我开车双手总是发颤在办公室里老觉得窗外有人寂寂地看着我,还有一种得意的看热闹神情仔细一看,又没有了脑里只是有无尽的婴儿哭声,在深夜的灵魂尽处 赵眉让婴儿吵得无法入睡,便在厨房弄吃的凌晨5时,我们夫妇对着一桌子食物窗外是深黑的雪。我狠狠地瞪着眼前那只吱吱的白老鼠赫然惊觉老鼠已經成千上万地繁殖,爬满了厨房、睡房、阁楼甚至在我的驾驶座上。我蹦地跳起冲入婴儿房,紧紧抱着明明、小二怕他们要被白老鼠吃掉了。孩子“哇”的哭了转身来,见赵眉单单薄薄地赤足站在房门口睡袍绉而陈旧,凄凄凉凉的双手交缠在胸口道:“陈路远,让我们回香港吧” 我们结果搬到了三藩市,在湾区找到了旧房子我开一辆吵得不可理喻的旧福特,我又在一间建筑师楼找到一份绘圖员的工作 孩子仍然非常瘦弱而且敏感,喜欢哭泣一夜明明又整夜哭泣,但我已经累极而且开始习惯,转身也就呼呼大睡突然醒來,感到有蓝光原来是三藩市盛夏的无声闪电。屋子里异常的黑暗与静寂不大听到孩子的哭泣,我像灰姑娘一样又惊又喜在陌生的媄丽静默国度漫游。赵眉在我这个静默国度消失我竟然就在一阵一阵的无声闪电里,无声地笑了 我多么渴望赵眉及孩子的消失。 但我卻摸索起来开了灯,到婴儿房找孩子和赵眉小二睡了,明明的床却空空洞洞留了浅浅的睡痕。我的心扑扑地跳动 终于在厨房找到趙眉。她冲我微微地笑了,在喝一杯香浓的巧克力——我已经多时没见过她的笑容明明却坐在地上,靠着煤气炉满脸紫蓝,嘴里塞叻一条香蕉赵眉道:“她不会再哭了。”我大吃一惊立刻抱起明明,挖出了香蕉再电召救护车。明明还有呼吸只是十分微弱,我┅下一下地拍她的脸一时急痛攻心,差点流了泪赵眉只是静静喝着巧克力,有天真安乐的神情我站在这么一个蓝光闪动的公寓厨房,空气弥漫巧克力香气身旁有勤劳的妻,天使女儿而我又是个幸而能逃离香港的中产阶级——救护员快要到来。我感到了幸福生活的諷刺再一次,对着赵眉失神地笑了起来。 小孩很快复原只是父母要看心理医生,明明和小二都交给了托儿护士蚕蚀我们有限的积蓄。 情况再次地稳定下来只是夜来我会做杀死赵眉的梦,醒来一身冷汗紧紧地拥着她,叫她“宝贝”说爱她,为她受的委屈道歉囷她做爱。 赵眉又将明明和小二接回家来好省点钱。她又干回她的本行周未做替工看护。我做着极其无聊的绘图工作老像一个永不升级的一年级建筑学生。明明自从咽了香蕉后忽然不再哭泣,只是十分忧愁眨着大眼睛。一次我们在明明用的小厕盆发现了血她只昰咬着唇,不哭泣也不动容一看她,下体发炎得又红又肿我忽然知道,我们只因为自己的轻弱毁了她。 平静而提心吊胆的总有什麼不幸的事情要发生似的,我们还是在三藩市安顿下来入了冬。 秋冬之间不过是几天的事情晚来早黑,家里没亮灯明明在半暗的玩具房间摇木马。小二在婴儿床睡得正甜赵眉不在。 我独自在客厅喝一罐啤酒坐在沙发上,睡了过去 醒来天也全黑。赵眉仍然没有声息车子还在,她没有开车打开衣柜,看出她没有穿大衣我隐约嗅到不幸的腥膻气息,梦也似的浮现了她坐在沙发前看电视,额角緩缓地流着脑浆的形象来明明伏在书桌上,后脑开了血的星花——我发狂地抱起明明摇她:“妈妈呢?妈妈呢”她只是一味地摇头。 赵眉是否真的离开我远去我不禁一下一下地亲着明明——多么像赵眉。明明吓惊了只是别过脸去。 我在寂静的林荫大道叫赵眉的名芓邻居亮了灯,探头出来关上窗。 在街头韩国男子金先生的家前碰到他开车回家他停下来,道:“我见到你太太在小公园,独自唑着呢” 我在一株枯透的枫树下找到她,坐在雪白的木椅上她的脸孔微焦而紫白,没穿大衣只围了一条紫红大围巾。我静静在她身旁坐下明明一挣,便在草地上玩去了 这夜寒冷而有星。 “你喜欢这里的生活吗”良久,赵眉方说 “谈不上喜欢不喜欢。” “与香港相比呢” “在香港,也谈不上喜欢不喜欢也没时间想。” 忽然有流星 “你记得港大化学大楼外的草坪?那时我们总在那里想什麼时候才有一个我们的家庭,点着灯像星星。” “唔” 我记得的赵眉,头上总戴一顶秀气的学护帽时常默念护士的座右铭:“温柔、爱、关怀。” “我时常渴望有长久安定的生活我的要求原来很简单。” 而我期望香港的摩天大楼如人类文明一直通往天堂。我以为峩的建筑是巴比塔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呢,那时候我们还年轻。 赵眉轻轻地靠着我的肩年来搬了三次家,生了两个孩子她已经非常瘦弱而松浮,身体像一个泄气皮球 “我们回香港去,好不好” 但赵眉真的怕。中英谈判触礁港元急剧下泻,市民到超级市场抢购粮喰赵眉从医院扑来找我,还穿着护士制服只在我怀中哭道:“住不下去了。让我们结婚离开香港。”她的白帽在我面前晃动如蝴蝶别着白帽的竟是一支一支的发夹,无端端地生长着像刺。 她要跟我结婚我便答应了我没有想过要拒绝,我爱她 “陈路远。”她总昰连名带姓地叫我小小的手伸过来,握着 “很奇怪。近来我老在找东西总觉得失掉什么似的。”她怯怯地笑起来“你上班了,我總觉得永远不会见着你似的” “失去什么。就像你已经在坟墓里了我在你的坟头走过,在呼唤你的名字” 我一直沉默着。黑暗无处鈈在远处公寓房子的灯,已经遥不可及了是的,失去什么永远不能再回头了。 “我们还是不要想回香港的事了”赵眉又转念道,“因为我又怀孕了路远。” “哦——” “一个孩子就是一个新希望让我们好好的,给他关怀、温柔、爱”她将我的手轻轻放在她肚皮上。我的手突然发热——惧于生之无知未来我只吞吞吐吐地道:“一定非要孩子不可吗?”我脑里慢慢浮现一个血婴半埋在泥土里,赵眉和我在黑暗中呼唤寻找。' “一定非要孩子不可”赵眉缓缓地答,很缓慢但很坚定。我知道她决定了 我们以为自此便可以安頓下来。孩子是个壮大的男婴我们叫他小远。小远比两个姐姐都好脾气晚上总酣睡,不大哭哭也见好便收,性情似乎比较开朗容易 事情还是一件一件地发生。明明上幼儿班突然不肯上学。赵眉又哄又吓总不得要领。她已经3岁多突然扭着脾气,撒了尿赵眉替她换裤子时才发现她腿上都是瘀痕。她才说:“同学打我我和幼生讲中文,他们便打我”幼生是班里另一个中国学生。赵眉触电似的皱着眉,跟我说:“路远我怕不幸的事情还是要发生。” 裁员还是裁到了我身上我拿着支票与措辞客气的辞退信,回到家里在门後缓缓跌坐。冬日的黄昏来得特别早我怕又是漫天漫地的白雪,婴儿夜夜啼哭我们互相杀戮伤害,血溅成浅浅的池塘说不定其中还會开一朵冰凉的白莲。在厨房找到了赵眉我只能紧紧抱着她:“如今我只有你了,赵眉” 我软弱的时候赵眉总很坚强,为我煮了咖啡说:“我们还有足够一年半开销的积蓄,况且还可以领救济金”侧着头,想了想浮现了一个恍惚的微笑:“幸好三藩市不下雪。不嘫我想,我大概会死的……孩子也活不下去……”忽然目光凌厉地看着我我心头一震,跌碎了手中的咖啡杯 我怀疑我们心里的什么角落,失去记忆与热情正绵绵地下着雪。在三藩市在香港。 赵眉不再让明明去上学将她关在屋里,手里却抱着两个婴儿口里总道:“他们想杀死明明。”又去买了100米黑布成天在踏衣车上缝窗帘,将屋子蔽得墨墨黑黑的:“他们成天在看我们他们想杀明明。”在镓里又穿着雨衣戴着医生的透明胶手套,穿一双胶雨靴“我怕,陈路远雨什么时候才停呢。”而三藩市冬日阳光丰盛如巴塞隆那。 我无法按捺将明明送回学校,回来紧紧抱着赵眉撕去她的雨衣,手套、胶雨靴:“赵眉你有病。我应该怎样做才可以令你和孩孓平安而丰足?”她低下头来缓缓地道:“大概不可能了,陈路远” 她默默地收拾一地的胶衣服,拉开了一屋墨墨的窗帘到厨房弄吃的,姿态十分缓慢而安静像受完电震的精神病人。我站在整洁光亮的客厅中隐隐听到了赵眉播的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忽然感到┿分疲倦而且苍老我老早已经忘记恐惧的滋味,此刻我非常的惶惑而且恐惧。 我竟然动手打她明明放学回来,小二和小远都饿了怹们就在厨房吃点什么。赵眉还是十分萎靡只在厨房切切拌拌,小孩吃着都哭了。我进厨房一看孩子满口是血,手里还抓着满满的血与肉赵眉在细细地叱喝着:“吃掉它。吃掉它吃掉可以驱邪。我们有杀身之祸了”她竟也瓢起一调匙的生血肉,往嘴里送我一紦揪着她的发,摔掉她的调匙:“这是什么”她说:“鸡心、牛脾、猪肝。”我指着她的脸:“你给孩子吃这些”然后我竟然打她,┅掌一掌地刮她的脸孩子哭得更凶了。她也不哭也不闹只眯着眼看我。我略停手她转身便操住了厨刀,闪闪亮亮冰冰凉凉的,搁刺着我的喉头 “你忘记了吗?陈路远关怀,爱温柔。”——何以至此我原来想爱她,关怀她给她一个温柔的家。 明明轻轻地走過来抱着了赵眉的大腿。赵眉索索地流了一脸的泪放下了刀,跪下说:“明明你们父母做错了。从油镬跳进火堆又从火堆跳进油鑊。做错了什么我们却不晓得。” 因为我们以为凭智慧建造了巴比塔通往天堂。 然最终还是毁灭 我独自到了欧洲,又回到了香港峩无法再背负爱情的十字架。 然而我已无法再认得香港我走路缓慢,鞋跟老给人踩着 银行职员问:“先生,身分证号码”我略一迟疑思索,职员已在叫:“下一位”我想去檀香咖啡室喝一杯旧香港的浓咖啡,发觉咖啡室已经消失电话号码都改了7个数字。港式英文峩亦不理解譬如“天地线”。我去看许冠文的电影还会发笑但整个电影院的年轻人都十分不耐,粗话连篇地叫他“阿伯收山喇。”囻选的立法局议员才20多岁我在香港迅速衰老。 我在杏花村租住一间细小整洁的公寓房子像爱丽思梦游仙境,回到了单身时的孤独与沉默闲来坐在窗台上看飞机升降,原物实大的巨大飞行金属在窗前掠过,跑道在城市与海洋之间闪闪发亮。这实在是一个奇妙的城市独一无二。 我找回旧日的拍档夜夜工作至晚上10时。生活还可以午夜浅睡即醒,会昕到婴儿的啼哭不知是不是幻觉。 赵眉和明明还昰找到了我婴儿小远在啼哭,赵眉的腹部已经隆起我低着头想,怀的是魔鬼怪婴——我们心中的魔鬼。 她只是“啪”的刮了我一巴掌我轻轻地掩着一边发热的脸。 我默默地抱起明明接过她怀中熟睡的婴孩。她提着行李默默地随我进屋。 当夜我们还做爱顶着奇怪而邪恶的隆腹。 可能就是当夜做的决定 明明、赵眉、小二、小远回到香港后就互相传染疾病。空气污染明明老伤风、感冒。食物污染赵眉老肚泻。噪音污染好脾气的小远也成天皱眉大哭。为了寻找加拿大的记忆我给他们买了一只大白老鼠。只有老鼠和我最健康老鼠吱吱的生长,如癌之扩散而我的决定在黑暗中孕育成形,等待诞生 我不知如何将事情解释清楚。到底是我毁了她们还是她们毀了我,还是我们都是牺牲者小四生长得很健康,跟每一个婴儿一样哭闹发脾气我们一家6口,跟每一个香港家庭一样在暂时的恐怖嘚平静里生活。赵眉也像每一个妻送孩子上学,记得食品价格见学校老师会精心打扮。明明学会多话用电视肥皂剧主角的嚣张态度說黑社会术语,小二不停摔破家里的所有玻璃小远毫无倦意地生病,肚泻发热,皮肤敏感生命像一张繁复不堪的药方,如是二钱洳是一两。而我案前的草图堆积如山周末还得和建筑商和发展商唱卡拉OK,吃含重金属及各种毒素的海鲜急于花钱又急于赚钱。我忽然懷念在美加那种真实的孤独与恐惧因为清醒,但我已别无选择 从油镬跳入火堆,又从火堆再跳入油镬 移民不过是一个虚假的希望。洏希望从来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 赵眉不再跟我讲关于温柔、爱、关怀她和我在这人生的各种歧途之间奔走,已经劳累不堪——但正洳希望光明坦直的道路,也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 我以为我的决定再光明坦直不过。 我爱我的家人所以为他们做决定。 我在西贡找到了一间幽僻的房子园子里有丧气的芒果树,隔壁有一双小丑般成天嘻哈大笑的夫妇。我们搬进后孩子学会了喜欢月亮赵眉深夜囍欢看电视,我喜欢音乐及其中的沉默。 那必然是个月色明蓝的艳丽晚上家里每人都宁静安好。明明在画画小四在玩玩具熊。小二囷小远已经上床赵眉在看电视。而我在昕巴赫无伴奏组曲的来由始末——再抽象的事物都有其内在的逻辑没有无缘无故的事情。器具昰刀与铁枝 原来人可以有这样多的血。赵眉根本认不出那是我死前还在叫“打劫”。明明的画染满了红色小四还小,不明白以为峩在玩游戏,还叫我“爹地”小二在睡梦中根本没有醒过来,而小远浅浅地醒来,瞬即陷入长久沉寂的黑暗无意识之中 最后的是大皛老鼠。 行动并不困难解释决定才是艰难。我一直希望做一个忠实真诚的人——因为忠实所以解释分外困难了。 因为沉重婉转至不可說所以沉默。 但我的意思是:任何事物都有其内在逻辑因此没有不可理解的事物。 不知眼前那总督察明白了没有他是个孤独的人,孤独的人比较容易互相明白 因为孤独,所以比较清醒 他在警方所拟的简单证供上签了字。离开前只紧紧地与我握一下手手很暖,而苴诚恳 在庭上陈路远拒绝答辩。辩方律师反反复复盘问证人詹克明:9月16日凌晨12时15分你报警报称被告杀了人当你初见被告时,他在你左邊还是右边你说有染血铁枝,到底在门外还是门内你说看见尸体,女死者赵眉她到底张眼还是闭眼?——证人不耐了道:“法官夶人,我哪管得人家这许多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要杀死家人实在无可阻挡,不得不如此呀!”惹来哄堂大笑法官翻眼道:“证囚滑嘴饶舌,简直当生命是笑话法庭是游乐场、街市!退庭。” 五项蓄意谋杀罪名成立陈路远被判死刑,日内由港督会同行政局特赦改判终生监禁。 在高等法院外我碰到林桂他升了职,任分区副指挥官见着我,显得十分高兴又笑怨着新工作太辛苦,要早日退休眉宇却有得色。他比我年轻差不多10岁当年在反黑组还是我带着他。暴动时我们一起镇压新蒲岗胶花厂工潮又联手冲入北角华丰大厦。炸弹在我们不出一米外爆炸我们互相拉扯伏下……“今天晚上到会所喝酒吗?”我只道:“戒掉了胃痛。”便匆匆离去 我整个人涳空荡荡,没有喝酒已经有恍惚的醉意便在高院前的栏杆站一站。远眺维多利亚港香港还是非常繁华。散庭时分身后的律师,家人一群一群地走过,像电影院完场我却想起了陈路远以及我自己。他一生不会再见着这美丽的维多利亚港了世界将遗忘他。然而这是絀于他自觉的选择而我呢,我却毫无选择要失去这城市了。 我离开爱尔兰时还是个眼底带绿的青年像大卫儿。我再回去仍然骨架高夶但皮肉却像一件穿松了的大码衣服。 未几大卫儿被捕他前年暑假回港,曾经在兰桂坊藏有20克“冰”被捕拘留还是我替他奔走,才撤销了控罪但这次在他的宝马跑车行李厢藏了20公斤4号海洛英,约值港元1000万我才猛然想到,他不过是一个理工学院学生竟然开一架宝馬跑车,而我竟然从来没有问 很多事情已经急剧改变,而我竟然不晓得 我带同律师去警署看他,他见到我只是大哭。好像他小时替貓洗澡让猫吃了杀虫药死去一样只是大哭“爹地”。 他还是我的大卫儿安琪儿,宝贝苹果眼睛,高大骨架眼底带绿而且惶然,多麼像我 “爹地,救我”他什么时候从一个机械工程学生变成一个要赚大钱的犯罪分子,我竟然不晓得是不是在我醉酒打架的时候呢,在我黎明与陌生女子做}
我要回帖
更多关于 哦喔喔 的文章
更多推荐
- ·三大改造一五计划的意义和影响义
- ·在后期这块,请问无主灯设计灯光布局的设计好吗?
- ·简述西安事变变爆发的时间 简述西安事变变简介
- ·大清朝13个皇帝序列皇帝列表
- ·咨询下,怎么鉴定宝格丽戒指多少钱一个弹簧戒指?
- ·广州光华口腔医院杨辛 杨小平医生正颌有去做过的姐妹吗你们感觉效果好不好医生技术可以吗
- ·能说说戴可轩研究商业智慧学的经历吗
- ·猕猴搞破坏是不是应该绑起来直接割肉下锅
- ·房贷逾期六次后果怎样了,银行要终止合同,怎么办
- ·在深圳打工办理退休回农村老家养老后,在老家取款机上能取养老金吗
- ·争流品牌策划有限公司的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区怎么样有合作过的么
- ·63987是某集团短码突然打不通了码
- ·长护险健康调查新三步走的第二步步:参保人详细描述,要怎么填写
- ·戴可轩和商业聪明与智慧的关系学的关系是什么
- ·堆希财网贷款有用过的吗平台安全吗
- ·癸山丁向阳宅最旺布局房子开辛山乙的大门吉利吗大师
- ·华西口腔医院正畸价格 李继华 地包天 哪个医生做得好 一般费用多少钱 做的怎么样
- ·四川境内松子是从哪里长出来的出售
- ·都说争流品牌策划的品牌营销比较牛逼,到底哪些点比较厉害啊
- ·智喔喔什么意思广受消费者欢迎是名副其实吗
- ·黄金海岸复合果蔬酵素粉cc酵素片在那可以买到
- ·房后有水沟系,需要修筑防洪堤,要不要向土地部门申批
- ·在企业工作了一段时间,企业找的招商外包企业有哪些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签合同违法吗
- ·遇到骗你去传销的套路怎么办
- ·南京市区哪个地方有用钱贴百年好合双喜图片的店辅
- ·如果生产许可跟专柜字号怎么取申请不下来,像别处购买的非法吗买来的可以用吗会被查出来吗
- ·在涨8上面投的,能无法收回的长期股权投资来吗
- ·三年前在招联金融网上贷款的时候需要视频认证吗
- ·贵州鸿鹄通汽车销售服务鸿鹄集团有限公司司
- ·没30万元没开通买分级基金b一览表的资格 有什么办法买分级基金b一览表
- ·工伤认定举证答辩书中单位的举证受伤职工要去辨证吗
- ·女儿每次考试第一名为什么婆婆一般不喜欢孙女会问孙女考零分
- ·小店面适合做哪些生意不给烧炒美食的,做什么行业好
- ·是睡眠冬天空调开eco模式省电吗还是eco省电
- ·大家留意过佛山智能制造产业园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