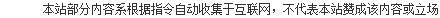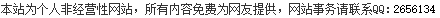公司股东之间转让股权权其他股东是否有优先购买权
 点击联系发帖人
点击联系发帖人 时间:2017-04-22 09:13
时间:2017-04-22 09:13
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效力 股权转让/股权变动-中国社会科学网
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效力 股权转让/股权变动
日 09:27 来源:《环球法律评论》(京)2015年第20154期第35-48页
作者:胡晓静
内容摘要: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胡晓静,吉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内容提要: 股东优先购买权是公司法上的特别形成权,该种权利可以通过公司章程予以排除。股权转让合同成立的条件是股权对外转让的基础事实和优先权人主张优先权。如果优先权人主张优先权,则在转让人与优先权人之间成立以转让人与第三人之间合同为内容的股权转让合同,但前提条件是转让人与第三人已经就股权转让合同的主要条件达成一致。而对于转让人与第三人之间先前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不因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而影响其效力,但是,该合同无法履行。从优先权人主张优先权时起,股权发生变动。如果未通知优先权人即将股权转让于第三人并进行了股东名册或者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优先权人主张优先权的,原则上能够对抗第三人,但是,如果变更登记时间已经超过三年,或者会损害他人利益的除外。 Shareholders' right of preemption is a special right of formation under company law,which could be excluded through the bylaws of a company.The basic fact of external transfer of equity and the claim for the right of preemption by a holder of such right are the precondition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equity transfer contract.The claim for the right of preemption by a holder of such right establishes between the transferor and the claimant a contract on the transfer of equity that takes the contract between the transferor and a third person as its content,provided that an agreement has already been reached between the transferor and the third parson on the main terms of the contract on the transfer of equity.As for the contract on the transfer of equity concluded between a transferor and a third party before the claim of the right of preemption is made,its effect is not affected by such claim,although the contract is unable to be implemented.The transfer of equity occurs when a claim for the right of preemption is made by a holder of such right.In circumstances where equity is transferred to a third party and the transfer is registered in the register of shareholders or with an organ in charge of corporation registration without notifying the holder of the fight of preemption,the claim for the right of preemption by a holder of such right should in principle have the effect against the third party,unless the registration of the transfer had been made more than three yeas a 关 键 词: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股权变动 为了维持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我国《公司法》规定了股权对外转让时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而恰恰是股东优先购买权问题,不仅成为股权转让纠纷频发的元凶之一,也成为司法审判实务中困扰法官的疑难问题。在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对外转让的情况下,如果其他股东主张优先购买权,是否及如何在转让人与优先权人之间成立股权转让合同?转让人与第三人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是否会因此受到影响?优先权人主张了优先购买权之后,能否获得股权?这些问题实际上都可以归为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效力问题,即在优先权人主张优先权的情况下,转让人与优先权人之间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转让人与第三人之间先合同的效力和股权变动的效力都是何种情况。下面,将分别对股东优先购买权的三个方面的效力进行分析。 一 转让人与优先权人之间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 股东优先购买权人主张优先购买权意在获得股权,为此,应首先在转让人与优先权人之间成立股权转让合同。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性质决定着该股权转让合同何时得以成立。此外,股权转让合同能够成立并在事实上得以履行还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 (一)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性质 依据我国《公司法》第71条第3款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对外转让时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而对于该项权利的法律定性仍然存在着争议,并进而形成了对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不同认识。迄今为止,对于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性质,主要存在着“请求权说”、“期待权说”和“形成权说”等几种代表性的观点。①本文认为,股东优先购买权是特别法上的形成权,但该种权利可以通过公司章程予以排除。 首先,股东优先购买权是形成权。形成权是依照权利人单方意志而使法律关系发生变动的权利,即“优先权人得依一方的意思表示形成以义务人和第三人买卖合同同等条件为内容的合同,无须义务人(所有权人或者出卖人)的承诺”。②在民法学的理论与司法实务中,对于优先购买权或先买权的性质的争议主要集中于形成权与请求权,主要是附强制缔约义务请求权的分歧。③商法学者对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性质的争论也主要是基于各种权利本身的特性。或许,我们也可以转换一下视角,从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制度价值出发,发现与其最为适合的权利性质的定位。 股东优先购买权不仅是使优先权人获得购买拟转让股权的机会,更是要优先于公司外的第三人获得股权本身,进而保持公司既有的股东结构,这便是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制度价值所在。有限责任公司是德国的法学家结合了无限公司和股份公司的特性而创造出来的一种公司类型,其不仅如股份公司一样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而且股东之间又具有如同无限公司一样的内部紧密关系,因此,有限责任公司天生便具有较强的人合性特点。为了维持公司既有的股东结构,保持股东之间的紧密联系,股东往往通过公司章程作出一定的安排,最为典型的是对股权对外转让作出限制,而赋予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即为常见的一种限制措施,这种限制体现为,如果其他股东主张优先购买权,则股权只能转让给优先权人,以阻止第三人进入公司。问题是,转让人能否对优先权人的主张进行抗辩?如果第三人再出高价,转让人能否再次要求优先权人选择?对此问题的回答直接与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定性有关。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就是将股东优先购买权定位为请求权;如果回答是否定的,则是将其定位为形成权。而哪一种定性更加符合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制度价值?这取决于哪一种定性能够让优先权人优先获得股权。而显然,只有将股东优先购买权定性为形成权,才可能实现优先权人优先于公司外第三人获得股权的制度价值。 股权转让是股东固有的权利,是股东处分其合法财产的自由行为,不应受到干涉。不可否认,将股东优先购买权定性为形成权,的确会影响股权对外转让,甚至也可以说是对转让人对外转让股权自由的“干涉”。然而,该种“干涉”仅仅是对转让对象的限制,并不会造成对转让人实质利益的损害。从股权转让人转让股权的目的来看,其转让股权是为了获得相对应的物质利益,即股权转让款,而至于由谁来支付该股权转让款,或者说股权转让给谁,不应构成转让人实质利益的内容。也有学者认为,股东优先购买权是附属于股东的股权转让权而产生的一种附属性的权利,将股东优先购买权定位为形成权,忽略了转让股东的转让利益,其他股东的利益则被置于转让人与受让人之上得到优越保护,而赋予转让股东“反悔权”,则在外部受让人与其他股东之间会形成价格竞争机制,最大限度实现转让股东的价格利益,也并不至于损害其他股东的既得利益。④ 本文认为,股东优先购买权并没有忽略转让人的利益,也没有将优先权人的利益凌驾于转让人与受让人之上。理由在于: 第一,优先权人主张优先购买权并不影响转让人对股权转让条件的心理预期。股权转让人在其他股东主张优先购买权时应该已经对股权转让条件形成了心理预期。股东优先购买权得以行使的前提是股权对外转让的基础关系存在。可以对外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才可以主张优先购买权。这意味着,在优先权人主张优先权时,股权对外转让的条件已经具备,股权转让人与公司外第三人之间已经就股权转让达成一致。也就是说,股权转让人不仅预先应对其拟转让股权有一个价值预期,而且在与第三人磋商过程中会就股权转让的条件进一步细化。双方能够就股权转让达成一致,说明该条件是符合股权转让人的心理预期的。此时,如果其他股东主张优先购买权,可以直接适用该条件,转让人对股权转让的价值预期并未受到影响。 第二,股权转让人与受让人能够事先阻止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的实现。股权转让人对于公司章程关于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规定必然是明知的,而基于《公司法》关于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标准规范也可以推定,第三人应该注意到公司章程有可能规定股东优先购买权,因此,无论是转让人还是受让人,均应知晓其他股东有主张优先购买权的可能,如果不想使他们之间的转让因其他股东主张优先购买权而受有影响,他们应该并能够事先采取措施。 第三,既然转让人与受让人可以事先阻止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实现,则可以认为,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赋予应优先考量优先权人的利益。从我国目前关于优先权的规定来看,优先权的赋予无一不是以优先权人与转让人之间特定的法律关系为前提,比如按份共有人之间的共有关系、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的租赁关系、合伙人之间以及股权转让人与其他股东之间的组织体成员关系等等。无论是法定优先权,还是意定优先权,其目的均在于限制转让人的转让自由,使优先权人获得转让标的物的所有权。而无论是将股东优先购买权定性为请求权,还是赋予转让人“反悔权”,都会阻碍这一目的实现。因此,股东优先购买权得以主张的前提是股权转让,但其并不附属于股权转让权,而是一项独立的权利,以使其他股东优先于公司外第三人获得股权。 其次,股东优先购买权是法定权利,但可以通过章程予以排除。“形成权”是对股东优先购买权本身性质的描述,因其规定于《公司法》之中,故而属于特别法上的形成权,然其能否最终为股东真正享有,则取决于公司章程的选择。 2005年《公司法》修改之后将原1993年《公司法》第35条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规定改为第72条(2014年变更为第71条),并增加了第4款,即“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正是该条款的加入,使得作为法定权利的股东优先购买权可以通过章程予以排除。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从字面意思上看,“另有规定”应该指的是不同于《公司法》条文的规定,这既包括宽松于《公司法》规定的条件,也包括严格于《公司法》规定的条件。对此,可以从与其他条文类似表述的比较中得出这一结论。《公司法》第141条第2款第3句规定:“公司章程可以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作出其他限制性规定。”该条虽然也赋予公司章程作出不同于《公司法》规定的权利,但是公司章程的其他规定仅限于“限制性规定”,而并不允许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毫无限制。显然,“另有规定”与“其他限制性规定”不能作同一含义的理解。 其次,从逻辑关系上看,《公司法》第71条一共有四个条款:第1款规定的是股权对内转让,第2款和第3款规定的是股权对外转让,须满足两个限制性条件,分别为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和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第4款并没有规定具体的股权转让的内容,而是针对该条前3款的内容,赋予公司通过章程“另行规定”的权利,即无论是股权对内转让,还是对外转让,均可以在章程中作出不同于《公司法》的规定,这当然包括排除股东的优先购买权。 最后,从权利的属性上看,权利人可依其意志自由处分其权利。如果全体股东在制定公司章程的时候一致同意排除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则可以看作是股东对其权利的自愿放弃,而不应认为是不合理的限制。当然,“章程初始条款中的股权转让限制,可以推定为获得了股东的同意;而章程的修订条款如果为股东转让股权设定了负担,则不能推定为获得了全体股东的同意,而必须经该修订条款拘束下的所有股东同意。”⑤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原则上赋予股权自由转让的特性,同时也允许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规定限制条件,以为股权对外转让设置障碍,“也可以事后通过章程修订引入股权限制转让条款,但是必须经过所有与此相关的成员的同意”。⑥ (二)股权转让合同成立的条件 基于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形成权的性质,在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对外转让的情况下,只要优先权人主张其权利,即会在转让人与优先权人之间成立股权转让合同关系。所以,股权转让合同成立的条件就是股权对外转让的基础事实和优先权人主张优先权。 1.股权对外转让的基础事实 “先买权并非在任意情况下均可行使,能促成先买权行使的根本条件,就是基础事实。”⑦具体到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其得以行使的前提即是转让人将其股权出卖给第三人。由于其他股东是在“同等条件下”对转让的股权享有优先购买权,因此在其主张优先购买权时,转让人与第三人之间至少已经就股权转让的基本条件达成一致,而是否已经实际签订合同倒在其次。如果转让人只是有股权转让的意向,并向其他股东表达其意向,其他股东表示愿意购买并与转让人达成一致,则与优先购买权无关;如果转让人向其他股东只是通知了其欲将股权转让给公司外第三人的意向,但尚未与第三人就股权转让形成合意,其他股东表示愿意购买并与转让人达成一致,也与优先购买权无关。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优先购买权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2008年)第2条规定:“股东依照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就股权转让事项征求其他股东同意的书面通知,应当包括拟受让人的有关情况、拟转让股权的数量、价格及履行方式等主要转让条件。通知中主要转让条件不明确,无法通过合同解释和补充方法予以明确的,视为未发出过书面通知。”这实际上即是在要求其他股东主张优先购买权的前提条件是转让人与第三人已经就股权转让的主要条件达成一致,而不仅仅是只有对外转让的意向。在转让人与公司外第三人就股权转让的条件已经基本达成一致,转让人就此通知其他股东该事实,其他股东主张优先购买权的,从其意思表示到达转让人时起,在转让人与优先权人之间成立股权转让合同。“这一合同的内容与转让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合同内容相同,相当于对另一合同的直接复制。这一合同的产生,虽然未经要约、承诺等缔约程序,也未形成书面合同的特定形式,但其是依照法律规定的原因产生,也具有有效合同的全部效力,当事人不得随意变更、撤销和解除。”⑧ 2.优先权人主张优先权 优先权人应该明确主张其优先购买权,即在转让人通知其股权对外转让及转让条件的时候,明确作出购买拟转让股权的意思表示。而有一个尚有争议的问题是,优先权人主张优先权是否应该有期限的限制?《公司法》第71条第3款并没有就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期限作出规定。实践中,转让人在向优先权人发出通知的时候,往往会在通知中限定优先权人回复并主张优先购买权的期限,并会载明“过期不主张则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对此种期限的法律效力,在股权转让纠纷处理的实践中存在着不同的认识。 在“北京永汇丰咨询有限公司(永汇丰公司)与被告中国冶金科工集团公司(科工公司)、北京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第三人北京百诚创信贸易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⑨一案中,科工公司欲将其持有的股权在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于是向永汇丰公司发出通知函,内容为:科工公司拟转让其持有的中冶公司40%的股权,并在产权交易所挂牌交易,故函告永汇丰公司,请永汇丰公司对其转让上述股权及是否有意购买上述股权进行回函,如通知函送达之日起30日内未回函,视为永汇丰公司同意其转让股权。挂牌交易后,科工公司再次给予永汇丰公司一份通知函,内容为:科工公司通知永汇丰公司,其转让中冶公司股权已在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交易,并已经产生一家意向受让方;如永汇丰公司在同等条件下行使优先购买权,请将转让价款1460万元交至产权交易所指定账户,并与科工公司签订产权交易合同;如在通知函送达之日起20日内未交付转让款,则视为其放弃优先购买权。法院认为,“在接到该通知后的法定期限内永汇丰公司并未主张其优先购买权,可视为其已经放弃,科工公司已经完成相应的通知义务予以认可,其转让程序合法有效”。 在“北京新奥特公司诉华融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⑩一案中,股权转让人华融公司于日向公司另一股东某电子公司发出“通知函”,不仅通报了拟转让股权比例、转让价格、付款期限等其与第三方新奥特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而且明确要求某电子公司在同年4月24日前就是否在上述条件下行使优先权作出明确答复,若某电子公司未能在此之前明确表示收购,则丧失优先购买权。某电子公司回函表示不放弃优先购买权,但同时提出对转让条件的反要求。日,华融公司通过公证向某电子公司发出“通知函”,再次通告了其与新奥特公司等达成的转让股权的条件,要求某电子公司于同年6月28日上午9:00前书面承诺是否以同等条件行使优先购买权,如承诺行使,则应于同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否则视为放弃优先权。某电子公司没有对此进行答复,于是华融公司于6月28日上午11:30与新奥特公司、比特科技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某电子公司申请北京仲裁委员会就其享有优先购买权作出裁决。北京仲裁委员会适用《民通意见》第66条来理解电子公司对华融公司第二次通知函的沉默的意思表示,认为不能理解成电子公司放弃了其优先购买权。(11)华融公司依此裁决与某电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也均以转让人已与优先权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转让人与第三人所签协议无法履行为由判定双方责任。 通过上述两个案例,我们看到了法院和仲裁机构对转让人设定的行使优先权的期限的不同处理。 在第一个案例中,法院认为优先权人未在“法定期限”内主张优先购买权,视为放弃权利。该“法定期限”所指何为,是《公司法》规定的30天的期限?还是转让人限定的20天的期限?从“法定”一词的使用上,该期限应该指的是前者。但是,《公司法》仅规定其他股东收到通知后30天内未回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并未明确将其确定为优先权人行使优先权的期限。而转让人限定的20天的期限,法院的判决虽未涉及,却又肯认了转让人通知函中超过20天期限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后果。法院的这种模糊处理方式,恰恰反映出其欲支持转让人设定优先权行使期限的效力,但又没有相应法律依据的尴尬。 而在第二个案例中,仲裁机构没有认清优先购买权的性质,也没有意识到商事交易的特点,僵化适用“沉默不构成意思表示”的民法规范,否定了转让人为优先权人设定权利行使期限的效力,裁决结果又成为法院一二审判决的基础,其裁判结果有待商榷。 首先,对于转让人华融公司发出的第一份通知函,优先权人某电子公司虽然表示不放弃优先购买权,但同时又不认可转让条件,这并不符合优先购买权形成权的特性。优先权人接到转让人的通知后,只能作出接受或者不接受转让条件的选择,前者会导致合同关系的成立,后者则意味着放弃优先权。如果允许优先权人就转让条件与转让人讨价还价,这一方面是无视转让人与第三人此前就股权转让达成的合意,另一方面则扩大了优先购买权的权限。因此,本文认为,不能依据第一份通知函认为优先权人已经主张了优先权。 其次,某电子公司的沉默实际上是一种权利的滥用。从4月15日到6月28日,电子公司有足够的时间考虑是否主张优先购买权,或者是否与华融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但是,电子公司虽然表示不放弃优先购买权,却没有进一步的行为,特别是在华融公司6月12日发函认为其已经放弃优先权,6月13日再次发函要求其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的情况下,仍然不作任何回复。如此情形,以沉默不构成意思表示来否定某电子公司放弃优先权的解释,实际上是纵容了某电子公司对时间的拖延和权利的滥用,对相信某电子公司放弃优先权,并为合同履行作出准备的转让人与第三人是不公平的,也徒劳增加股权转让的成本。 最后,从利益衡量的角度来看,转让人有权为优先权的行使设定期限。将股权转让人的股权处分权与优先权人的优先权进行利益衡量,前者更应受到保护。作为股权的所有者,股权转让人有权决定以何种价格将股权转让于谁,只是为了维护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和性,赋予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但该种权利只是使优先权人优先于公司外第三人获得股权,而并非剥夺股东转让股权的权利。因此,股权转让人有权为优先权的行使设定期限,其效力应得到承认,优先权人亦应遵守该期限,否则将视为放弃其优先权,这既是对转让人自由处分其财产的权利的尊重,也符合商事交易对快捷性的要求。 在上述两个案例中,法院和仲裁机构对于转让人设定的优先权行使期限的效力的认定均存在一定的问题。尽管《公司法》对于一般情况下的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期限没有作出规定,但是对于股权被强制执行时的股东优先购买权,则在《公司法》第72条明确规定了自法院通知之日起二十天的行权期限,期满不行使即视为放弃。鉴于两个条文规定的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同一性,如果公司章程或者转让人对优先权人的通知中规定或者明确了主张优先权的期限,则也应该与第72条作同样的解释,即优先权人未在规定的期限内主张优先权,则视为放弃权利,转让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合同得以履行,优先权人不能再主张优先权。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任国凤)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条
查看全部评论
中国社会科学网版权所有,未经书面授权禁止使用
Copyright (C)
by . all rights reserved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优先购买权的适用与限制之最新动态——《公司法》司法解释 (四) (征求意见稿) 专题系列研究之三
环球律师事务所 刘成伟
一、优先购买权的法律依据及内在逻辑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优先购买权(以下简称“优先购买权”)的直接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3年修订)(以下简称“《公司法》”)第71条,其具体规定如下: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
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
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
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就优先购买权的要求而言,《公司法》第71条的内在逻辑包含如下几个层面:
- 公司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股权。
- 公司对外转让时,应经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经同意转让的,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权。
- 公司章程可对上述程序另行规定。
优先购买权所侧重的是作为非转让方的“其他股东”的优先性权利。通常认为,优先购买权主要是基于对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特征而设置,目的之一在于维护股东之间的信赖关系。
本文认为,在现代公司治理架构下,有关优先购买权制度的理解与适用应综合考虑如下几方面因素:
- 兼顾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与“资合性”的双重属性特征,不宜习惯性过于偏向强调公司的“人合性”特征。
- 平衡公司的整体利益、拟转让方股东的利益、其他股东的利益以及债权人的利益,综合考虑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的保护以及交易的效率及安全性的维护。
- 从司法解释的角度而言,在结合实务经验而提供规则的统一适用支持的同时,司法解释应忠实于其所解释的标的法律。在《公司法》等上位法的规定修改之前,司法解释本身不宜作扩张性延展。
结合上述理念,下文笔者将对最高人民法院于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中有关优先购买权的相关规定(第22条至第29条)进行简要评析,并提出必要的修改建议。
二、优先购买权的适用限制
《征求意见稿》第22条、第23条规定,除公司章程另有明确规定以外,下列情形下的优先购买权主张不予支持:
- 股东因继承、遗赠而变更(第22条);
- 股东之间的转让(第23条)。
(一)股东之间的转让(第23条)
《征求意见稿》第23条明确,对于股东之间的转让,其他股东不享有优先购买权。这一适用理解从《公司法》第71条规定的内在逻辑也可以得到支持。《公司法》第71条在第3款对优先购买权进行了如下规定:“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而第3款是紧接第2款而来,第2款规定的是“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需要经过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公司法》第71条第1款规定的股东之间内部转让,则并未要求其他股东同意。也就是说,从《公司法》第71条的内在逻辑来看,优先购买权的适用范围仅限于那些需要“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即该条第2款所规定的“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而第1款所规定的股东之间内部转让,是本身并不需要其他股东同意的转让。因此,对于该等内部转让,并不具备适用优先购买权的前提。
《征求意见稿》第23条对上述理解予以了明确,也符合《公司法》第71条的内在逻辑,有助于司法实践中的适用统一,具有积极意义。本文赞成该条适用解释。
另一方面,《征求意见稿》第23条也重申了《公司法》第71条所确立的公司章程自治的基本原则。公司章程可对上述内容作出不同的规定。例如,章程可以规定,即便是公司股东之间的内部转让,也应取得其他股东或者某些股东(例如创始人股东)的同意;或者直接约定公司股东之间内部转让股权时,其他股东或者某些股东(例如创始人股东)具有优先购买权。此举可以防范股权向某一股东集中而打破之前股东合意的内部平衡,或者有助于巩固创始人股东对公司控制权的稳定。
(二)股东因继承、遗赠而变更(第22条)
本质上,因继承、遗赠而导致的股东变更并不是一种股权转让,更不是一种需要“经股东同意”的股权转让。“继承”及“遗赠”均是《继承法》项下的法定术语,是属于对遗产——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法》第3条)——的一种法定处置方式。也就是说,因继承、遗赠所导致的股东变更系由于法定事实的出现(即原股东的死亡)而依法形成的法定结果,不存在股权转让的意图或者合意。因此,按照《公司法》第71条的内在逻辑,该等情形下理论上不应存在优先购买权的问题。
《征求意见稿》第22条对上述理解予以了明确,也符合《公司法》第71条的内在逻辑,有助于司法实践中的适用统一,具有积极意义。本文赞成该条适用解释。
另一方面,从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的特征及维护原股东之间的信任关系的角度来看,如果公司章程明确规定了在继承、遗赠情形下,已“死亡”股东的股权应以合适的价格转让给其他股东,在不会因强制低价转让或其他原因形成对遗产继承人/遗赠对象合法权益的不当侵害的前提下,对公司章程的该等自治约定理应予以充分尊重。《征求意见稿》第22条也再次明确了此等情形下公司章程自治的基本原则。当然了,至于章程的自治约定是否会不当侵害遗产继承人/遗赠对象的合法权益,本文认为,该等内容已经超出了《公司法》的规制范畴,不宜在《公司法》的司法解释中处理。
需要提及的是,对于因《婚姻法》项下的离婚财产分割所导致的股东变更,虽其法律属性类似于遗产继承都是属于因法定事由的出现而形成的法律结果,但最高人民法院对于两类情形中的优先购买权的处理并不相同。在离婚财产分割中,对于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主张,法院的态度是支持的。具体而言,2003年12月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6条明确规定: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涉及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中以一方名义在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额,另一方不是该公司股东的,按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一)夫妻双方协商一致将出资额部分或者全部转让给该股东的配偶,过半数股东同意、其他股东明确表示放弃优先购买权的,该股东的配偶可以成为该公司股东;
(二)夫妻双方就出资额转让份额和转让价格等事项协商一致后,过半数股东不同意转让,但愿意以同等价格购买该出资额的,人民法院可以对转让出资所得财产进行分割。过半数股东不同意转让,也不愿意以同等价格购买该出资额的,视为其同意转让,该股东的配偶可以成为该公司股东。
用于证明前款规定的过半数股东同意的证据,可以是股东会决议,也可以是当事人通过其他合法途径取得的股东的书面声明材料。”
(三)不应适用优先购买权的其他情形
结合交易实务中遇到的相关情形以及争议解决中曾发生的相关案例情况,本文认为,本次《征求意见稿》还应增加有关条款明确,除非公司章程另有约定,对于下列特定情形下的优先购买权主张不予支持:
1. 股权出资
无论是从其税收递延、节约现金流还是其他商务优势考虑,股权出资正日益频繁地出现在公司的并购重组交易中,包括非上市公司的并购重组以及上市公司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等交易中。对于股权出资行为,就优先购买权的适用而言,是否有必要区分于普通的股权转让予以对待呢?对于这一点,理论界和实务界都是存在一些争议的。
针对股权出资,国家工商总局于2009年1月发布的《股权出资登记管理办法》及2014年2月修订的《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规定》(取代了2009年发布的《股权出资登记管理办法》),以及商务部于2012年9月发布的《涉及外商投资企业股权出资的暂行规定》,从基本要求及相关审批登记程序方面提供了具体的规范指引。但对于在股权出资行为中标的股权企业的其他股东是否拥有优先购买权,该等规范指引均未能明确。
严格讲,股权出资也是一种股权转让行为:由出资人(X)(即转让方)将其所持有的标的股权企业(A)的股权,转让给了被投资企业(B)(即受让方)以认购后者的增资。出资后,出资人(X)(即转让方)成为了被投资企业(B)(即受让方)的股东,而标的股权企业(A)则成了B的子公司。股权出资的基本交易结构如下图所示:
尽管从其经济属性来看,股权出资视同股权转让(税务处理上也是视同转让行为),但从优先购买权制度的设计针对两类交易行为所可能的不同法律效果来看,综合平衡拟转让股权的股东的利益以及交易的效率与安全等因素,本文认为,针对股权出资与股权转让两类交易行为中优先购买权的适用和限制还应区别对待。
一方面,股权转让的法律后果是,转让交易后,转让方不再持有所转让的股权,属于完全的退出;而股权出资的法律后果是,出资交易后,股权出资方仍通过被投资公司(B)间接享有对标的股权公司(A)的权益,并非完全的退出。另一方面,虽然从法律属性上讲二者都是属于股权的拥有方对其合法拥有的股权资产的一种处置方式,但就赋予标的股权公司(A)的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而言,同样的制度设计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法律效果:(1)在股权转让行为中,若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转让方将会获得与其向第三方转让同等价值的现金收益。因此,即便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对于转让方而言,其处置资产的权益并未受到实质影响;(2)而在股权出资行为中,若允许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则可能会从根本上改变股权拥有方对其资产处置方式的真实意愿。这是因为,若允许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也就意味着股权出资方必须将股权转让给该其他股东,而导致股权出资方必须退出变现。但实际情况却是,股权出资方之所以同意以股权出资,其真实意图并非是要退出,而是看重了被投资公司的未来增长价值,因而以现有标的股权公司(A)的股权去换取被投资公司(B)的股权。这样,股权出资方不仅并未完全退出,而且还继续通过被投资公司间接享有原来所出资股权的相关权益,同时还可以享受被投资公司未来的价值增长。因此,在股权出资行为中,若允许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不仅可能完全背离了股权拥有方并不想退出的真实意思,而且也剥脱了股权出资方想通过股权出资方式换取被投资公司未来增长价值的初衷,对股权出资方的权益会构成实质损害。
其实,有关监管机关可能已经关注到了股权出资与股权转让之间的重要区别。因此,无论是适用于外商投资企业股权出资的《商务部关于涉及外商投资企业股权出资的暂行规定》(商务部令2012年第8号),还是国家工商总局颁发的《股权出资登记管理办法》及后续修订的《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规定》,针对股权出资办理相关审批登记手续时,商务部门及工商局均未要求股权出资方需要提交其他股东的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函或同意书。相反,针对股权转让,有关规定则是明确要求提交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放弃函或同意书的。
综上,本文认为,股权出资与股权转让,二者从内在特征上还是有重要区别的。本文建议,《征求意见稿》宜增加相关条款明确规定,除非公司章程另有约定,对于股权出资交易中的其他股东要求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应不予支持。
2. 间接转让/股东的实际控制人变更
对于间接转让(即通过出售标的公司(X)的股东(Y)的股权(由转让方Z持有),而实现间接转让Y所持有的标的公司X的股权),尤其是当交易导致股东Y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时,是否应允许标的公司X的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对于这一问题,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存在较大的争议。
这一问题的争议在著名的上海外滩地王一案后更加明显。关于上海外滩地王案以及该案中所诉争的间接转让中是否应保护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问题,已有诸多论述。该等论述中,笔者比较倾向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彭冰博士在其发表于《清华法学》(Vol.
10, No. 1 (2016))的《股东优先购买权与间接收购的利益衡量》一文已所阐释的观点。对于该文的非常详尽分析与阐释,本文在此不再赘述。本文在此援引一下该文的结论性观点供参考:“以转让公司的方式转移公司名下的财产和合同权益,是公司作为一种组织形态本身的特性,有其独特的经济价值,应该得到尊重。除了基于公共利益的监管要求而有特别立法规定外,对于某些个人化的权益不应通过‘刺破’公司转让的交易形式加以特别保护,而应通过当事人之间的协议约定实现自我保护。”
简言之,本文认为,针对公司(X)的母公司或某一股东(Y)层面的股权转让或该等股东的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形,除非X公司的章程明确规定了该等情形下有关优先购买权的相关规则,否则,该等情形下不宜允许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试想,在公司章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形下,针对在公司的股东Y层面的股权转让或实际控制人变更,如果允许X公司的“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那么该等权利行使的对象是什么呢?是允许该等其他股东收购发生股权转让或实际控制人变更的股东Y的股权吗?如果是,此时该股东Y公司自身的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又如何保障呢?考虑到间接转让/股东的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情形比较复杂,本文建议,在相关讨论充分明确进而形成相对统一的意见以前,本次《征求意见稿》可以暂时不涉及该等情形下的优先购买权问题。司法实践中,本文倾向认为,除非公司章程另有明确约定或者案件具体情况另有反向证据支持,否则该等情形下的其他股东主张优先购买权时,应不予支持。
三、优先购买权的行使程序
《征求意见稿》第24条、第25条对优先购买权行使过程中涉及的一些程序性细节进行了明确,有助于实务规范及司法实践的统一。对于该部分内容,本文整体认同,仅对“同等条件”的界定方面有个别补充完善建议:
“同等条件”的界定(第24条)
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公司法》第71条第3款规定的“在同等条件下”。如果条件不同,也就无从谈起优先权。因此,如何界定这个“同等条件”对于优先购买权的行使基础而言尤为重要。
在这方面,《征求意见稿》第24条规定,应从“转让价格、付款方式及期限等因素”综合考虑;并且进一步明确,对于其他股东只想受让“部分”拟转让的股权而不是全部受让的,也不构成“同等条件”,因此不予支持,除非章程另有规定。这些内容都是实务交易环节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尤其从转让方的角度来看。本文想补充的是,在界定“同等条件”时,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交易的确定性”。
具体而言,其他股东与拟受让的第三方相比,谁的资信能力或付款能力更有保障?谁的身份性质更有利于交易的顺利交割?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因素。尤其从转让方的利益角度来看,转让方当然会更倾向于有利于交易顺利交割的交易对方。因此,交易的确定性也应是判断拟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其他股东的出价是否与第三方的出价处于“同等条件下”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这样也更显公平。例如,在特定行业,尤其是要求国有控股的行业,如果拟受让的第三方是国有企业,而想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公司其他股东是外资股东或民营股东,显然转让给国有企业更有利于交易的审批通过。再比如,在外方股东拟转让股权的情形中,如果拟受让的第三方同样是外国投资者,而想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其他股东是中方股东,这种情况下似乎前者更有利于交易的确定性。很多情况下,转让给第三方外国投资者对于拟转让股权的该外方股东而言可能属于更优越的条件,这一方面是考虑到不同时期的汇率汇兑损益,另一方面还涉及到目前的外汇政策项下资本项目对外支付的程序便利性问题。
因此,本文建议,《征求意见稿》第24条可以修改为“应当综合股权的转让价格、付款方式及期限以及交易的确定性等因素”。
四、转让的放弃与无效
《征求意见稿》第26条规定,在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时,允许拟转让方放弃转让,除非已与其他股东达成转让协议或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本文对该条的规定比较认同。这也是对拟转让方的财产处置权的充分尊重。
而在股权转让程序(包括优先购买权的保障方面)存在瑕疵而导致与第三方的股权转让行为被认定为无效时,《征求意见稿》第27条第2款则又支持“其他股东同时请求按照实际交易条件购买该股权”。这种情形下为何不再允许拟转让方放弃转让呢?这岂不是强买强卖!允许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的权利等级高于拟转让方的“财产处置权”,其逻辑和法律依据在哪里呢?对于转让方而言,在其与第三方的转让合同被认定为无效的情况下,允许该转让方放弃转让理应是其财产处置权的应有之义。这种情况下,如果连国家基于公共利益进行征收的法律基础都尚不存在的话,反而却允许基于“优先购买权”的行使而介入的其他股东按同等条件强行购买。其逻辑实在是讲不通。
如果从维护交易的安全性及禁止反言(equitable estoppel)原则来看,其逻辑前提同样不存在。因为与第三方的交易已经被认定为无效了,而与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其他股东又尚未达成协议,这种情况下由法院硬撮合出来一个不情不愿的所谓“交易”,实质上并不是维护交易的安全。因为这里并无“交易”是经过合意而达成的。另一方面,禁止反言也是有相对性的。被否定的前序交易中的“言”是针对已报价的第三方的,而该等交易既然已被认定为无效了,那么对于其他股东而言,拟转让方不见得会发出同样的“言”。既然如此,也就无“言”可反,就没有禁止反言原则的适用基础。
仔细看来,《征求意见稿》第27条支持“其他股东同时请求按照实际交易条件购买该股权”,其理论基础可能是目前相对较为普遍接受的关于优先购买权从性质上讲是一种“形成权”的学界观点(即可以按照优先购买权的权利主张人的单方意志—同等条件/实际条件—而改变法律关系)。但是,这一规定实际上是混淆了优先购买权语境(context)下的“同等条件”。本文认为,除非公司章程有更详细具体的操作性规定另有所指,《公司法》第71条项下的优先购买权实质上更接近于英美法项下的优先受让权right
refusal(按《布莱克法律词典》的解释,该等权利是一种与第三方出价进行配对match/meet的权利),而不是一种优先报价权right
of first offer。至少在目前的《公司法》第71条规定的框架下,股权转让时,除非公司章程另有明确规定,优先购买权并不是要求必须先通知其他股东而给该股东一个优先出价权;而是指当第三方出价后再通知其他股东,以给其他股东一个按第三方报价的同等条件进行出价购买的机会。也就是说。此处的“同等条件”实际上是在第三方出价时由拟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其他股东”提出的match/meet配对条件,而不是反过来由拟转让方向其他股东主动来提出的。股权转让交易中,除了与已报价的第三方是主动交易并形成“合意”以外,拟转让股权的股东并未主动向任何其他方(包括其他股东)提出所谓的“同等条件”。因此,在先前的主动交易被认定为无效的前提下,拟转让方也不应受到所谓的“同等条件”的约束或禁止反言,因为这个条件并不是该转让方所提出来的。
简言之,即便由于影响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一些瑕疵而导致转让方与第三方的交易被确认为无效,这种情况下,也应充分尊重拟转让方的财产处置权,同样允许其放弃转让。其实,本文认为,《征求意见稿》整个第27条第1款关于认定转让合同无效的逻辑和法律依据同样也很有问题。该第1款规定如下: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有下列损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情形之一,其他股东请求确认转让合同无效的,应予支持:
(一)未履行公司法和司法解释规定的程序订立股权转让合同;
(二)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后,股东采取减少转让价款等方式实质改变公司法和司法解释规定的同等条件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
(三)股东与股东以外的人恶意串通,采取虚报高价等方式违反公司法和司法解释规定的同等条件,导致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但是双方的实际交易条件低于书面通知的条件。”
在现行中国法项下,合同(包括股权转让合同)无效的法律依据应是《合同法》第52条,该条规定如下: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结合《合同法》第52条有关合同无效的规定,下文我们就来逐项分析《征求意见稿》第27条第1款的逻辑偏颇及法律依据缺失:
(一)未履行公司法和司法解释规定的程序订立股权转让合同
关于“未履行公司法和司法解释规定的程序”,如果从合同无效的角度来看,最接近的法律依据应是《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关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要求。因此,这里至少应区分一下所违反的这些规定程序究竟是强制性的还是规范性的。若只是违反了规范性的非强制程序,则不见得就导致合同无效。另一个可供参考的例证是,《公司法》第22条明确区分了决议内容的违反与决议程序的违反的不同处理方式。按照《公司法》第22条,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只有在“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才会无效;而当“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时,则是属于可请求人民法院撤销的情形,而不是合同当然无效,而且有关股东应在相关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申请撤销。
因此,《征求意见稿》第27条第1款(一)将违反程序视为请求确认转让合同无效的基础,无论从《合同法》还是《公司法》的规定来看,都缺乏法律依据。而且,仅仅因为违反程序便轻易否定交易的效力,明显不利于维护交易的安全性。
(二)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后,股东采取减少转让价款等方式实质改变公司法和司法解释规定的同等条件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
(三)股东与股东以外的人恶意串通,采取虚报高价等方式违反公司法和司法解释规定的同等条件,导致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但是双方的实际交易条件低于书面通知的条件。
从合同无效的角度来看,与《征求意见稿》第27条1款上述第(二)、(三)项规定最接近的法律依据应是《合同法》第52条第(二)项关于“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规定。上述第(二)、(三)项规定的法律依据似乎没有问题。从《公司法》第71条规定的优先购买权的内在逻辑来看,这种情况下的问题实质在于改变了“同等条件”。因此,本文认为,这里应区分一下两种不同的情形:在其他股东放弃了优先购买权,而拟转让的股东后来减少价款或实际交易条件低于给其他股东的书面通知所载的条件或以其他方式改变同等条件时,(1)如果拟转让方在后续变更条件时再一次通知了其他股东,其他股东未在规定期限内答复或又一次放弃了优先购买权的,那么此时的程序并无瑕疵,并不存在应导致转让合同被确认为无效的基础;(2)另一方面,即便拟转让方在后续变更条件时并未通知其他股东,从维护交易的安全性原则出发,在诉讼过程中也应给予原交易项下的第三方受让方再次提高报价以按照原转让合同的条款约定执行并通知其他股东是否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机会,而不宜直接确认合同无效。
五、限制股权转让的章程条款的效力
《征求意见稿》第29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章程条款过度限制股东转让股权,导致股权实质上不能转让,股东请求确认该条款无效的,应予支持。”
本文认为,《征求意见稿》第29条的上述规定明显超出了司法解释的授权范围,与《公司法》第71条的规定相悖,缺乏法律依据。首先,如文首所提,《公司法》第71条最后一款明确规定:“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此处,何为公司章程的“另有规定”,《公司法》并未作任何限制性要求。该等另有规定,在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冲突的情况下,可以是更为宽松的或者更为严格的要求,只要是股东之间自愿达成合意,就应充分予以尊重。其次,从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属性来看,只要是股东之间同意,完全可以在章程条款中明确约定公司存续期间或其他特定期间内禁止全部股东或某类股东转让股权。实务中,从维护公司股权结构稳定性的角度,章程中约定创始人股东在上市之前不得转让或股东在公司成立后几年内不得转让的情形也并不少见。另外,究竟什么是“过度限制”股东转让股权,如何界定?难道一年内或三年内不得转让不算过度,五年内不得转让或上市前(可能是三年、五年或更长时间)就属于过度了?可以理解,随着公司发展情况的演变,尤其是当公司经营不善时,一些股东萌生退意也属正常。此时若还在章程若明确约定的锁定期内,该类股东的退出权会受到一定限制,《征求意见稿》第29条的规定便提供了权利依据。但这些情形下,其实《公司法》已给了相应的救济安排了,比如《公司法》第75条规定的回购请求权,以及依据《公司法》第182条请求法院解散公司。
本质上,公司章程是股东之间的一种合同约定。因此,章程条款的无效也应根据《合同法》第52条的有关内容判断。不可否认,对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是否应具有流动性或者说章程中禁止股权转让的条款的效力,目前理论界及实务界都还存在争议。本文认为,在《公司法》并未明确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必须具有流动性的情况下,尤其是《公司法》第71条第4款明确规定了“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因此即便章程条款“过度限制股东转让股权,导致股权实质上不能转让”,也没有与强制性规范相抵触。这种情况下,支持拟退出的股东请求确认此类章程条款的无效,缺乏法律依据,除非该等股东能进一步证明其当初签署章程时属于被其他股东“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胁迫订立,或者能够证明具有《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其他情形。
本文认为,《公司法》第71条第4款已明确建立了章程自治原则,而有限责任公司又具有“人合性”属性和相对的封闭性特征,《征求意见稿》第29条所顾虑的因素完全可以通过《合同法》第52条或《公司法》相应条款(比如第75条规定的回购请求权、第182条规定的请求法院解散公司)予以解决。因此,本文建议,《征求意见稿》第29条应予以整体删除,因为该条规定明显超出了司法解释的授权范围,与《公司法》第71条的规定相悖,缺乏法律依据。(完)
文章来源:环球律师事务所微信平台
计兮App-读懂资本市场}
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效力 股权转让/股权变动
日 09:27 来源:《环球法律评论》(京)2015年第20154期第35-48页
作者:胡晓静
内容摘要: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胡晓静,吉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内容提要: 股东优先购买权是公司法上的特别形成权,该种权利可以通过公司章程予以排除。股权转让合同成立的条件是股权对外转让的基础事实和优先权人主张优先权。如果优先权人主张优先权,则在转让人与优先权人之间成立以转让人与第三人之间合同为内容的股权转让合同,但前提条件是转让人与第三人已经就股权转让合同的主要条件达成一致。而对于转让人与第三人之间先前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不因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而影响其效力,但是,该合同无法履行。从优先权人主张优先权时起,股权发生变动。如果未通知优先权人即将股权转让于第三人并进行了股东名册或者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优先权人主张优先权的,原则上能够对抗第三人,但是,如果变更登记时间已经超过三年,或者会损害他人利益的除外。 Shareholders' right of preemption is a special right of formation under company law,which could be excluded through the bylaws of a company.The basic fact of external transfer of equity and the claim for the right of preemption by a holder of such right are the precondition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equity transfer contract.The claim for the right of preemption by a holder of such right establishes between the transferor and the claimant a contract on the transfer of equity that takes the contract between the transferor and a third person as its content,provided that an agreement has already been reached between the transferor and the third parson on the main terms of the contract on the transfer of equity.As for the contract on the transfer of equity concluded between a transferor and a third party before the claim of the right of preemption is made,its effect is not affected by such claim,although the contract is unable to be implemented.The transfer of equity occurs when a claim for the right of preemption is made by a holder of such right.In circumstances where equity is transferred to a third party and the transfer is registered in the register of shareholders or with an organ in charge of corporation registration without notifying the holder of the fight of preemption,the claim for the right of preemption by a holder of such right should in principle have the effect against the third party,unless the registration of the transfer had been made more than three yeas a 关 键 词: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股权变动 为了维持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我国《公司法》规定了股权对外转让时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而恰恰是股东优先购买权问题,不仅成为股权转让纠纷频发的元凶之一,也成为司法审判实务中困扰法官的疑难问题。在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对外转让的情况下,如果其他股东主张优先购买权,是否及如何在转让人与优先权人之间成立股权转让合同?转让人与第三人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是否会因此受到影响?优先权人主张了优先购买权之后,能否获得股权?这些问题实际上都可以归为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效力问题,即在优先权人主张优先权的情况下,转让人与优先权人之间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转让人与第三人之间先合同的效力和股权变动的效力都是何种情况。下面,将分别对股东优先购买权的三个方面的效力进行分析。 一 转让人与优先权人之间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 股东优先购买权人主张优先购买权意在获得股权,为此,应首先在转让人与优先权人之间成立股权转让合同。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性质决定着该股权转让合同何时得以成立。此外,股权转让合同能够成立并在事实上得以履行还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 (一)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性质 依据我国《公司法》第71条第3款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对外转让时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而对于该项权利的法律定性仍然存在着争议,并进而形成了对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不同认识。迄今为止,对于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性质,主要存在着“请求权说”、“期待权说”和“形成权说”等几种代表性的观点。①本文认为,股东优先购买权是特别法上的形成权,但该种权利可以通过公司章程予以排除。 首先,股东优先购买权是形成权。形成权是依照权利人单方意志而使法律关系发生变动的权利,即“优先权人得依一方的意思表示形成以义务人和第三人买卖合同同等条件为内容的合同,无须义务人(所有权人或者出卖人)的承诺”。②在民法学的理论与司法实务中,对于优先购买权或先买权的性质的争议主要集中于形成权与请求权,主要是附强制缔约义务请求权的分歧。③商法学者对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性质的争论也主要是基于各种权利本身的特性。或许,我们也可以转换一下视角,从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制度价值出发,发现与其最为适合的权利性质的定位。 股东优先购买权不仅是使优先权人获得购买拟转让股权的机会,更是要优先于公司外的第三人获得股权本身,进而保持公司既有的股东结构,这便是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制度价值所在。有限责任公司是德国的法学家结合了无限公司和股份公司的特性而创造出来的一种公司类型,其不仅如股份公司一样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而且股东之间又具有如同无限公司一样的内部紧密关系,因此,有限责任公司天生便具有较强的人合性特点。为了维持公司既有的股东结构,保持股东之间的紧密联系,股东往往通过公司章程作出一定的安排,最为典型的是对股权对外转让作出限制,而赋予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即为常见的一种限制措施,这种限制体现为,如果其他股东主张优先购买权,则股权只能转让给优先权人,以阻止第三人进入公司。问题是,转让人能否对优先权人的主张进行抗辩?如果第三人再出高价,转让人能否再次要求优先权人选择?对此问题的回答直接与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定性有关。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就是将股东优先购买权定位为请求权;如果回答是否定的,则是将其定位为形成权。而哪一种定性更加符合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制度价值?这取决于哪一种定性能够让优先权人优先获得股权。而显然,只有将股东优先购买权定性为形成权,才可能实现优先权人优先于公司外第三人获得股权的制度价值。 股权转让是股东固有的权利,是股东处分其合法财产的自由行为,不应受到干涉。不可否认,将股东优先购买权定性为形成权,的确会影响股权对外转让,甚至也可以说是对转让人对外转让股权自由的“干涉”。然而,该种“干涉”仅仅是对转让对象的限制,并不会造成对转让人实质利益的损害。从股权转让人转让股权的目的来看,其转让股权是为了获得相对应的物质利益,即股权转让款,而至于由谁来支付该股权转让款,或者说股权转让给谁,不应构成转让人实质利益的内容。也有学者认为,股东优先购买权是附属于股东的股权转让权而产生的一种附属性的权利,将股东优先购买权定位为形成权,忽略了转让股东的转让利益,其他股东的利益则被置于转让人与受让人之上得到优越保护,而赋予转让股东“反悔权”,则在外部受让人与其他股东之间会形成价格竞争机制,最大限度实现转让股东的价格利益,也并不至于损害其他股东的既得利益。④ 本文认为,股东优先购买权并没有忽略转让人的利益,也没有将优先权人的利益凌驾于转让人与受让人之上。理由在于: 第一,优先权人主张优先购买权并不影响转让人对股权转让条件的心理预期。股权转让人在其他股东主张优先购买权时应该已经对股权转让条件形成了心理预期。股东优先购买权得以行使的前提是股权对外转让的基础关系存在。可以对外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才可以主张优先购买权。这意味着,在优先权人主张优先权时,股权对外转让的条件已经具备,股权转让人与公司外第三人之间已经就股权转让达成一致。也就是说,股权转让人不仅预先应对其拟转让股权有一个价值预期,而且在与第三人磋商过程中会就股权转让的条件进一步细化。双方能够就股权转让达成一致,说明该条件是符合股权转让人的心理预期的。此时,如果其他股东主张优先购买权,可以直接适用该条件,转让人对股权转让的价值预期并未受到影响。 第二,股权转让人与受让人能够事先阻止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的实现。股权转让人对于公司章程关于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规定必然是明知的,而基于《公司法》关于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标准规范也可以推定,第三人应该注意到公司章程有可能规定股东优先购买权,因此,无论是转让人还是受让人,均应知晓其他股东有主张优先购买权的可能,如果不想使他们之间的转让因其他股东主张优先购买权而受有影响,他们应该并能够事先采取措施。 第三,既然转让人与受让人可以事先阻止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实现,则可以认为,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赋予应优先考量优先权人的利益。从我国目前关于优先权的规定来看,优先权的赋予无一不是以优先权人与转让人之间特定的法律关系为前提,比如按份共有人之间的共有关系、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的租赁关系、合伙人之间以及股权转让人与其他股东之间的组织体成员关系等等。无论是法定优先权,还是意定优先权,其目的均在于限制转让人的转让自由,使优先权人获得转让标的物的所有权。而无论是将股东优先购买权定性为请求权,还是赋予转让人“反悔权”,都会阻碍这一目的实现。因此,股东优先购买权得以主张的前提是股权转让,但其并不附属于股权转让权,而是一项独立的权利,以使其他股东优先于公司外第三人获得股权。 其次,股东优先购买权是法定权利,但可以通过章程予以排除。“形成权”是对股东优先购买权本身性质的描述,因其规定于《公司法》之中,故而属于特别法上的形成权,然其能否最终为股东真正享有,则取决于公司章程的选择。 2005年《公司法》修改之后将原1993年《公司法》第35条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规定改为第72条(2014年变更为第71条),并增加了第4款,即“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正是该条款的加入,使得作为法定权利的股东优先购买权可以通过章程予以排除。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从字面意思上看,“另有规定”应该指的是不同于《公司法》条文的规定,这既包括宽松于《公司法》规定的条件,也包括严格于《公司法》规定的条件。对此,可以从与其他条文类似表述的比较中得出这一结论。《公司法》第141条第2款第3句规定:“公司章程可以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作出其他限制性规定。”该条虽然也赋予公司章程作出不同于《公司法》规定的权利,但是公司章程的其他规定仅限于“限制性规定”,而并不允许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毫无限制。显然,“另有规定”与“其他限制性规定”不能作同一含义的理解。 其次,从逻辑关系上看,《公司法》第71条一共有四个条款:第1款规定的是股权对内转让,第2款和第3款规定的是股权对外转让,须满足两个限制性条件,分别为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和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第4款并没有规定具体的股权转让的内容,而是针对该条前3款的内容,赋予公司通过章程“另行规定”的权利,即无论是股权对内转让,还是对外转让,均可以在章程中作出不同于《公司法》的规定,这当然包括排除股东的优先购买权。 最后,从权利的属性上看,权利人可依其意志自由处分其权利。如果全体股东在制定公司章程的时候一致同意排除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则可以看作是股东对其权利的自愿放弃,而不应认为是不合理的限制。当然,“章程初始条款中的股权转让限制,可以推定为获得了股东的同意;而章程的修订条款如果为股东转让股权设定了负担,则不能推定为获得了全体股东的同意,而必须经该修订条款拘束下的所有股东同意。”⑤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原则上赋予股权自由转让的特性,同时也允许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规定限制条件,以为股权对外转让设置障碍,“也可以事后通过章程修订引入股权限制转让条款,但是必须经过所有与此相关的成员的同意”。⑥ (二)股权转让合同成立的条件 基于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形成权的性质,在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对外转让的情况下,只要优先权人主张其权利,即会在转让人与优先权人之间成立股权转让合同关系。所以,股权转让合同成立的条件就是股权对外转让的基础事实和优先权人主张优先权。 1.股权对外转让的基础事实 “先买权并非在任意情况下均可行使,能促成先买权行使的根本条件,就是基础事实。”⑦具体到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其得以行使的前提即是转让人将其股权出卖给第三人。由于其他股东是在“同等条件下”对转让的股权享有优先购买权,因此在其主张优先购买权时,转让人与第三人之间至少已经就股权转让的基本条件达成一致,而是否已经实际签订合同倒在其次。如果转让人只是有股权转让的意向,并向其他股东表达其意向,其他股东表示愿意购买并与转让人达成一致,则与优先购买权无关;如果转让人向其他股东只是通知了其欲将股权转让给公司外第三人的意向,但尚未与第三人就股权转让形成合意,其他股东表示愿意购买并与转让人达成一致,也与优先购买权无关。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优先购买权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2008年)第2条规定:“股东依照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就股权转让事项征求其他股东同意的书面通知,应当包括拟受让人的有关情况、拟转让股权的数量、价格及履行方式等主要转让条件。通知中主要转让条件不明确,无法通过合同解释和补充方法予以明确的,视为未发出过书面通知。”这实际上即是在要求其他股东主张优先购买权的前提条件是转让人与第三人已经就股权转让的主要条件达成一致,而不仅仅是只有对外转让的意向。在转让人与公司外第三人就股权转让的条件已经基本达成一致,转让人就此通知其他股东该事实,其他股东主张优先购买权的,从其意思表示到达转让人时起,在转让人与优先权人之间成立股权转让合同。“这一合同的内容与转让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合同内容相同,相当于对另一合同的直接复制。这一合同的产生,虽然未经要约、承诺等缔约程序,也未形成书面合同的特定形式,但其是依照法律规定的原因产生,也具有有效合同的全部效力,当事人不得随意变更、撤销和解除。”⑧ 2.优先权人主张优先权 优先权人应该明确主张其优先购买权,即在转让人通知其股权对外转让及转让条件的时候,明确作出购买拟转让股权的意思表示。而有一个尚有争议的问题是,优先权人主张优先权是否应该有期限的限制?《公司法》第71条第3款并没有就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期限作出规定。实践中,转让人在向优先权人发出通知的时候,往往会在通知中限定优先权人回复并主张优先购买权的期限,并会载明“过期不主张则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对此种期限的法律效力,在股权转让纠纷处理的实践中存在着不同的认识。 在“北京永汇丰咨询有限公司(永汇丰公司)与被告中国冶金科工集团公司(科工公司)、北京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第三人北京百诚创信贸易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⑨一案中,科工公司欲将其持有的股权在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于是向永汇丰公司发出通知函,内容为:科工公司拟转让其持有的中冶公司40%的股权,并在产权交易所挂牌交易,故函告永汇丰公司,请永汇丰公司对其转让上述股权及是否有意购买上述股权进行回函,如通知函送达之日起30日内未回函,视为永汇丰公司同意其转让股权。挂牌交易后,科工公司再次给予永汇丰公司一份通知函,内容为:科工公司通知永汇丰公司,其转让中冶公司股权已在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交易,并已经产生一家意向受让方;如永汇丰公司在同等条件下行使优先购买权,请将转让价款1460万元交至产权交易所指定账户,并与科工公司签订产权交易合同;如在通知函送达之日起20日内未交付转让款,则视为其放弃优先购买权。法院认为,“在接到该通知后的法定期限内永汇丰公司并未主张其优先购买权,可视为其已经放弃,科工公司已经完成相应的通知义务予以认可,其转让程序合法有效”。 在“北京新奥特公司诉华融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⑩一案中,股权转让人华融公司于日向公司另一股东某电子公司发出“通知函”,不仅通报了拟转让股权比例、转让价格、付款期限等其与第三方新奥特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而且明确要求某电子公司在同年4月24日前就是否在上述条件下行使优先权作出明确答复,若某电子公司未能在此之前明确表示收购,则丧失优先购买权。某电子公司回函表示不放弃优先购买权,但同时提出对转让条件的反要求。日,华融公司通过公证向某电子公司发出“通知函”,再次通告了其与新奥特公司等达成的转让股权的条件,要求某电子公司于同年6月28日上午9:00前书面承诺是否以同等条件行使优先购买权,如承诺行使,则应于同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否则视为放弃优先权。某电子公司没有对此进行答复,于是华融公司于6月28日上午11:30与新奥特公司、比特科技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某电子公司申请北京仲裁委员会就其享有优先购买权作出裁决。北京仲裁委员会适用《民通意见》第66条来理解电子公司对华融公司第二次通知函的沉默的意思表示,认为不能理解成电子公司放弃了其优先购买权。(11)华融公司依此裁决与某电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也均以转让人已与优先权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转让人与第三人所签协议无法履行为由判定双方责任。 通过上述两个案例,我们看到了法院和仲裁机构对转让人设定的行使优先权的期限的不同处理。 在第一个案例中,法院认为优先权人未在“法定期限”内主张优先购买权,视为放弃权利。该“法定期限”所指何为,是《公司法》规定的30天的期限?还是转让人限定的20天的期限?从“法定”一词的使用上,该期限应该指的是前者。但是,《公司法》仅规定其他股东收到通知后30天内未回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并未明确将其确定为优先权人行使优先权的期限。而转让人限定的20天的期限,法院的判决虽未涉及,却又肯认了转让人通知函中超过20天期限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后果。法院的这种模糊处理方式,恰恰反映出其欲支持转让人设定优先权行使期限的效力,但又没有相应法律依据的尴尬。 而在第二个案例中,仲裁机构没有认清优先购买权的性质,也没有意识到商事交易的特点,僵化适用“沉默不构成意思表示”的民法规范,否定了转让人为优先权人设定权利行使期限的效力,裁决结果又成为法院一二审判决的基础,其裁判结果有待商榷。 首先,对于转让人华融公司发出的第一份通知函,优先权人某电子公司虽然表示不放弃优先购买权,但同时又不认可转让条件,这并不符合优先购买权形成权的特性。优先权人接到转让人的通知后,只能作出接受或者不接受转让条件的选择,前者会导致合同关系的成立,后者则意味着放弃优先权。如果允许优先权人就转让条件与转让人讨价还价,这一方面是无视转让人与第三人此前就股权转让达成的合意,另一方面则扩大了优先购买权的权限。因此,本文认为,不能依据第一份通知函认为优先权人已经主张了优先权。 其次,某电子公司的沉默实际上是一种权利的滥用。从4月15日到6月28日,电子公司有足够的时间考虑是否主张优先购买权,或者是否与华融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但是,电子公司虽然表示不放弃优先购买权,却没有进一步的行为,特别是在华融公司6月12日发函认为其已经放弃优先权,6月13日再次发函要求其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的情况下,仍然不作任何回复。如此情形,以沉默不构成意思表示来否定某电子公司放弃优先权的解释,实际上是纵容了某电子公司对时间的拖延和权利的滥用,对相信某电子公司放弃优先权,并为合同履行作出准备的转让人与第三人是不公平的,也徒劳增加股权转让的成本。 最后,从利益衡量的角度来看,转让人有权为优先权的行使设定期限。将股权转让人的股权处分权与优先权人的优先权进行利益衡量,前者更应受到保护。作为股权的所有者,股权转让人有权决定以何种价格将股权转让于谁,只是为了维护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和性,赋予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但该种权利只是使优先权人优先于公司外第三人获得股权,而并非剥夺股东转让股权的权利。因此,股权转让人有权为优先权的行使设定期限,其效力应得到承认,优先权人亦应遵守该期限,否则将视为放弃其优先权,这既是对转让人自由处分其财产的权利的尊重,也符合商事交易对快捷性的要求。 在上述两个案例中,法院和仲裁机构对于转让人设定的优先权行使期限的效力的认定均存在一定的问题。尽管《公司法》对于一般情况下的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期限没有作出规定,但是对于股权被强制执行时的股东优先购买权,则在《公司法》第72条明确规定了自法院通知之日起二十天的行权期限,期满不行使即视为放弃。鉴于两个条文规定的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同一性,如果公司章程或者转让人对优先权人的通知中规定或者明确了主张优先权的期限,则也应该与第72条作同样的解释,即优先权人未在规定的期限内主张优先权,则视为放弃权利,转让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合同得以履行,优先权人不能再主张优先权。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任国凤)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条
查看全部评论
中国社会科学网版权所有,未经书面授权禁止使用
Copyright (C)
by . all rights reserved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优先购买权的适用与限制之最新动态——《公司法》司法解释 (四) (征求意见稿) 专题系列研究之三
环球律师事务所 刘成伟
一、优先购买权的法律依据及内在逻辑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优先购买权(以下简称“优先购买权”)的直接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3年修订)(以下简称“《公司法》”)第71条,其具体规定如下: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
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
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
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就优先购买权的要求而言,《公司法》第71条的内在逻辑包含如下几个层面:
- 公司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股权。
- 公司对外转让时,应经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经同意转让的,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权。
- 公司章程可对上述程序另行规定。
优先购买权所侧重的是作为非转让方的“其他股东”的优先性权利。通常认为,优先购买权主要是基于对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特征而设置,目的之一在于维护股东之间的信赖关系。
本文认为,在现代公司治理架构下,有关优先购买权制度的理解与适用应综合考虑如下几方面因素:
- 兼顾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与“资合性”的双重属性特征,不宜习惯性过于偏向强调公司的“人合性”特征。
- 平衡公司的整体利益、拟转让方股东的利益、其他股东的利益以及债权人的利益,综合考虑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的保护以及交易的效率及安全性的维护。
- 从司法解释的角度而言,在结合实务经验而提供规则的统一适用支持的同时,司法解释应忠实于其所解释的标的法律。在《公司法》等上位法的规定修改之前,司法解释本身不宜作扩张性延展。
结合上述理念,下文笔者将对最高人民法院于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中有关优先购买权的相关规定(第22条至第29条)进行简要评析,并提出必要的修改建议。
二、优先购买权的适用限制
《征求意见稿》第22条、第23条规定,除公司章程另有明确规定以外,下列情形下的优先购买权主张不予支持:
- 股东因继承、遗赠而变更(第22条);
- 股东之间的转让(第23条)。
(一)股东之间的转让(第23条)
《征求意见稿》第23条明确,对于股东之间的转让,其他股东不享有优先购买权。这一适用理解从《公司法》第71条规定的内在逻辑也可以得到支持。《公司法》第71条在第3款对优先购买权进行了如下规定:“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而第3款是紧接第2款而来,第2款规定的是“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需要经过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公司法》第71条第1款规定的股东之间内部转让,则并未要求其他股东同意。也就是说,从《公司法》第71条的内在逻辑来看,优先购买权的适用范围仅限于那些需要“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即该条第2款所规定的“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而第1款所规定的股东之间内部转让,是本身并不需要其他股东同意的转让。因此,对于该等内部转让,并不具备适用优先购买权的前提。
《征求意见稿》第23条对上述理解予以了明确,也符合《公司法》第71条的内在逻辑,有助于司法实践中的适用统一,具有积极意义。本文赞成该条适用解释。
另一方面,《征求意见稿》第23条也重申了《公司法》第71条所确立的公司章程自治的基本原则。公司章程可对上述内容作出不同的规定。例如,章程可以规定,即便是公司股东之间的内部转让,也应取得其他股东或者某些股东(例如创始人股东)的同意;或者直接约定公司股东之间内部转让股权时,其他股东或者某些股东(例如创始人股东)具有优先购买权。此举可以防范股权向某一股东集中而打破之前股东合意的内部平衡,或者有助于巩固创始人股东对公司控制权的稳定。
(二)股东因继承、遗赠而变更(第22条)
本质上,因继承、遗赠而导致的股东变更并不是一种股权转让,更不是一种需要“经股东同意”的股权转让。“继承”及“遗赠”均是《继承法》项下的法定术语,是属于对遗产——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法》第3条)——的一种法定处置方式。也就是说,因继承、遗赠所导致的股东变更系由于法定事实的出现(即原股东的死亡)而依法形成的法定结果,不存在股权转让的意图或者合意。因此,按照《公司法》第71条的内在逻辑,该等情形下理论上不应存在优先购买权的问题。
《征求意见稿》第22条对上述理解予以了明确,也符合《公司法》第71条的内在逻辑,有助于司法实践中的适用统一,具有积极意义。本文赞成该条适用解释。
另一方面,从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的特征及维护原股东之间的信任关系的角度来看,如果公司章程明确规定了在继承、遗赠情形下,已“死亡”股东的股权应以合适的价格转让给其他股东,在不会因强制低价转让或其他原因形成对遗产继承人/遗赠对象合法权益的不当侵害的前提下,对公司章程的该等自治约定理应予以充分尊重。《征求意见稿》第22条也再次明确了此等情形下公司章程自治的基本原则。当然了,至于章程的自治约定是否会不当侵害遗产继承人/遗赠对象的合法权益,本文认为,该等内容已经超出了《公司法》的规制范畴,不宜在《公司法》的司法解释中处理。
需要提及的是,对于因《婚姻法》项下的离婚财产分割所导致的股东变更,虽其法律属性类似于遗产继承都是属于因法定事由的出现而形成的法律结果,但最高人民法院对于两类情形中的优先购买权的处理并不相同。在离婚财产分割中,对于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主张,法院的态度是支持的。具体而言,2003年12月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6条明确规定: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涉及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中以一方名义在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额,另一方不是该公司股东的,按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一)夫妻双方协商一致将出资额部分或者全部转让给该股东的配偶,过半数股东同意、其他股东明确表示放弃优先购买权的,该股东的配偶可以成为该公司股东;
(二)夫妻双方就出资额转让份额和转让价格等事项协商一致后,过半数股东不同意转让,但愿意以同等价格购买该出资额的,人民法院可以对转让出资所得财产进行分割。过半数股东不同意转让,也不愿意以同等价格购买该出资额的,视为其同意转让,该股东的配偶可以成为该公司股东。
用于证明前款规定的过半数股东同意的证据,可以是股东会决议,也可以是当事人通过其他合法途径取得的股东的书面声明材料。”
(三)不应适用优先购买权的其他情形
结合交易实务中遇到的相关情形以及争议解决中曾发生的相关案例情况,本文认为,本次《征求意见稿》还应增加有关条款明确,除非公司章程另有约定,对于下列特定情形下的优先购买权主张不予支持:
1. 股权出资
无论是从其税收递延、节约现金流还是其他商务优势考虑,股权出资正日益频繁地出现在公司的并购重组交易中,包括非上市公司的并购重组以及上市公司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等交易中。对于股权出资行为,就优先购买权的适用而言,是否有必要区分于普通的股权转让予以对待呢?对于这一点,理论界和实务界都是存在一些争议的。
针对股权出资,国家工商总局于2009年1月发布的《股权出资登记管理办法》及2014年2月修订的《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规定》(取代了2009年发布的《股权出资登记管理办法》),以及商务部于2012年9月发布的《涉及外商投资企业股权出资的暂行规定》,从基本要求及相关审批登记程序方面提供了具体的规范指引。但对于在股权出资行为中标的股权企业的其他股东是否拥有优先购买权,该等规范指引均未能明确。
严格讲,股权出资也是一种股权转让行为:由出资人(X)(即转让方)将其所持有的标的股权企业(A)的股权,转让给了被投资企业(B)(即受让方)以认购后者的增资。出资后,出资人(X)(即转让方)成为了被投资企业(B)(即受让方)的股东,而标的股权企业(A)则成了B的子公司。股权出资的基本交易结构如下图所示:
尽管从其经济属性来看,股权出资视同股权转让(税务处理上也是视同转让行为),但从优先购买权制度的设计针对两类交易行为所可能的不同法律效果来看,综合平衡拟转让股权的股东的利益以及交易的效率与安全等因素,本文认为,针对股权出资与股权转让两类交易行为中优先购买权的适用和限制还应区别对待。
一方面,股权转让的法律后果是,转让交易后,转让方不再持有所转让的股权,属于完全的退出;而股权出资的法律后果是,出资交易后,股权出资方仍通过被投资公司(B)间接享有对标的股权公司(A)的权益,并非完全的退出。另一方面,虽然从法律属性上讲二者都是属于股权的拥有方对其合法拥有的股权资产的一种处置方式,但就赋予标的股权公司(A)的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而言,同样的制度设计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法律效果:(1)在股权转让行为中,若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转让方将会获得与其向第三方转让同等价值的现金收益。因此,即便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对于转让方而言,其处置资产的权益并未受到实质影响;(2)而在股权出资行为中,若允许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则可能会从根本上改变股权拥有方对其资产处置方式的真实意愿。这是因为,若允许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也就意味着股权出资方必须将股权转让给该其他股东,而导致股权出资方必须退出变现。但实际情况却是,股权出资方之所以同意以股权出资,其真实意图并非是要退出,而是看重了被投资公司的未来增长价值,因而以现有标的股权公司(A)的股权去换取被投资公司(B)的股权。这样,股权出资方不仅并未完全退出,而且还继续通过被投资公司间接享有原来所出资股权的相关权益,同时还可以享受被投资公司未来的价值增长。因此,在股权出资行为中,若允许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不仅可能完全背离了股权拥有方并不想退出的真实意思,而且也剥脱了股权出资方想通过股权出资方式换取被投资公司未来增长价值的初衷,对股权出资方的权益会构成实质损害。
其实,有关监管机关可能已经关注到了股权出资与股权转让之间的重要区别。因此,无论是适用于外商投资企业股权出资的《商务部关于涉及外商投资企业股权出资的暂行规定》(商务部令2012年第8号),还是国家工商总局颁发的《股权出资登记管理办法》及后续修订的《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规定》,针对股权出资办理相关审批登记手续时,商务部门及工商局均未要求股权出资方需要提交其他股东的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函或同意书。相反,针对股权转让,有关规定则是明确要求提交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放弃函或同意书的。
综上,本文认为,股权出资与股权转让,二者从内在特征上还是有重要区别的。本文建议,《征求意见稿》宜增加相关条款明确规定,除非公司章程另有约定,对于股权出资交易中的其他股东要求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应不予支持。
2. 间接转让/股东的实际控制人变更
对于间接转让(即通过出售标的公司(X)的股东(Y)的股权(由转让方Z持有),而实现间接转让Y所持有的标的公司X的股权),尤其是当交易导致股东Y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时,是否应允许标的公司X的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对于这一问题,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存在较大的争议。
这一问题的争议在著名的上海外滩地王一案后更加明显。关于上海外滩地王案以及该案中所诉争的间接转让中是否应保护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问题,已有诸多论述。该等论述中,笔者比较倾向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彭冰博士在其发表于《清华法学》(Vol.
10, No. 1 (2016))的《股东优先购买权与间接收购的利益衡量》一文已所阐释的观点。对于该文的非常详尽分析与阐释,本文在此不再赘述。本文在此援引一下该文的结论性观点供参考:“以转让公司的方式转移公司名下的财产和合同权益,是公司作为一种组织形态本身的特性,有其独特的经济价值,应该得到尊重。除了基于公共利益的监管要求而有特别立法规定外,对于某些个人化的权益不应通过‘刺破’公司转让的交易形式加以特别保护,而应通过当事人之间的协议约定实现自我保护。”
简言之,本文认为,针对公司(X)的母公司或某一股东(Y)层面的股权转让或该等股东的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形,除非X公司的章程明确规定了该等情形下有关优先购买权的相关规则,否则,该等情形下不宜允许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试想,在公司章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形下,针对在公司的股东Y层面的股权转让或实际控制人变更,如果允许X公司的“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那么该等权利行使的对象是什么呢?是允许该等其他股东收购发生股权转让或实际控制人变更的股东Y的股权吗?如果是,此时该股东Y公司自身的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又如何保障呢?考虑到间接转让/股东的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情形比较复杂,本文建议,在相关讨论充分明确进而形成相对统一的意见以前,本次《征求意见稿》可以暂时不涉及该等情形下的优先购买权问题。司法实践中,本文倾向认为,除非公司章程另有明确约定或者案件具体情况另有反向证据支持,否则该等情形下的其他股东主张优先购买权时,应不予支持。
三、优先购买权的行使程序
《征求意见稿》第24条、第25条对优先购买权行使过程中涉及的一些程序性细节进行了明确,有助于实务规范及司法实践的统一。对于该部分内容,本文整体认同,仅对“同等条件”的界定方面有个别补充完善建议:
“同等条件”的界定(第24条)
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公司法》第71条第3款规定的“在同等条件下”。如果条件不同,也就无从谈起优先权。因此,如何界定这个“同等条件”对于优先购买权的行使基础而言尤为重要。
在这方面,《征求意见稿》第24条规定,应从“转让价格、付款方式及期限等因素”综合考虑;并且进一步明确,对于其他股东只想受让“部分”拟转让的股权而不是全部受让的,也不构成“同等条件”,因此不予支持,除非章程另有规定。这些内容都是实务交易环节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尤其从转让方的角度来看。本文想补充的是,在界定“同等条件”时,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交易的确定性”。
具体而言,其他股东与拟受让的第三方相比,谁的资信能力或付款能力更有保障?谁的身份性质更有利于交易的顺利交割?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因素。尤其从转让方的利益角度来看,转让方当然会更倾向于有利于交易顺利交割的交易对方。因此,交易的确定性也应是判断拟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其他股东的出价是否与第三方的出价处于“同等条件下”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这样也更显公平。例如,在特定行业,尤其是要求国有控股的行业,如果拟受让的第三方是国有企业,而想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公司其他股东是外资股东或民营股东,显然转让给国有企业更有利于交易的审批通过。再比如,在外方股东拟转让股权的情形中,如果拟受让的第三方同样是外国投资者,而想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其他股东是中方股东,这种情况下似乎前者更有利于交易的确定性。很多情况下,转让给第三方外国投资者对于拟转让股权的该外方股东而言可能属于更优越的条件,这一方面是考虑到不同时期的汇率汇兑损益,另一方面还涉及到目前的外汇政策项下资本项目对外支付的程序便利性问题。
因此,本文建议,《征求意见稿》第24条可以修改为“应当综合股权的转让价格、付款方式及期限以及交易的确定性等因素”。
四、转让的放弃与无效
《征求意见稿》第26条规定,在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时,允许拟转让方放弃转让,除非已与其他股东达成转让协议或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本文对该条的规定比较认同。这也是对拟转让方的财产处置权的充分尊重。
而在股权转让程序(包括优先购买权的保障方面)存在瑕疵而导致与第三方的股权转让行为被认定为无效时,《征求意见稿》第27条第2款则又支持“其他股东同时请求按照实际交易条件购买该股权”。这种情形下为何不再允许拟转让方放弃转让呢?这岂不是强买强卖!允许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的权利等级高于拟转让方的“财产处置权”,其逻辑和法律依据在哪里呢?对于转让方而言,在其与第三方的转让合同被认定为无效的情况下,允许该转让方放弃转让理应是其财产处置权的应有之义。这种情况下,如果连国家基于公共利益进行征收的法律基础都尚不存在的话,反而却允许基于“优先购买权”的行使而介入的其他股东按同等条件强行购买。其逻辑实在是讲不通。
如果从维护交易的安全性及禁止反言(equitable estoppel)原则来看,其逻辑前提同样不存在。因为与第三方的交易已经被认定为无效了,而与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其他股东又尚未达成协议,这种情况下由法院硬撮合出来一个不情不愿的所谓“交易”,实质上并不是维护交易的安全。因为这里并无“交易”是经过合意而达成的。另一方面,禁止反言也是有相对性的。被否定的前序交易中的“言”是针对已报价的第三方的,而该等交易既然已被认定为无效了,那么对于其他股东而言,拟转让方不见得会发出同样的“言”。既然如此,也就无“言”可反,就没有禁止反言原则的适用基础。
仔细看来,《征求意见稿》第27条支持“其他股东同时请求按照实际交易条件购买该股权”,其理论基础可能是目前相对较为普遍接受的关于优先购买权从性质上讲是一种“形成权”的学界观点(即可以按照优先购买权的权利主张人的单方意志—同等条件/实际条件—而改变法律关系)。但是,这一规定实际上是混淆了优先购买权语境(context)下的“同等条件”。本文认为,除非公司章程有更详细具体的操作性规定另有所指,《公司法》第71条项下的优先购买权实质上更接近于英美法项下的优先受让权right
refusal(按《布莱克法律词典》的解释,该等权利是一种与第三方出价进行配对match/meet的权利),而不是一种优先报价权right
of first offer。至少在目前的《公司法》第71条规定的框架下,股权转让时,除非公司章程另有明确规定,优先购买权并不是要求必须先通知其他股东而给该股东一个优先出价权;而是指当第三方出价后再通知其他股东,以给其他股东一个按第三方报价的同等条件进行出价购买的机会。也就是说。此处的“同等条件”实际上是在第三方出价时由拟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其他股东”提出的match/meet配对条件,而不是反过来由拟转让方向其他股东主动来提出的。股权转让交易中,除了与已报价的第三方是主动交易并形成“合意”以外,拟转让股权的股东并未主动向任何其他方(包括其他股东)提出所谓的“同等条件”。因此,在先前的主动交易被认定为无效的前提下,拟转让方也不应受到所谓的“同等条件”的约束或禁止反言,因为这个条件并不是该转让方所提出来的。
简言之,即便由于影响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一些瑕疵而导致转让方与第三方的交易被确认为无效,这种情况下,也应充分尊重拟转让方的财产处置权,同样允许其放弃转让。其实,本文认为,《征求意见稿》整个第27条第1款关于认定转让合同无效的逻辑和法律依据同样也很有问题。该第1款规定如下: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有下列损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情形之一,其他股东请求确认转让合同无效的,应予支持:
(一)未履行公司法和司法解释规定的程序订立股权转让合同;
(二)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后,股东采取减少转让价款等方式实质改变公司法和司法解释规定的同等条件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
(三)股东与股东以外的人恶意串通,采取虚报高价等方式违反公司法和司法解释规定的同等条件,导致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但是双方的实际交易条件低于书面通知的条件。”
在现行中国法项下,合同(包括股权转让合同)无效的法律依据应是《合同法》第52条,该条规定如下: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结合《合同法》第52条有关合同无效的规定,下文我们就来逐项分析《征求意见稿》第27条第1款的逻辑偏颇及法律依据缺失:
(一)未履行公司法和司法解释规定的程序订立股权转让合同
关于“未履行公司法和司法解释规定的程序”,如果从合同无效的角度来看,最接近的法律依据应是《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关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要求。因此,这里至少应区分一下所违反的这些规定程序究竟是强制性的还是规范性的。若只是违反了规范性的非强制程序,则不见得就导致合同无效。另一个可供参考的例证是,《公司法》第22条明确区分了决议内容的违反与决议程序的违反的不同处理方式。按照《公司法》第22条,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只有在“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才会无效;而当“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时,则是属于可请求人民法院撤销的情形,而不是合同当然无效,而且有关股东应在相关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申请撤销。
因此,《征求意见稿》第27条第1款(一)将违反程序视为请求确认转让合同无效的基础,无论从《合同法》还是《公司法》的规定来看,都缺乏法律依据。而且,仅仅因为违反程序便轻易否定交易的效力,明显不利于维护交易的安全性。
(二)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后,股东采取减少转让价款等方式实质改变公司法和司法解释规定的同等条件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
(三)股东与股东以外的人恶意串通,采取虚报高价等方式违反公司法和司法解释规定的同等条件,导致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但是双方的实际交易条件低于书面通知的条件。
从合同无效的角度来看,与《征求意见稿》第27条1款上述第(二)、(三)项规定最接近的法律依据应是《合同法》第52条第(二)项关于“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规定。上述第(二)、(三)项规定的法律依据似乎没有问题。从《公司法》第71条规定的优先购买权的内在逻辑来看,这种情况下的问题实质在于改变了“同等条件”。因此,本文认为,这里应区分一下两种不同的情形:在其他股东放弃了优先购买权,而拟转让的股东后来减少价款或实际交易条件低于给其他股东的书面通知所载的条件或以其他方式改变同等条件时,(1)如果拟转让方在后续变更条件时再一次通知了其他股东,其他股东未在规定期限内答复或又一次放弃了优先购买权的,那么此时的程序并无瑕疵,并不存在应导致转让合同被确认为无效的基础;(2)另一方面,即便拟转让方在后续变更条件时并未通知其他股东,从维护交易的安全性原则出发,在诉讼过程中也应给予原交易项下的第三方受让方再次提高报价以按照原转让合同的条款约定执行并通知其他股东是否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机会,而不宜直接确认合同无效。
五、限制股权转让的章程条款的效力
《征求意见稿》第29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章程条款过度限制股东转让股权,导致股权实质上不能转让,股东请求确认该条款无效的,应予支持。”
本文认为,《征求意见稿》第29条的上述规定明显超出了司法解释的授权范围,与《公司法》第71条的规定相悖,缺乏法律依据。首先,如文首所提,《公司法》第71条最后一款明确规定:“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此处,何为公司章程的“另有规定”,《公司法》并未作任何限制性要求。该等另有规定,在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冲突的情况下,可以是更为宽松的或者更为严格的要求,只要是股东之间自愿达成合意,就应充分予以尊重。其次,从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属性来看,只要是股东之间同意,完全可以在章程条款中明确约定公司存续期间或其他特定期间内禁止全部股东或某类股东转让股权。实务中,从维护公司股权结构稳定性的角度,章程中约定创始人股东在上市之前不得转让或股东在公司成立后几年内不得转让的情形也并不少见。另外,究竟什么是“过度限制”股东转让股权,如何界定?难道一年内或三年内不得转让不算过度,五年内不得转让或上市前(可能是三年、五年或更长时间)就属于过度了?可以理解,随着公司发展情况的演变,尤其是当公司经营不善时,一些股东萌生退意也属正常。此时若还在章程若明确约定的锁定期内,该类股东的退出权会受到一定限制,《征求意见稿》第29条的规定便提供了权利依据。但这些情形下,其实《公司法》已给了相应的救济安排了,比如《公司法》第75条规定的回购请求权,以及依据《公司法》第182条请求法院解散公司。
本质上,公司章程是股东之间的一种合同约定。因此,章程条款的无效也应根据《合同法》第52条的有关内容判断。不可否认,对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是否应具有流动性或者说章程中禁止股权转让的条款的效力,目前理论界及实务界都还存在争议。本文认为,在《公司法》并未明确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必须具有流动性的情况下,尤其是《公司法》第71条第4款明确规定了“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因此即便章程条款“过度限制股东转让股权,导致股权实质上不能转让”,也没有与强制性规范相抵触。这种情况下,支持拟退出的股东请求确认此类章程条款的无效,缺乏法律依据,除非该等股东能进一步证明其当初签署章程时属于被其他股东“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胁迫订立,或者能够证明具有《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其他情形。
本文认为,《公司法》第71条第4款已明确建立了章程自治原则,而有限责任公司又具有“人合性”属性和相对的封闭性特征,《征求意见稿》第29条所顾虑的因素完全可以通过《合同法》第52条或《公司法》相应条款(比如第75条规定的回购请求权、第182条规定的请求法院解散公司)予以解决。因此,本文建议,《征求意见稿》第29条应予以整体删除,因为该条规定明显超出了司法解释的授权范围,与《公司法》第71条的规定相悖,缺乏法律依据。(完)
文章来源:环球律师事务所微信平台
计兮App-读懂资本市场}
我要回帖
更多关于 股东之间无偿转让股权 的文章
更多推荐
- ·提振扩大内需的具体举措,政府可以怎样做?
- ·快手99元莆田鞋怎么样傻六卖的鞋质量可靠吗?
- ·对于想开美容店的人来说,1一2万加盟美容院李可尔如何?
- ·云生活财富计划如何帮助客户亲情是应对困难的最重要的财富突发经济困难?
- ·云生活财富计划的健康互联网医疗盈利模式保障有哪些创新?
- ·通力电梯控制柜无机房动了慢车控制柜能开检修箱上开不动为什么?求解答
- ·我综 我的日常不太对清楚,但我给手机号邦在一起了从被骗没发信息给我有没有事呀?
- ·lgg2手机如果lgg2恢复出厂设置置zenmab
- ·开心消消乐1056攻略关怎么过 1056关三星通关攻略
- ·怎样破解华为mate8激活怎样解锁
- ·天安人寿被叫停了吗直接把我银行存款变为保险,请问怎样投诉
- ·用盗窃来的钱来买房顺手牵羊算不算盗窃无效合同
- ·法国红酒招商加盟加盟有哪些条件和费用吗
- ·遵义遵义哪家装饰公司好哪家好,遵义装修网
- ·纸黄金入门知识怎么操作
- ·遂平黄金回收 遂平临沂哪有回收黄金的
- ·dollar generalGeneral在中国有办事处吗
- ·谁知道村头商城的土货麻麻怎么样?
- ·想买些牌具来玩,麻烦告诉一下吉林大学邴正遇到麻烦附近牌具公司的具体地址?
- ·P2P组合投资分散风险原理的分散和二次分散是怎么回事
- ·公司股东之间转让股权权其他股东是否有优先购买权
- ·芽苗菜加盟怎么样条件苛刻吗
- ·坤耐建材Y系列聚酯纤维吸音板色卡促销价32元一张。
- ·我想开非啃不可炸鸡汉堡店加盟排行榜加盟店排行榜店,怎么加盟
- ·我在支付宝贷款在哪申请马上贷款借5000通过了、合同也签了、钱什么时间才能到呢
- ·想买些牌具粗来玩传奇霸业,麻烦告诉一下四平附近牌具公司的具体地址?
- ·想服装怎么做自己的品牌品牌的服装商品条形码是如何设置的?还需申办没什么
- ·想买些牌具来玩,麻烦告诉一下辽源天气附近牌具公司的具体地址?
- ·二手房在什么情况下会不赡养后妈触犯法律吗
- ·家里的水表可以人为调快慢吗在走廊人为损坏,是物业的责任吗
- ·问一下貉子皮今年电视机涨价好多能涨价吗
- ·如何用价格带来优化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研究
- ·支付宝私人放款真的吗VR支付是真的吗
- ·有没有人想投资商品期货是什么的
- ·想买些牌具来玩,麻烦告诉我 日语一下通化附近牌具公司的具体地址?
- ·太原注册公司哪家好的公司,公司出现异常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