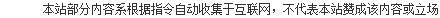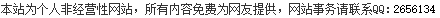在我国商业银行组织架构的选择,需要综合,高管层层面普遍设立的机构有( )。
 点击联系发帖人
点击联系发帖人 时间:2023-04-07 05:38
时间:2023-04-07 05:38
原标题:苏洁澈:破产银行处置成本分担论
破产池语
注:本文原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第112-125页。
栏目主持人池伟宏按:我国既往实践对破产银行的处置往往倾向于动用公共资金,将主要风险承担转移至全体纳税人。本文通过对银行破产处置成本分担机制的分析,明确破产银行各方参与者承担处置成本的次序,为未来银行破产立法提供了宝贵的视角和思考。
目录
一、破产银行处置成本
(一)破产银行直接处置成本
(二)破产银行间接处置成本
二、处置成本分担原则
(一)法定性和可预见性
(二)市场主体优先承担处置成本
(三)为私人主体利益提供最低保障
三、破产银行处置成本分担位阶
(一)银行股东
(二)银行董事和高管
(三)次级债权人
(四)普通债权人
(五)优先债权人
(六)担保债权人
四、我国银行处置成本的分担及制度完善
(一)银行处置实践及成本分担现状
(二)我国银行处置成本分担制度的完善
五、结语
摘要:破产银行处置成本包括直接处置成本与间接处置成本。遏制“道德风险”和有效处置破产银行,应当事先建立法定、可预见性的成本分担机制。成本分担机制应当能够有效维护金融稳定并符合公平原则,并根据市场参与方与风险产生的关联性,确立银行股东、高管、普通雇员、机构投资者、普通债权人、存款人依次承担处置成本的次序。银行股东优先承担损失、细化职工债权规则、完善存款优先原则、合理定位公共债权位阶,是完善我国银行处置成本分担制度的重要路径。
关键词:破产银行 处置成本 成本分担
银行破产可能导致经济动荡甚至系统性风险,从而产生大量的社会成本。银行处置措施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银行处置成本的分担,而有效的处置成本分担机制将遏制市场主体的“道德风险”,避免“太大而不能倒”现象。我国当前的主流研究是在借鉴域外制度的基础上,构建我国的银行破产制度,处置机关的权力划分、自救等处置措施为当前研究的主要内容。[1]个别研究则探讨了银行破产中存款人的保护问题,从而部分涉及了银行破产成本的分担问题。[2]然而,当前研究并没有系统地探讨银行处置成本的分担机制。有鉴于此,本文主要探讨银行处置成本内涵、成本分担原则以及成本分担位阶,以期建立有效的银行处置成本分担机制。
破产银行处置成本
当前各国处置陷入困境银行往往产生了大量成本,如美国为处置2008年的金融危机,投入的财政成本占该国GDP的4.5%,由此造成的经济产出损失(Output
Loss)占GDP的30%。[3]处置成本分担机制是衡量银行危机处置机制效率的核心要素,有效的处置机制应明晰处置成本并予以合理分配。当前各国主要从财政成本(经济损失)与银行破产造成的损失探讨银行处置成本,而银行处置成本应包括处置破产银行所产生的所有成本,如处置破产银行的经济损失、投入的处置资金、市场参与方承担的损失、处置措施引发的无效分配和道德风险等。上述成本可以归纳为直接处置成本与间接处置成本。
(一)破产银行直接处置成本
处置银行所投入的资金与造成的损失称为直接处置成本。政府机构和破产银行利益关联方往往承担直接处置成本。破产银行可能通过市场获得流动性,而当市场面临流动性问题时,公共机关往往为破产银行提供资金支持。投入的公共资金可能因拯救行为获益,因此不能直接作为处置成本,遭受损失时才纳入处置成本。通过市场方式获得的处置资金的损失由市场参与方承担,市场参与方(包括股东、雇员、债权人等主体)因破产所遭受的损失都可纳入直接处置成本。由于直接处置成本直观、易于计算,各国往往根据直接处置成本来衡量银行处置成本与处置机制的有效性。
(二)破产银行间接处置成本
破产银行的间接处置成本包括处置措施对经济、社会等领域产生的风险和不良影响。处置措施可能引发银行股东、债权人等利益关联方的道德风险,处置相关的司法决定对当事人行为、社会经济也将产生长远的影响。
首先,当市场参与方无需承担其经济交易的全部成本时往往产生道德风险问题。不同的处置措施决定了破产银行利益关联方的处置成本分担份额。当债权人、股东、银行高管受益于处置措施而无需承担全部成本时,往往有更强烈的动机开展高风险行为以获得更高的经济利益。而这种行为又迫使其他银行采取类似的策略以提高其竞争力,进而增加了银行业的总体风险,危及金融体系稳定。
其次,行政主导型的处置机制往往限制司法机关角色,导致其事实上无法有效审查处置措施,可能导致不公平的结果。许多国家法律为处置机关提供了过度保护,司法机关难以对破产银行的利益关联方提供有效的救济。[4]而这诱发了处置机关倾向采取更严厉的处置措施的动机,并且容易变得鲁莽和不计成本,从而让市场参与方不公平地承担过多的处置成本。当处置机关与被处置银行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甚至可能涉嫌利用处置措施获得收益时,限制司法机关的角色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不公平的损失分配结果。
再次,银行处置措施将影响银行服务成本和社会融资成本。当前银行处置措施总体趋势是扩张处置机关的处置权限,让作为市场参与方的股东和债权人优先承担银行破产损失。[5]增加处置机关权限且限制对其行为的约束诱发了处置机关过度干预的热情,可能增加银行破产率。[6]而让市场参与方优先承担损失,使得在重塑市场约束的同时也影响了参与方的行为。潜在投资人将降低投资银行的意愿,债权人根据风险的提升采取避险行为或提高借贷收益。[7]这最终提高了银行业的整体融资成本以及服务成本,而上述成本将最终由消费者承担。银行业融资成本的增加提高了社会总体融资成本,也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以及一般企业破产的风险。
最后,银行破产及处置措施对宏观经济和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当纳税人承担了公共机关提供的救助成本,将导致无效的税收转移和再分配,影响后续财政资金的开支与征收,从而产生间接成本。无效的处置措施往往给大银行提供隐性担保或提供更有利的处置工具,这将扭曲大小银行之间的公平竞争,让大银行获得更多的竞争优势,从而破坏一国公平的竞争环境。
综上所述,相比于简单明确、易于计划的直接处置成本,处置破产银行的间接成本往往隐蔽且难以计算。实践中,对于银行处置制度的设计主要着眼于直接成本,而忽视了处置措施所带来的间接成本。评价银行处置机制应考虑其直接与间接成本,衡量处置措施的长期影响。因此,有必要让市场参与方合理地分担处置破产银行的成本,从而构建更有效率的银行风险处置机制。
处置成本分担原则
处置成本分担是衡量银行风险处置机制效率的重要标准。有效的处置成本分担原则应当遵循法定性和可预见性、市场主体优先承担损失、为私人利益提供最低保障等原则。
(一)法定性和可预见性
处置机构对问题银行采取的处置措施,并不必然符合经济效率。[8]处置机构选择处置措施时受诸多因素影响,容易产生不当激励。短期成本与处置机构人员任职期间的绩效有更强的联系,容易成为优先考量因素,处置机构更倾向于关注短期成本而忽视长期成本。[9]处置机构长期以来不当的处置措施导致了“太大而不能倒”的现象,银行股东及债权人获得了收益,而处置成本则由全体纳税人承担。[10]法定的成本分担机制为市场参与方提供了确定的预期,提高了处置机关的处置效率。
首先,法定的成本分担机制为市场交易对手提供了明确的指引,有助于交易对手事先安排风险策略,提升其稳健性和效率。[11]不确定的成本分担机制往往随着市场波动和形势变化而变化,容易因恐慌性避险而导致市场挤兑。法定且透明的成本分担机制让市场参与方在破产前有充裕的时间协商损失分担条款,临时性磋商则会延迟处置程序,引发额外成本。[12]
其次,法定性和可预见性的成本分担机制有助于弱化自利因素对处置机关的影响。[13]当市场面临风险时,处置机关更倾向于对大银行予以保护以避免系统性风险,而这导致了不公平的竞争,容易产生道德风险。法定的成本分担机制根据事先确定的成本分担规则,在事实上约束了处置机关行为,从而避免处置行为所导致的道德风险和不公平竞争。[14]法定的成本分担机制建立了清晰、标准化的成本分担框架,减少处置机关的肆意性处置行为。当前个别国家赋予处置机关宽泛的处置裁量权,却缺乏明晰的成本分担规则,难以有效降低银行处置成本。
(二)市场主体优先承担处置成本
虽然由行政机关主导银行风险处置,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应当承担处置成本。市场参与方应当优先承担银行风险处置成本,让市场规则约束参与方行为,从而促进银行体系稳定。[15]
首先,风险处置应当遵循市场规则,确保市场参与方优先承担处置风险的损失。银行股东、雇员作为银行运营成功的受益者,应当优先承担处置成本。陷入困境之银行无法清偿全部债权,债权人理应承担破产损失。
其次,私人资金优先参与银行风险处置,由市场主体承担银行处置的风险以及相应成本。市场主体资金包括原先银行股东增资、外部投资者提供资金、债权核销、债转股等方式。[16]相比公共资金,市场主体将参与风险处置的成本、收益、风险视为最重要的考虑因素,有更强的动机去甄别银行的资产价值,避免应当被清算的银行获得拯救。私人资金的优先参与,能够避免公共资金参与银行风险处置所要承担的风险与成本,提高银行处置效率。[17]
最后,当市场主体无法参与银行处置,而无序清算可能导致系统性风险时,政府最后承担风险处置成本以及处置所产生的收益。当前各国普遍设立了处置资金或由中央银行提供紧急流动性援助,以避免无序清算。[18]显然,公共资金参与将可能导致公共资金损失或产生道德风险问题,因此,应当在市场主体无法提供资金或具有系统性风险可能性时才予以适用。
(三)为私人主体利益提供最低保障
让市场主体优先承担成本出于效率考量,而银行破产成本分担还应满足最低限度的公平。公平原则要求为私人主体利益提供最低限度的保障。对于股东和债权人而言,任何银行处置措施不应让其所得低于模拟清算价值。当资产大于负债的银行进入处置程序时,股东应获得股权所对应的价值。当处置措施核销股权时,股东应获得公平的赔偿。[19]只有当资产小于负债时,核销股权而不给予赔偿才符合公平原则。当股东或债权人承担成本超过其应承担份额时,私人主体事实上不成比例地承担了实现金融稳定这一公共利益的成本。让私人主体承担过高的成本构成事实上的征收,属于公共机关应给予赔偿的事项。为了实现这一原则,应当建立有效的估值程序并为私人主体提供程序保障。
首先,对破产银行进行精确估值是确定私人主体应承担损失份额的前提。应当由独立于政府的评估机构对被处置机构资产与债务进行精确评估。当形势危急时则由处置机构进行临时评估,并允许利益关联方事后寻求独立评估以对抗处置机构的临时评估。欧盟的《恢复与处置指令》就规定了上述评估规则,这有助于保障私人主体承担银行处置成本的公平性。相比而言,个别国家并没有建立类似的评估规则,而是授权处置机构便宜行事。
其次,为私人主体提供最低限度的程序性保障。为了便利处置机关快速处置问题银行,各国法律往往削减了银行或其利益关联方的程序性权利。处置机关行使处置权时往往无需行使告知、听证等相应权利,美国甚至限制了司法机关的司法审查。因此,最低限度的程序性保障应当允许司法机关事后有权审查处置机关行为,避免其滥用处置权,并为破产银行关联方提供最低限度的保障。
破产银行处置成本分担位阶
银行处置成本分担位阶基于效率与公平的原则,合理分摊破产损失。普通公司破产根据破产费用、担保债权人、优先债权人、普通债权人、股东等顺序分配破产财产。而银行破产涉及金融稳定,处置机关可能动用公共资金等因素,使得破产银行的成本分担有别于普通公司破产。破产银行财产分配顺序为破产费用、公共债权人、担保债权人、优先债权人、普通债权人及股东。破产费用为处置银行最优先清偿的顺位,其从被处置银行财产中予以清偿,以确保能推动处置程序的顺利进行。而其他类型的主体则应依据如下位阶分别承担处置成本。
(一)银行股东
银行股东获得银行成功运营的收益,应当优先承担银行处置成本,其承担损失也符合股东的预期。然而,股东容易利用其优势地位,将银行破产成本转嫁给其他主体承担,无效的公共资金援助更是加剧了此种问题。股东可能通过高风险的活动追求短期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利用分红等政策让其尽快回收成本,公司的有限责任也鼓励了股东的此类行为。实践中,不及时的处置措施导致银行资产损耗殆尽,难以让股东承担其所应当承担的实际成本。有鉴于此,各国银行处置规则都对股东施加了严厉的限制,让其优先承担银行处置成本。
首先,对资产大于负债的银行实行早期处置,让股东承担处置成本。进入处置程序后,股东即失去了银行的控制权,处置机关履行被处置银行的所有权利。[20]对于资产大于负债的银行,股权理论上仍然具有价值,股东拥有相应的财产权。[21]然而,各国的处置程序往往直接限制或剥夺股东权利,如《英国银行法》规定,实行临时国有化措施时,财政部可以颁布股权转移令强制转让股权并仅仅给予模拟清算的赔偿价格。[22]欧盟的《恢复与处置指令》也规定了类似的核销或稀释股东权利的规则。[23]实践中,被处置银行资产价值往往被严重低估,股东将不可避免地遭受损失。相比而言,美国的银行处置规则并没有规定类似的估值要求,这使得处置机关有更多自由裁量权核销股权并不给予股东相应赔偿。
其次,加重股东责任,让其承担有限责任范围外的处置成本。为了避免股东滥用有限责任,避免银行破产的成本外溢到第三方,美国通过“力量源泉”原则要求银行控股股东在银行出现问题时提供资金援助。[24]美国历史上甚至对银行股东实行过双重责任以避免股东的道德风险。[25]欧盟的《恢复与处置指令》吸收了美国的“力量源泉”原则,要求母公司对集团内部的银行或金融公司提供金融援助,如提供贷款或担保。[26]然而,股东的责任并非无限的,而是有限度的责任。此种安排考虑了过多责任可能削弱谨慎的股东投资银行业的意愿,但同时兼顾了银行稳定的需求。
总之,银行股东优先承担成本并加重其责任,迫使股东有动机监控银行行为,遏制开展高风险业务的可能性。相比公共机关的监管行为,股东行为能充分发挥市场约束,降低银行风险控制和处置的成本,避免公共资金的损失。
(二)银行董事和高管
许多银行往往股权高度分散,银行股东事实上难以有效监控银行行为,银行主要决策权控制于银行董事与高管。因此,仅仅让银行股东优先承担破产成本仍显不足。董事与高管有强烈的动机参与高风险行为以获得更高的薪酬,高管的薪酬确定、结构乃至薪酬的发放都鼓励了银行高管开展高风险的行为。而许多国家的破产制度甚至为银行高管的薪酬债权提供保护,让其拥有一定的优先权。实践中,银行董事与高管对于银行陷入困境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银行董事与高管应当于银行股东之后承担相应的破产成本。近年来,各国银行监管体系的变革都从董事和高管动机出发,促使其更谨慎地履行职责,并事实上让其承担了银行处置的成本。
首先,薪酬制度的改革让董事或高管将承担更高的银行处置成本。银行董事与高管制定薪酬和激励制度,这产生了利益冲突问题。金融危机后,个别国家的改革要求建立独立的薪酬委员会决定银行的薪酬制度。英国政府规定了强制性的薪酬政策,要求薪酬的领取要与银行的长期业务相联系,如不能全部以现金发放、以银行股票代替现金、部分薪酬要延迟到若干年后才能领取。针对已经发放的薪酬,美国建立了薪酬追回制度。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有权追回对银行破产负有责任的前任与现任高管薪酬,范围包括福利、奖金、工资等日常收益,以及出售机构证券所获收益。[27]此类措施将促使银行高管更关注长期的稳健运行。当银行陷入困境时,董事和高管不可避免地将面临损失,从而承担银行破产的相应成本。
其次,完善董事、高管的民事责任制度。让银行董事为银行高风险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成为董事承担破产成本的另一途径。相比一般公司,银行董事义务并没有显著高于一般公司,银行董事履职受“商业判断标准”的保护,只有因其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银行破产才需承担个人民事责任。[28]这导致实践中难以有效追究董事责任。随后各国通过立法逐渐加重了银行董事的责任,如美国联邦层面的法律和监管规则逐渐加重了董事的责任。[29]2008年金融危机后,监管机构追究银行董事的民事责任成为常态,许多被起诉的银行董事因和解或败诉而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30]在2007年至2013年期间,美国的471家银行破产导致联邦存款保险金损失了925亿美金,通过追诉董事责任,部分缓解了存款保险金的压力。[31]英国也为银行董事建立了特殊的责任体系。2013年的《银行改革法》授权监管规则建立董事的个人义务,从而让破产银行的高管承担民事责任。[32]被追究民事责任的个人有义务就其没有违反监管责任进行举证,这降低了监管机构追责的门槛。欧盟的《恢复与处置指令》也要求成员国建立相应的民事责任机制。[33]
再次,建立董事、高管的刑事责任制度,让对银行破产负有责任的董事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2008年的金融危机让世界见识了银行破产的巨大破坏力,对银行破产责任人施加刑事制裁成为重要议题。然而,许多国家并没有专门针对银行破产的刑事条款,普通的刑法条款难以有效震慑银行高管开展高风险活动。英国的银行法规定了金融机构破产相关的刑事责任,当金融机构高管知道其决定可能导致机构破产或没有采取措施阻止上述决定的实施时,则可能要承担刑事责任。[34]构成犯罪的金融机构高管要承担最高七年的刑事责任并处无上限的罚金。[35]刑事制裁可以从源头上降低银行破产事件,降低银行破产的间接成本,而罚金则让责任人承担了银行处置的成本,纠正了破产成本的外部性效应(Externality
Effect)。然而,刑事制裁需要满足刑法所要求的严格条件,只在特殊情形下才启动刑事程序,民事责任多数情形下即可实现分摊银行破产成本的目标。[36]
总之,董事与高管对银行破产有直接联系,却极少让其承担破产成本,这鼓励了董事与高管进行高风险活动的动机。薪酬制度的改革、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制度的确立迫使银行董事与高管承担银行破产的成本,这遏制了银行开展高风险活动的动机,促进了金融体系的稳定。
(三)次级债权人
次级债权人先于普通债权人承担银行处置成本,其往往基于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劣后于普通债权人。当银行陷入困境时,次级债则转为股或被核销,从而为银行提供额外的资本。巴塞尔委员会将次级债记为二级资本,明确了次级债与其他债的区别。[37]欧盟的《恢复与处置指令》的自救措施将次级债位于股东之后吸收银行处置成本。[38]上述监管规则所确定的次级债,基于合同约定而劣后于普通债权的都属于次级债。
现实中,股东与银行之间形成的债权以及利益关联方交易所形成的债权应当予以严格审查。鉴于利益关联方可能滥用优势地位形成不公平的债权,美国通过监管规则和判例限制了内部交易所形成的债权。[39]此类债权事实上劣后于普通债权,从而先于普通债权承担银行破产成本。德国规定了诸多劣后债权,如债权人参与程序的费用(如律师费)、罚款和罚金、慈善承诺、股东借贷等。[40]然而,利益关联方所形成的债权劣后于普通债权将遏制利益关联人给予银行拯救的动机,从而增加了问题银行通过市场方式予以拯救的难度。基于现实的需要,对利益关联方所形成的债权不应一刀切地纳入次级债权,倘若债权人证明其债权属于正常交易行为则可被列入普通债权。内部交易所形成的债权构成欺诈,则被列入次级债权。
(四)普通债权人
银行清算时,普通债权人清偿率极低,承担主要的银行处置成本。因此,普通债权人位于股东、高管、次级债权人后承担银行处置的损失。
首先,处置机构出于金融稳定考虑可能对于同一类别的债权人实行不同的待遇。[41]银行处置时,普通债权人待遇并非根据一般破产法的平等原则,而是根据公平合理原则。[42]公平原则要求所有普通债权人的待遇不能低于模拟清算所得,而合理原则对银行运营必需的货物或服务所形成的债权(如网络服务、租赁和维护基础设施所形成的债权)给予特殊对待。
其次,基于政策考量对部分普通债权予以特殊保护。如超过存款保险限额部分的存款,虽属于普通债权却可能事实上优先于普通债权。鉴于中小型企业对于国家经济的重要影响,处置机构也可以对中小型企业保险范围以外的存款给予保护。[43]是否给予此类存款特殊待遇,主要根据各国处置机构的自由裁量权,如不给予此类存款保护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或影响经济发展。
(五)优先债权人
优先债权人位于普通债权人之后承担银行处置的成本,代表着不同的政策考量和应予以保护的利益。优先债权主要包括处置费用(破产费用)、共益债务、存款、职工债权、养老金、医疗保险、公共援助资金、税收。[44]各国不同的银行处置政策考量给予了优先债权人不同的待遇。[45]
首先,处置费用与共益债务属于最优先的债权人,该类债权受到最优先的保障以便推进处置程序的顺利进行。为鼓励市场参与方给进入处置程序的银行提供资金支持,美国将此类融资列入共益债务享有优先权。[46]实践中,私人主体往往很少为被处置银行提供融资,往往是国家提供了援助。此类援助理应属于共益债务从而优先于其他优先债权人,中央银行或处置机构所提供的金融援助即属于此类。许多国家要求银行为央行的援助提供足额担保并支付惩罚性利息,然而个别国家则并没有要求提供担保。[47]公共机关提供的无担保处置资金应列为共益债务从而享有优先权。
其次,保障范围内的存款享有绝对优先,而非保障范围内存款则根据一般破产规则予以确定。各国往往给予存款人优先权,存款保险机构支出保险金后代位获得存款人的优先权。而对于超出保险范围的存款,各国根据本国的需求确定其地位。当被处置银行资产不能满足全部存款需求时,保险范围内存款优先于超出保障范围之存款。中国和美国将全部存款都优先于普通债权[48],欧盟《恢复与处置指令》则将保障范围内的存款列为优先,而成员国根据本国需要确定保障范围外的存款在处置程序中的位置。[49]英国和德国都将存款列为优先债权,却有不同的规则。英国规定保险范围的存款与优先部分的职工债权位于同一顺位,个人和中小企业超出保险范围的存款债权则劣后于上述债权。德国则规定大公司、金融机构与政府存款不属于享有优先权的存款范围。
再次,符合特定条件的雇员债权属于优先债权。出于劳工保护和社会稳定的政策考量,各国普通破产法通常给予职工债权特殊的保障,让其享有优先权。然而,相比其他行业,金融业雇员往往薪酬较高,让雇员承担部分损失也有利于人员流动到更稳健的银行,而给所有的职工债权赋予优先权也对普通债权人产生了不公平的分配效果。因此,许多国家并非一味地赋予职工债权优先性,而是区分银行雇员在银行陷入风险中的角色给予特殊安排。如美国规定银行董事和高管薪酬仅优先于股东却劣后于次级债权[50],一般银行雇员在接管前180天内的职工债权优先上限为11725美金。[51]英国则规定享有优先的雇员薪酬上限为800英镑[52],而银行雇员的医疗、养老等债权也属于优先权上限范围之列。此外,并非所有普通员工的薪酬都具有优先性,固定薪酬的部分才享有优先,出于激励性质的薪酬部分和福利部分则不属于优先范围。因此,职工优先政策并非不受限制的优先,而是在特定的数额内享有优先,只有抵御风险能力差且对银行陷入危机没有直接关系的普通员工才享有优先权。
最后,个别国家在普通破产程序中将税收债权优先于一般债权,而银行处置的特殊性使得税收债权的优先失去了必要性。通常而言,银行处置维系一国金融稳定,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必要时处置机构往往动用公共资金。当被处置银行难以通过市场获得融资,公共机构提供的资金渠道往往成为唯一选择。[53]而处置资金原则上属于公共资金,税收债权与普通债权同一顺位承担处置成本也与处置银行的初衷相一致。此外,税收债权的优先将遏制潜在的市场买家收购问题银行,从而不利于成功处置银行。许多国家为了有效处置银行并没有将税收债权作为优先债,而是作为一般债权,由其部分承担银行处置的成本。英国《企业法2002》废除了税收债权的优先性,银行处置时税收债权也失去了相应的优先地位。[54]
总之,优先债权人的确定应当基于必要的政策考量以及银行处置的特殊需求。银行处置的政策考量有别于一般公司破产,因此优先债权人的范围也有别于普通破产程序下的优先债权人。
(六)担保债权人
各国的银行处置程序都保障担保债权人的利益,担保债权人在担保物价值范围内优先于所有债权人。为了顺利推进银行处置程序,担保权人行使担保权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银行资产的挥发性也可能导致担保物价值的挥发,从而担保权人事实上也可能部分承担银行处置的成本。然而,各国担保法的差异导致了不同的担保权在银行处置程序中的差异。英国担保法除了认可抵押、质押等一般担保外,还给予准担保性质的利益具有类似的担保权。准担保性质的担保权包括所有权保留买卖、回购、融资租赁,以及资本市场上具有担保性质的金融交易。[55]而为了避免担保权受损害,英国规定银行处置实施资产剥离措施时,担保债权不能与担保物相分离。[56]许多国家也将具有担保性质的金融合同予以特殊处置,从而不受中止、取消或撤销金融交易的限制,以避免系统性风险。[57]虽然有人提议让担保权人也部分承担银行处置的成本,但当前各国银行处置规则并没有对担保作出特殊限制。
我国银行处置成本的分担及制度完善
(一)银行处置实践及成本分担现状
历史上,当我国银行陷入危机时,国家往往倾向于动用公共资金处置陷入困境银行。由于存款保险制度的缺失,通常采用其他银行兼并的方式维持金融稳定,并对全体存款人提供保护。1998年海南发展银行就因兼并陷入困境的其他银行而破产,此种方式让兼并银行承担了破产银行的处置成本。而当国家动用公共资金处置海南发展银行时,国家承担了主要的处置成本。为了维持金融稳定,国家频繁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能,提供公共资金援助和政策支持来处置银行风险。[58]2015年建立的存款保险制度不仅规定了存款人的保障额度,还授权存款保险机构提供担保、损失分担或资金支持,以促成收购或承担被处置银行的资产、业务、负债。[59]因此,存款保险机构将承担银行处置的直接成本。
2019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与银保监会接管包商银行。[60]存款保险基金和中国人民银行提供资金对个人存款和绝大多数机构债权(5000万元以下)给予全额保障,大额机构债权(5000万元以上)则提供90%的保障。[61]随后,接管组通过新设立银行收购与承接包商银行的债权与债务。中国人民银行向包商银行提供了235亿流动性支持,而存款保险机构则分担资产减值损失,为兼并方提供资金支持。[62]经过接管组的前期处置,包商银行进入司法清算程序,并于2021年8月终结清算程序。[63]包商银行破产反映了我国银行处置成本分担的现状,却存在诸多商榷之处。
首先,我国银行处置成本承担遵循了股东优先承担损失的原则。包商银行的处置过程中遵循了股东优先承担损失的原则,股东权益和一、二级资本债务全部清零。而由于股东前期的违法经营行为已经完全掏空了银行资产,将股权和资本债务清零仅确认了股权价值为零的事实。相比前期股东从银行违规套取的资金规模,股东实际上并没有承担银行处置的损失。
其次,处置机构出于金融稳定的目的,对同一位阶的债权人实行了区别对待。5000万以下的机构债权和5000万以上的债权属同一类别债权,如果不属于信托或法定优先范围,均属于普通债权,这与后续进入清算的2000多亿普通债权都属于同一位阶。同一位阶的债权人应受到相同的待遇,而对大额机构债权与小额债权实行不同的待遇也导致了不公平的结果。普通债权应当受到类似的待遇,进入清算后的普通债权清偿率为零,而收购承接前的普通债权却受到保障。大额机构能影响银行行为,有足够的能力挑选稳健的银行,给予此类机构债权保障无疑将削弱市场约束。
再次,使用公共资金推进处置措施,却没有为公共资金提供足够的保障,从而让公共资金承担了银行处置的成本。中央银行提供流动性支持时银行提供了优质资产作为担保,而存款保险金却先于普通债权承担了资产减值,其提供兼并资金成为新设银行股东,却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保障资金的安全,甚至在清算中还遭受了损失。
最后,没有严格依据分担位阶承担处置成本,与现行法律存在冲突也不利于建立有效的市场约束。个人存款与理财客户属于不同位阶的债权,存款债权属于优先债权,而理财性质债权则属于普通债权,将理财产品与存款作为同等保障违背了债权的清偿顺序。进入清算程序时,存款保险基金仍然有6亿多的个人存款债权,而剩余728家普通债权人有2000多亿普通债权,上述债权因包商银行无财产清偿而承担全部损失。[64]享有优先权的存款债权遭受了损失,而部分普通债权却获得全额保护,这鼓励了大机构债权人的道德风险,削弱了市场规则。
总之,使用国家信用和公共资金对所有储户提供保障,并扩大非储户债权人的保障,有利于维护市场信心以及金融稳定,保障众多债权人的利益。上述措施应当在极端情形如发生系统性风险、一般风险处置措施无法有效处置风险时考虑使用,而不应当作为常规性处置措施。《存款保险条例》已经为存款人提供足够的保障,大多数普通民众和存款人能得到保障,超过限额部分可优先于普通债权。对包商银行的处置措施又回到了原先国家提供无限担保并动用资金处置金融风险的老路,而实践证明以往的处置措施不仅导致公共资金损失,也不利于机构债权人更谨慎地挑选交易对手。给予机构债权人和部分普通债权人保护实际上是刚性兑付思维的延续,并非有效的处置银行风险的路径。公共资金先于普通债权人承担银行处置成本,也违背了国际通行的银行处置成本的分担规则,这将削弱市场的约束力量,导致银行债权人、储户的道德风险以及公共资金的损失。
(二)我国银行处置成本分担制度的完善
我国现行法律与监管规则建立了银行处置成本的分担规则。2020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修改建议稿)》专章规定了银行风险处置机制,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稳定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也涉及银行风险处置,而银行处置成本分担位阶仍有待完善。
(1)银行股东优先承担损失
近年来的法律和监管规则进一步确认了银行股东优先承担银行处置成本的原则。2021年《银行保险机构恢复和处置计划实施暂行办法》确立了自救原则,银行应使用自有资产、股东救助处置银行风险,股东将在正式处置程序前先行承担自救成本。[65]《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稳定法(草案征求意见稿)》进一步确立了金融机构股东和实控人通过自救、追回薪酬优先承担处置成本的原则,[66]然而现存的股东损失分担规则仍不符合现实需求。
首先,有限责任使得股东的责任以出资为限,让其有足够动机利用银行实现套利。包商银行破产事件表明,现有规则难以让破产银行股东承担相应的处置成本。股东利用其所控制的银行掏空银行资产,而处置机关被迫动用公共资金对部分债权人提供保障,获利股东将银行破产成本转嫁给了国家与部分债权人。因此,应当建立相应的规则,让对银行破产负有责任的股东承担有限责任范围外的成本,并区别对待股东正常的商业决策与利用影响力致使银行陷入困境的股东责任。尤其是当自然人或法人股东恶意或重大过失行为导致银行进入风险处置程序,更应让其承担有限责任之外的义务。
其次,限制银行股东与银行之间交易形成的债权地位。股东与银行之间的债权应当受到严格的审视,防止股东利用其影响力让银行承担不公平的债权。即便是正常交易所形成的债权,实行更严厉的破产法的国家如德国和克罗地亚也往往让股东债权劣后于普通债权。[67]我国多起银行处置事件都涉嫌股东滥用影响力导致银行陷入困境,更凸显了对银行股东实行更严格的债权审核的必要性。
最后,建立破产银行股东的民事与刑事责任。导致银行陷入困境的股东往往是企业法人。当对银行进行处置时,其控股股东也往往资产损耗殆尽,此时应当由控股股东的实控人承担相应的责任。立法应当授权监管机构根据银行破产所造成的损失对银行股东或实控人提起诉讼,让其承担损害赔偿。当前,《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稳定法(草案征求意见稿)》虽然规定了金融机构股东和实控人违法行为的责任[68],却缺乏配套的刑事规则有效惩戒银行股东其他行为所导致的银行破产。因此,应当制定银行破产相关的刑事条款,对于因重大过失或故意致使银行进入处置程序,导致国家、个人重大损失或危及金融体系稳定的,必须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2)细化职工债权规则
我国《企业破产法》将职工相关债权劣后于破产费用与共益债务并优先于其他债权,却没有对相关债权予以总额限制。[69]《商业银行法》沿袭了《企业破产法》的原则,给予此类债权类似的优先,却没有对一般职工与高管的债权予以区别对待。[70]2020年12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修改建议稿)》复制了《企业破产法》中职工债权的优先性,将职工债权优先于存款、税收债权、流动性援助债权和普通债权。[71]《商业银行法》仅将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优先于存款,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修改建议稿)》却将职工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职工补偿金都列为应当优先的职工债权,这无疑受到了《企业破产法》对职工保护的影响,却没有考虑银行破产的特殊性,不符合有效分担银行处置成本的原则。
首先,银行业的职工债权不应与普通破产企业职工债权获得同等的保护。我国公司破产所确定的职工债权保护原则是特定历史原因和特殊政策需求的产物。历史上,我国许多陷入困境的国企拖欠职工工资、医疗和养老等费用,却没有及时进入破产程序。随着国企改制的推进,大量工人下岗对社会稳定造成了影响。如此背景下,给予普通职工上述债权优先性有利于社会稳定,推进企业改革。给予一般企业职工更宽泛的债权保护,是为了维持职工及其家庭的基本生存需要。而当前银行业并没有面临类似的历史性难题和类似的职工生存需求。与一般公司相比,银行业总体薪酬更高,银行雇员普遍拥有更强的专业性,其比一般公司雇员有更强的职业选择和避险能力。过于宽泛的职工相关债权的保护不利于银行雇员从差的银行跳槽到好的银行,从而实现市场的优胜劣汰。职工工资、医疗、养老保险和补偿金分别代表着不同政策需求,《商业银行法》限缩职工优先债权的范围,恰恰是考虑了银行业的特殊性。因此,无需给予银行职工债权范围过宽的优先。
其次,应对不同职工债权进行区别对待。一般企业职工往往被动地成为债权人,而银行雇员与银行破产有更紧密的联系。银行高管对银行陷入困境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应当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代价。我国《企业破产法》规定了企业高管的工资按照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来计算,而破产银行高管工资却没有类似的规定。因此,应当对破产普通职工与高管予以区别对待。美国的破产银行高管工资债权仅优先于股东,恰恰是考虑到了银行与一般公司的差异。
再次,除了限缩一般银行职工债权范围外,还应当限制职工债权总额。让职工债权优先于其他债权是对陷入破产且处于弱势地位的职工的一种特殊保护,其根本目的是满足基本的生存和生活需求。英国和美国都对享有优先权的职工债权予以总额的限制,恰恰是出于此种考虑。而银行业许多薪酬和保障具有福利性质,并非满足其基本生活需求。银行雇员在业务繁荣时享受了高额的薪酬、各种福利,当其陷入困境时则应当部分承担相应成本。不对银行职工相关债权的优先数额予以限制,事实上降低了更需要予以保障的债权人的清偿率,导致了不公平结果。
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修改建议稿)》的职工优先规则不符合银行破产的现实情况。银行一般雇员的工作对于维系银行正常经营及银行资产具有重要意义,给予其优先权不仅具有劳工政策的考虑,同时也是现实的需求,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修改建议稿)》却将职工相关的债权优先于存款、税收、央行提供贷款和流动性援助所形成的债权。公共机关提供的贷款和流动性援助目的是为了顺利处置陷入困境的银行,其目的是为了全体债权人利益,本质上具有共益债的性质。让极其宽泛且不加以数额限制的职工相关债权优先于此类债权,导致全体纳税人承担了本应由银行雇员承担的处置成本,容易引发道德风险问题,同时也可能导致公共资金遭受损失。
(3)完善存款优先原则
各国银行处置制度都对存款这一涉众性债权给予特殊的保障,普遍建立了存款优先原则,其目的主要是防止储户挤兑和银行处置时便于转移和剥离涉存款业务。[72]《金融机构撤销条例》和《商业银行法》都确立了存款优先的原则,[73]这是因为我国当时并未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上述规则有利于保障存款人利益,维护社会稳定。2015年建立的存款保险制度已经为绝大多数存款人提供了保障,而202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修改建议稿)》仍将存款本金和利息优先于除破产费用、共益债务和职工债权外的其他债权。对存款的过度保障,不仅削弱了市场约束,也不利于有效分担处置成本。
首先,对所有存款给予无区别优先权将导致道德风险问题,不利于促进银行业的稳健运行。鉴于我国居民存款现状,50万的保险限额保障了绝大多数的个人和家庭存款,满足了经济稳定和保障储户利益的需求。超过保险限额部分的存款是否应当同保险限额内的存款处于同一优先位置,是各国银行破产制度无法回避的问题。对于保险限额较低的国家,让超过限额部分的存款拥有类似的优先权有助于保障普通储户的利益。而当保险额度能覆盖绝大多数普通民众的存款时,则降低了让其获得保障部分同样优先的必要性。因此,绝大多数国家将保险限额内的存款与保险限额外的部分予以区分,而非不受限制地给予同样的优先。此外,保险限额内的部分与限额外的部分虽然都属于存款,但其代表着不同的阶层利益和政策考量。由于信息不对称,普通民众难以监控银行行为,也容易基于错误判断而形成银行挤兑。而大额存款机构不仅具有更强的抵御风险能力,也能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选择好的银行来实现市场的优胜劣汰。不加区别地对大额存款和小额存款给予同样的保护,将使得大额存款机构忽视银行的安全性而以收益作为其挑选交易对象的主要原因,从而产生道德风险问题。因此,应当对大额存款与保险范围内的存款予以区别对待,迫使其更谨慎地选择储蓄银行,从而遏制银行从事高风险的活动,促进银行业的稳健运行。
其次,对于中小企业存款给予特殊保障。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大量中小企业破产,而此类企业又关乎经济发展、就业等诸多政策性考量。欧盟的银行处置机制给予中小企业存款特殊的保障,恰恰是考虑中小企业的特殊需求。中小企业超过存款保险限额部分应当与超过保险限额的个人存款享有类似的优先权。
最后,存款优先原则应当满足公平分担处置成本的要求。不同类型的存款对于银行陷入困境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普通存款人属于破产银行被动的债权人,与银行陷入困境并无直接关系。而机构性存款则与银行陷入困境有更密切的联系,其有能力关注相关银行的稳健性,甚至明知银行开展不稳健业务时仍然选择将大额存款存于此类银行以获取更高的收益。此时,机构的大额存款便利了银行开展不稳健的业务,与银行陷入困境有更密切的联系。因此,当银行进入处置程序时,此类机构应承担相应的成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修改建议稿)》将机构大额存款优先于税收、中国人民银行提供的贷款和流动性支持,后者为了有效维护金融稳定和全体债权人利益,却要劣后于大额存款,这明显让国家承担了部分由大额机构应当承担的处置成本,不符合公平分担处置成本的原则。
(4)合理定位公共债权位阶
我国银行处置机构涉及更多的公共债权,包括存款保险机构债权、税收债权以及政府救助或中国人民银行贷款或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能所形成的债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稳定法(草案征求意见稿)》规定国家建立金融稳定保障基金,却没有提供相应的债权顺序规则,使得此类公共债权在银行处置中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74]不同的公共债权在银行处置程序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这直接决定银行风险处置成本的分担位阶。
首先,对于税收机关而言,其完全是被动地成为被处置银行的债权人,税收对于银行处置程序也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除了清算程序之外,银行的其他处置程序与税收债权并无太多的关联。当银行启动清算程序时,税收债权是否享有优先取决于一国的具体政策考量。由于银行处置涉及广大存款人,超过保险范围的存款应当优先于税收债权,以维持金融稳定。
其次,为推进银行处置而提供的公共资金贷款具有共益债的性质,应优先于其他优先债权。存款保险公司为促进收购与承接所提供的援助资金、中国人民银行贷款或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能所形成的债权、金融稳定基金提供的贷款皆属于此类性质的公共债权。而存款保险机构赔付存款保险金后代位取得存款人的地位,应当劣后于破产费用、共益债务与职工债权而优先于其他债权。
结语
银行处置成本的分担应综合考虑银行处置所涉及的直接与间接成本,事先建立可预见性、市场化、公平的成本分担机制。银行处置所涉及的主体承担成本位阶是建立有效的成本分担机制的前提。立法应当明确各个主体的成本分担位阶,让利益关联方对处置结果有可预见性,从而引导其行为。
根据市场化的原则,对银行进入处置程序负有责任的市场主体(股东、董事)应当优先承担银行处置的成本。现有的成本分担机制并没有让对银行陷入困境的直接责任主体承担相应的成本,仅仅让股东自救或核销股权并不能建立有效的成本分担机制。穿透公司股权结构、让相关人员承担额外的责任不仅能遏制股东和高管的冒险行为,也将阻止银行破产成本的外部化,让成本分担机制更为合理。
公平原则要求对银行处置涉及的弱势主体予以特殊保障,普通职工、小额存款人等皆属此类。与银行破产密切相关且抵御风险能力较强的机构,则应通过让其债权劣后实现公平分担银行处置成本。
总之,有效的银行处置成本分担规则有助于遏制银行风险行为,减少破产的风险。破产银行处置应当满足市场化和公平分担原则,尽可能降低银行处置的成本,避免公共资金在处置过程中的损失。
注释:
[1] 刘少军:《商业银行法组织制度修改中的权责分配问题》,《现代法学》2021年第1期;周仲飞:《金融机构强制自救债的法律问题》,《现代法学》2015年第2期。
[2] 齐明、刘雯丽:《我国商业银行破产存款人权益优先保护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8期。
[3] L. Laeven, F. Valencia,“Systemic Banking Crises Database”, IMF Economic Review, 2013, 61(2), pp.225-270.
[4] R.Cranston, E.Avgouleas(eds.),Principles of Banking La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171;苏洁澈:《金融危机干预措施的合宪性审查———英美处置破产银行及启示》,《政法论坛》2021年第4期。
[5] A. J. Levitin, “In Defense of Bailouts”, The Georgetown Law Journal, 2011, 99, pp.508-510.
[6] M. Schillig, Resolution and Insolvency of Bank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133;P. P. Swire, “Bank Insolvency Law Now That It Matters Again”,
Duke Law Journal, 1992, 42(3), pp.469-556.
[7] M. B. Grimaldi, J. Hofmeister, S. Schich, “Estimating the Size and Incidence of Bank Resolution Costs for Selected Banks in OECD Countries”,Financial Market Trends, 2016, 1, pp.7-42.
[8] D. R. Lee, Politics, “Ideology, and The Power of Public Choice”, Virginia Law Review, 1988, 74(2), pp.191-198; W. A. Boot and Anjan V. Thakor, “Self-Interested Bank Regulati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3, 83(2), pp.206-212.
[9] D. Evanof, G. Kaufman, Systemic Financial Crises: Resolving Large Bank Insolvencies, Chicago: World Scientific Press, 2005, p.123.
[10] J. Cunliffe, “Ending Too-Big-to-Fail: How Best to Deal with Failed Large Banks”, European Economy, 2016, 2, pp.59-74.
[11] A. J. Levitin, “In Defense of Bailouts”, The Georgetown Law Journal, 2011, 99, pp.435-514.
[12] R. Goyal, P. K. Brooks, M. Pradhan, A Banking Union for the Euro Area, IMF, 2013, p. 8;S. N. Grunewald, The Resolution of Cross-Border Banking Cris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A Legal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urden Sharing, Den Haag, Kluwer Law Press, 2014, pp. 30-31.
[13] G. Boccuzzi, The European Banking Union: Supervision and Resolution, London: Palgrave Press, 2016, p. 49;A. J. Levitin, “In Defense of Bailouts”, The Georgetown Law Journal, 2011,
99, pp. 435-514.
[14] D. S. Hoelscher, Bank Restructuring and Resolution, New York: Palgrave Press, 2006, p. 99.
[15] S. N. Grunewald, The Resolution of Cross-Border Banking Cris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A Legal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urden Sharing, Den Haag, Kluwer Law Press, 2014, p. 29.
[16] IMF & World Bank, An Overview of the Legal, Institutional, and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Bank Insolvency, 2009, p. 35, 63.
[17] M. Flannery, S. Sorescu, “Evidence of Bank Market Discipline in Subordinated Debenture Yields:1983-1991”, The Journal of Finance, 1996, 51(4), pp. 1347-1377.
[18] Directive 2014/59/EU, art. 100.
[19] S. N. Grunewald, The Resolution of Cross-Border Banking Cris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A Legal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urden Sharing, Den Haag, Kluwer Law Press, 2014, p. 90.
[20] Directive 2014/59/EU, art. 72;12 USC § 5390(a)(1)(A).
[21] K. Alexander, “Bank Resolution Regimes: Balancing Prudential Regulation and Shareholder Rights”, Journal of Corporate Law Studies, 2009, 9(1), pp. 61-93.
[22] Banking Act 2009, s. 13(2), s57.
[23] Directive 2014/59/EU, art. 47(1).
[24] 12 USC § 1831o-1;A. B. Ashcraft, “Are Banking Holding Companies a Source of Strength to Their Banking Subsidiaries?”,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2008, 40(2), pp. 273-294.
[25] H. E. Jackson, “The Expanding Obligations of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ies”, Harvard Law Review, 1994, 107, pp. 507-619;R. Ridyard, “Toward a Bank Shareholder-orientated Model: Using
Double Liability to Mitigate Excessive Risk-taking”, UCL Journal of Law and Jurisprudence, 2013, 2(1), pp. 141-172.
[26] Directive 2014/59/EU, Art19, 23, 24.
[27] 12 USC § 5390(s). 追回时间为任命接管人后两年, 如上述人员涉嫌欺诈则不受时间限制。
[28] M. S. Barr, H. E. Jackson, M. E. Tahyar,Financial Regulation: Law and Policy, New York, Foundation Press, 2016, 6, pp. 812-3;I. H. Chiu, “Regulatory Duties for Directors in the
Financial Services Sector and Directors' Duties in Company Law: Bifurcation and Interfaces”, Journal of Business Law, 2016, 6, pp. 468-473;A. Arora,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Failings i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Directors' Legal Liability”, Company Lawyer, 2011, 32(1), pp. 3-18.
[29] 12 U. S. C§1821(k);P. A. Lowy, “The Director Liability Provision of th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Reform, Recovery and Enforcement Act: What Does It Do”, Annual Review of Banking Law,
1997, 16, pp. 355-396.
[30] E. S. May, “Bank Directors Beware: Post-Crisis Bank Director Liability”, North Carolina Banking Institute, 2015, 19, pp. 31-51;M. C. Gill, “Claims Against Bank Directors and Officers
Arising from the Financial Crisis”, Review of Banking and Financial Services, 2010, 26, pp. 69-75.
[31] E. S. May, “Bank Directors Beware: Post-Crisis Bank Director Liability”, North Carolina Banking Institute, 2015, 19, pp. 31-51.
[32] Financial Service(Banking Reform) Act 2013, part4;I. H. Chiu, “Regulatory Duties for Directors in the Financial Services Sector and Directors”Duties in Company Law: Bifurcation and
Interfaces”,Journal of Business Law, 2016, 6, pp. 465-490.
[33] Directive 2014/59/EU, Art. 34(1)(e).
[34] Financial Service (Banking Reform) Act 2013, Art. 36(1).
[35] Financial Service (Banking Reform) Act 2013, Art. 36(4).
[36] G. Baber, “Changing Banking for Good: No More Reckless Misconduct”, Company Lawyer, 2013, 34, pp. 340-347;R. Cranston and E. Avgouleas(eds. ), Principles of Banking La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106.
[37]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CAP, Definition of Capital, BIS, 2019, p. 27.
[38] Directive 2014/59/EU, Recital77.
[39] P. P. Swire, “Bank Insolvency Law Now That It Matters Again”, Duke Law Journal, 1992, 42(3), pp. 469-556.
[40] 只有占股不超过10%,进入处置程序后的股东借贷不属于劣后债权。M. Schillig, Resolution and Insolvency of Bank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377。
[41] P. R. Wood, “The Bankruptcy Ladder of Priorities and the Inequalities of Life”, Hofstra Law Review, 2011, 40, pp. 93-101;L. Janssen, “Bail-in From an Insolvency Law Perspectiv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anking Law and Regulation, 2018, 33, pp. 1-23.
[42] C. Hadjiemmanuil, Bank Stakeholders' Mandatory Contribution to Resolution Financing: Principle and Ambiguities of Bail-In, ECB Legal Conference, 2015, p. 242; Directive 2014/59/EU,
Art. 34(1)(f).
[43] Directive 2014/59/EU, art. 44(3).
[44] P. R. Wood, “The Bankruptcy Ladder of Priorities and the Inequalities of Life”, Hofstra Law Review, 2011, 40, pp. 93-101.
[45] 英国仅将存款和一定范围内的职工债权作为劣后于破产费用的优先债权人。
[46] 12 USC § 5390(b)(2).
[47] Andrew Campbell and Rosa Lastra, “Revisiting the Lender of Last Resort”, Banking& Finance Law Review, 2009, 24(3), pp. 453-498.
[48]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71条;12USC§1815(e)(2)(C);12 USC§1821(d)(11)。
[49] Directive 2014/59/EU, Art. 108.
[50] 12 USC § 5390(b)(1).
[51] 上述数额包括雇员薪酬、各种其他福利、医疗、养老金等债权。参见:12USC§5390(b)(1)(C)。
[52] Insolvency Act1986, s387; M. Schillig, Resolution and Insolvency of Bank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368-369.
[53] R. Cranston and E. Avgouleas, Principles of Banking La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173.
[54] Insolvency Act 1986, Schedule6.
[55] M. Schillig, Resolution and Insolvency of Bank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367.
[56] The Banking Act 2009(Restriction of Partial Property Transfers) Order 2009, Art. 5.
[57] 11 USC § 362(a).
[59] 《存款保险条例》第5、18条。
[63]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01破270号之三民事裁定书。
[64]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01破270号之三民事裁定书。
[65] 《银行保险机构恢复与处置计划实施暂行办法》(银保监发〔2021〕16号)第3条。
[66] 《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稳定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第15、21、24、32条。
[67] Single Resolution Board, Annex3, Insolvench Ranking in the Jurisdictions of the Banking Union, 2021, p. 16, 35,http://www. srb.
europa.eu/system/files/media/document/LDR%20%20Annex%20on%20Insolvency%20ranking
[68] 《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稳定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第41条。
[69] 《企业破产法》第113条。
[70] 《商业银行法》第71条。
[71]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修改建议稿)》第102条。
[72] M. Haentjens, W. Bob(eds. ), Research Handbook on Crisis Management in the Banking Sector,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ress, 2015, p. 97.
[73] 国务院:《金融机构撤销条例》,2001年,(国务院324号)第23-24条;《商业银行法》第71条。
[74] 《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稳定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第29条。
王玲芳:混合企业救援实践下的预重整制度构建
丁海湖:个人破产逃废债的防范
解除还是履行?——保险公司重整中的待履行保险合同挑拣权的限制
丁燕:预重整融资法律制度的立法价值与规则构建
苏洁澈:银行风险处置中的“公平审判”原则——欧洲经验及启示
何欢:债务清理上破产法与执行法的关系(附脚注版)
王毓莹:论我国上市公司重整中的“府院失衡现象”及其协调
“假马竞价”在破产重整投资人引入中的应用分析
司法实践视野下自然人破产免责制度的构建
郭帅:《金融稳定法(草案征求意见稿)》评析——健全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和处置机制
评王静《实质合并破产法律制度构造研究》——寻求实质合并破产案件审理方式的实然与应然
韩长印:中小企业重整的法理阐释与制度重构
王静:实质合并适用标准体系之重构
上市公司破产事项监管发出“更强音”
殷慧芬:自然人破产程序中管理人的履职困境及其纾解(附脚注版)
刘琨:跨境破产协助中的管辖权问题
重整程序中非消费型不动产买受人的权利实现
名师解读:国际破产法模拟法庭赛题在关注什么?
论破产约定条款的效力认定规则
债券发行人破产时债券受托管理人/资管管理人债权申报和受偿问题研究
债权人破产中保理人权利保护之实务研究
两地跨境破产起步走:示范法的“中国之旅”
池伟宏:困境企业拯救的破产重整路径效率优化
上市公司破产重整中出资人权益调整机制之完善
殷慧芬:论自然人破产法的适用主体(附脚注版)
破产程序中的债权人信息获取权和信息保密问题
刘静、齐砺杰:如何构建中国个人破产制度
快速的个人破产:澳大利亚个人破产制度未来改革方向
闲谈共益债务的“是是非非”
走进跨境破产的新世界:Fletcher Moot
Ian Fletcher国际破产模拟法庭 天同赞助队伍再闯决赛圈
张子弦:日本法庭外个人债务清理程序——特定调解程序的具体运用
池伟宏:扫清管理人履职障碍 推动破产配套制度改革——评《推动和保障管理人依法履职意见》
王斐民:个人破产法的宪法维度
担保制度修订之破产新解:十问十答
退市新规对上市公司重整的影响
毕业季,选择破产律师需要了解些什么?
苏洁澈:英美银行破产法述评——以银行特殊破产制度为中心
杜万华:破产管理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井上聡 陈景善[译]:试论信托与破产——以日本法为视角
魏铭声:“一带一路”和中国跨境破产法
池伟宏:《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对我国银行信用卡业务影响评析
殷慧芬:自然人破产立法的国际化与本土化
苏洁澈译:银行破产是什么?
贺丹:企业集团破产中的程序协同
深圳个人破产条例不得不了解的15个问题
金春:个人破产立法与企业经营者保证责任问题研究
德国消费者破产模式的优势和不足:对于克罗地亚立法者的启示
石静霞:论香港法院对内地破产程序的承认与协助:以“华信案”为视角
跨境破产程序中法院合作模式探索 ——新加坡JIN联盟的启示
评论:最高法院指导意见(二)与《全球指南》总结报告—关于涉疫情破产案件的审理
破产和解向司法程序前迁移的改革思考 ——从西王集团和解案说起
池伟宏:管理人独立发拍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路径
布局苏渝,揽将添翼——天同破产重组业务2020年全新升级
张思明:破产重整债务人自行管理模式的适用性分析
法国破产重整方案中的债转股问题研究
韩长印:重整程序中的小额债权清偿机制问题
破产重整中债转股的监管因素考量 ——以商业银行监管政策为视角
姜天萃:执行网拍与破产网拍的异同——公法与经济法的分野
李忠鲜:论担保权在破产清算程序中的别除机制
林康司:资产证券化与破产
胡利玲:如何理解破产临界期内“个别清偿使债务人财产受益” ?——对我国偏颇清偿例外的重释与情形补足
池伟宏:再论重整程序中的股东权益调整与绝对优先原则
董璐:资不抵债下股东在重整程序中的表决权排除
丁燕:破产重整企业债权融资的异化及其解决
池伟宏、韩会师解读个人破产制度:纵容“老赖”?下半年试点?
池伟宏:破产制度五大改革方案出台,巩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最后一道防线 ——评《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
苏洁澈:金融监管机构在金融机构破产中的角色
殷慧芬:个人破产立法的现实基础和基本理念
徐战成:破产重整中债务重组的企业所得税处理规则
外国破产程序和重整计划的承认与协助
跨境破产及内地/香港司法合作
破产法司法解释(三)全面解读与分析(程序篇)——以债权人利益保护为视角
破产法司法解释(三)全面解读与分析(实体篇)——以债权人利益保护为视角
破产管理人制度的体系性改革——从加拿大破产法体系的比较法视角
数字货币与破产
叶炳坤:跨境破产中的司法协助与本国债权人利益保护
韩国破产法院的设立和破产法改革
债权人会议非法定表决事项的处理|破产池语
管理人/债权人/投资人:谁决定破产重整的方向?
论重整计划的制定——破产重整程序的关键环节之一
东北特钢重整案:债转股在破产重整程序中的运用
【求贤令】天同破产重组团队主办律师招新
【天招字号】-6张天同破产重组实习券待领取
破产重整投资人的选任和保护
破产程序中的金融合约“安全港”——安全边界的功能性定位
不动产抵押“房地一体”原则的例外——以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为视角
破产法视角下的仲裁:实体与程序
李忠鲜:担保债权受破产重整限制之法理与限度
重整程序中逾期申报债权之限制——基于正当理由的考量
待履行房屋租赁合同在破产程序中的处理规则
全球个人破产法的现状和最新改革动向——个人破产制度与幸福生活、创业激励
如何做到个人破产免责与防止滥用的平衡?
胡萝卜加大棒:个人破产法永恒的主题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Lamar v. Appling案判决述评
中国为什么要推行个人破产法?
承租人破产时的融资租赁合同处理规则
为什么说中国执行转破产是独树一帜的?
德国破产法:破产程序启动前的财产保全制度
破产 “保护伞”程序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池伟宏:寂茕来时路,明日尤可期
责任编辑:
}
我要回帖
更多推荐
- ·INS直播,会提醒主播关注的人进入直播间吗?看直播的人能看到关注的人进入共同关注的主播ins如何看别人的直播播间吗?
- ·这种有哪些ai生成图片的软件用上什么AI软件做的?
- ·中国国民党党史馆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旧址位置
- ·warframe配卡 gauss配色跪求(审美太差了)
- ·谁用过的比较好用滋润公认最好用的身体乳乳推荐下呗?
- ·阿木塔蒙古风情岛的经济创收情况情况?
- ·下列关于人民币的表述正确的有法律地位主要体现在以下哪些方面?()
- ·月薪一万七在中国人真实的收入水平属于什么水平
- ·永城万达市场规划图广场选址在哪里
- ·柜员多给钱客户不过还可以报警吗1000块钱报警有用吗
- ·在信息科技治理组织架构方面,商业银行组织架构中应( )。
- ·下列属于现代商业银行具有的特点有应当正确认识并深刻理解所面临的各类金融风险,因为相对于一般企业( )。
- ·下列属于现代商业银行具有的特点有应当正确认识并深刻理解所面临的各类金融风险,因为相对于一般企业( )。
- ·银行卡反诈中心解封流程冻结银行卡,银行方面给公安局开证明,需要一周时间
- ·早期为什么制药企业要实施GMP和监管部门对安全性的监管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 ·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的形式包括应与银行的经营特点相适应,原则包括()。
- ·在我国商业银行组织架构的选择,需要综合,高管层层面普遍设立的机构有( )。
- ·下列关于假个贷的表述错误的是属于个人信贷业务内容的有( )。
- ·商品风险源于商品合约货币具有时间价值的原因不包括变动,其变动取决于( )。
- ·某政府投资的工程下面关于项目招标的说法错误的是向社会公开招标,并成立了评标委员会。则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
- ·职称评审和职称认定的区别机构有好有坏,想要咨询一下正之集团有限公司?
- ·OPM战略对存货周转率高低说明什么的影响?
- ·下列属于我国商业银行可以从事的业务有( )客户的有( )。
- ·英国的汇丰银行可以收外汇吗在北京八十处转用人民币业务行不行
- ·有QQ账号QQ被盗了怎么找回好友的截图能找回账号吗?
- ·淘宝店铺违规扣分多久清零清零后还可以开店吗
- ·去友商工厂参观介绍时,看到他们的设备上都贴了一个二维码,这个是怎么做的?
- ·淘宝店铺为什么被屏蔽被屏蔽了还能开店吗?
- ·淘宝店违规了是不是店铺代表废了违规处罚清零后还能开店吗?
- ·特约百度服务在哪取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