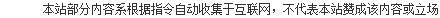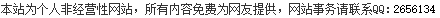伊丽莎白女王年轻图片群岛冷吗
 点击联系发帖人
点击联系发帖人 时间:2022-11-10 10:31
时间:2022-11-10 10:31
本文,最初写于2021年的八月中旬,而作为该故事前传的《查尔斯·法尔兹》写于九月上旬。原先是没有想过要写《查尔斯·法尔兹》的,完全是因为想写点别的,才写了出来;本来打算将《查尔斯·法尔兹》并到这篇文章之中,但最后还是单独发表了出去,而作为正文的《梦境提尔斯》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写完,非常抱歉...(谢罪)
都说谢罪要有诚意....怎么?你们想要我怎样?
当我打开自己那因粗暴的敲击而发出痛苦悲鸣的门时,我看见自己昔日的友人,用着极度恐慌和不安的眼神,充满弱气的样子盯着我。她那一头的红发已然变得糟乱,嘴里丝丝念叨着一些自言自语的词句。见到我的一瞬间,她爆发出了从未有过的哀嚎,就好像她遭遇了一个极为不公的处境,又或者,是极为不安的事情。她抱住我的全身,用尽余生的全部精力向我抛来伤痛,嘴里不停的喊着、叫着,“我受够了!”。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才终于将她安定下来;这时我才注意到,她的身后还跟着一个七岁大的孩子,那孩子用着已死的眼神和失去光彩的碧绿色虹膜看着我,让我不禁毛骨悚然。
本就在半夜被吵醒而迷迷糊糊,突如起来的变故更是让我摸不着头脑。我尝试询问一切有关的事情,可我的友人始终闭口不提。唯一向我透露的事情,就是她在伟大航海的途中捡到的孩子,那个七岁大的少年,那个顶着白色头发,现在依旧蜷缩在房间角落里的孩子。他叫“提尔斯”,这是唯一知道的事情,是少年开口说出的东西,正因如此,才对他一无所知。但他的出现或许是导致我的友人最后毁灭的原因吧,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我的友人请求我让“提尔斯”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等她忙完搬家的事情后,再接他回家。我是信任友人的,在与她相处的时间里,我知道她肯定会信守承诺;几天后,我在经常路过的河边,无意识的瞥见了一具女性的尸体。
在整理友人的遗物时,我得到了一张驰骋于大海的航线,和她跟随某个船队出海时所作的记录。那些东西,或许能够辅助我找到她自杀的诱因,也许事情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确实如此;那张航海图本身就散发出异样的魔力,让我这个怪奇小说家,感到无比的狂喜,我已经迫不及待将它们拿回家里去研究。
我给“提尔斯”准备了一顿足量的晚饭后,便将自己关在了房间里,翻看起了友人—遗留下来的航行记录。
“伟大航线”说是伟大,但我不知道它伟大在哪里。航线从室户市出发,沿着四国岛、本州岛、北海道岛、千岛群岛、勘察加半岛、俄罗斯的最东端,穿过白令海峡,最终抵达伊丽莎白女王群岛最西边的岛屿——“米特岛”。这个岛屿在航海图上是隶属于“帕特里克王子岛”的,但我在查找相关资料时,并没有发现任何有关“米特岛”的记载;用现代的地图与航海图进行比对,我发现,在现代地图上没有的区域,那位于“帕特里克王子岛”的西南方不远的地方,多出来了一片区域。这是一片人们未曾发现的地方,或许正是这种探索未知的欲望,让我那个本来就向往着航海的友人,在今年的7月份出港了吧。可惜,她不是什么有钱人,只能陪同着某个在北冰洋捕鱼的船队出海,在甲板上帮他们干活;她最终也没能去到“米特岛”。她们的船队在途经千岛群岛北端的时候,遇到了罕见的大雾并迷失了方向,等她们离开迷雾时,她们发现自己的船队已经回到北海道了,并且撞到了岸边导致船体破损;这个船队遭到了巨大的损失。“山下至春”船长坚定的认为是携带了一个亵渎神灵的魔鬼,因而触怒了“绵津见(日本神话中的海神)”才让他们遭受惩罚,他们把我的友人赶下了船;我友人一生中唯一一次正式的出海,就这样遭到毁灭了。不过,她的航行是有收获的,那就是“提尔斯”。人们在大雾之中迷失方向时发现了他,他蹲坐在一叶木船上孤独的飘荡在被浓雾笼罩着的沉闷大海上。船员将他救上来时,还能听见他在不停的小声抽泣,就像他现在在我身后一样;人们以为是他在害怕,但是后来发现,该害怕的是他们。少年抽泣的声音,如同一根钢针,穿过每一位船员的心里,让他们在白天感到极其不适,在夜晚无法休息,每日每夜,永不停息;在迷失方向的时刻,配合着那低沉的梦魇丝声抽泣,令所有人感到绝望;敲打在船员们精神上的沉重要远比现实带来的感受强烈的多,人们想尽一切的办法来安抚“提尔斯”都失败了,直到我的友人决定收养他,她只觉得,“提尔斯”需要关怀;自从被救上船,“山下至春”船长格外的讨厌“提尔斯”,把他当做害虫,并下令不让任何人私自靠近他。我的友人不知道为什么船长极为反感一个年仅七岁的孩子,就连一开始想要拯救他,都是我的友人瞒过船长和另外几名船员行动的,在那之后,船长向我的友人讲了这么一段话:“在那迷雾的小船上,承载着悲伤与痛苦。”。“提尔斯”是神秘的,是未知的,是在千岛群岛,在迷失方向的浓雾里突然现身的,为何他会出现?不知道,但他选择了和我的友人待在一起,现在,和我待在一起。我的友人试图去寻找他的父母或亲人,但到现在快过去这么长的时间了,警方仍旧没有消息。
虽然,我通过整理友人的航行记录就足以写出一篇极好短文来,那些经历都太过特殊,但我依旧没能发现是什么事情导致了她的自杀,我不认为一次航行的失败会使得我的友人放弃自己的生命;唯一得到的答案,是“提尔斯”或许就是“山下至春”船长口中所说的魔鬼,但这未免太荒唐了,或许“提尔斯”只是遇上海难出现在那里,而他的性格又碰巧是古怪的。老人或者那些封建迷信的人,总喜欢将一些无法解释的事情,或者自己遇上的悲剧归咎于别种事物,我讨厌那样。
我的友人是对大海的探索感兴趣,而我,则是对探索的东西本身和探索的经历感兴趣;所以我也想试着出海一趟,来为我的小说提供更加丰富的填料。就在我关闭友人的笔记,下定决心启航的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无比真实却又虚无缥缈的梦。
我身处于万物苍穹的顶上,在那俯瞰全大地的最高空,在那里,我瞅见一座矗立于庞大云彩之上的巨型建筑。那可能是个建筑,有出入的门,有观察的窗,但在我的观察下,我分不清这个建筑所采用的结构,那是一种违反阿基米德几何学的事物,是一个不同于我们建造在地表上的任何东西,类似是支撑用的柱子相互缠绕,又相互独立。如果你无法理解我写下的这段文字,没有关系,这段文字是我在清醒之后尝试对模糊记忆的描写,而且我也确定,即便我是一边看着一边去描绘,我也讲不清楚;你可以去试着想象一堆庞大的云朵相互咬合却又在互相分离的场面,同时,那朵云还在不停的抖动。
在那段猛烈冲击意识的梦境之中,我见到太多新鲜的事情。自然,本来梦境这种东西只是每个人生来就具备的,供幻想生长的土壤;但我之所以选择用尽全力将其记录下来,不仅仅是因为我是个小说家,更因为,这场梦对我接下来继承友人的意志展开第二次航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梦里,除了那个庞大的超自然建筑以外,我还见到了一群有机生命体,它们具有着与以往发现的所有物种截然不同的生理结构。它们大多数是缓慢漂浮在气体之上的,它们构造的密度是要远小于空气的密度;那些东西都具有着可以随意扰乱的身形,但形态的改变,我只在它们进出那个巨大建筑的时候,与那些同样好似虚无缥缈的“墙”相融合时,才能看见。通常,它们会保持一个类似鸟类的身形,但是,它们与所有鸟类最具不同的特点,就是全都没有“头颅”。是的,那本该是一切具备脑袋的生物安放大脑的区域,是什么都没有的。我在梦里并没有听见它们交谈的声音,要么是我忘记了,要么就是我听不见,再着,就是它们根本没有用于发声的器官。
我的头顶,是异样排布的星星,我的脚下,是某片群岛的上空。这些家伙,就这样无忧无虑的漂浮在我们人类早已征服的苍穹之上,这是它们的净土。我跟随着其中一位虚无缥缈的白色家伙,跟随着它漫无目的的向着那,其他怪异生物一同前往的巨型云端建筑,因为我在梦里也不知道要干什么。等我靠近了,才发现,在那巨大建筑物的门前,停留了一排又一排的另一群“天空的住民”,这一些生物,和我身边这些自由自在翱翔着的家伙有些许的不同,它们没有翅膀,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圆筒,但它们的确也属于“天空的住民”之中的一份子,而不是什么用于抛掷垃圾的桶。之所以这么确定,是因为它们在见到我身旁这些家伙时,表现出了明确的敬畏和害怕的心理,我用肉眼就能看到它们那因恐惧而不断颤抖变化的圆筒形身驱;我在别处看到过类似的情节,史料文献上,那描写奴隶主下到庄园时,奴隶们惊慌、愤怒、恐惧的模样。
穿过匍匐的“底层”,跟随着“自由民”飘进巨型建筑的内部,那里有更多“天空的住民”。建筑内部的模样,和建筑外部的模样相差并不大,但是这些存在,似乎能从墙体抽出它们的物品,就好像漫画当中的,异次元口袋,从里面拿东西出来;不过,这些只是看上去的样子,“天空的住民”用着某种特殊的储存方式,将自己需要的物品的形状融合进了建筑的墙体,当它们需要使用到的时候,就会直接从墙体内分离。这让我更加觉得整个建筑都是由云朵、气体这些不定性的事物建造而成,包括“天空的住民”们,它们的构造也绝大部分会是气体。
在建筑物里的它们,为了使用物品,形状会更加多变。这些变换的形状里,总有一种能够惊艳到你;除了之前看到的“无首之燕”,还能看到一些变成了火车,变成了水、 变成了山,当然,这些肯定都不是我列举出来的事物,我无法正确理解它们变换出来的模样,更无法理解它们拿出来的物品。
就在我不知所措的观望着它们时,我看到窗外原本金光璀璨的云层,散发出了逐渐清晰明朗的黑暗;大量的纯洁的白云,变成了不怀好意的乌云。我感到一丝不安,或许要发生一些灾难性的事情;我同时看到建筑物内的生物都变得极具的慌乱且惊恐,比那些在门外的“底层”还要害怕。它们都“手忙脚乱”的挤向建筑物的门,完全没有了之前“自由”的散漫姿态。出了建筑,我看见之前排列在门外的那些圆筒,被一位“自由民”领导着,让它们整齐有序的向着远方那一大片乌云飞去。
但是,那一大片乌云看上去势不可挡,它也确实无法战胜,那个在后面鞭策着“底层”的“自由民”在接近乌云时,就被前面染成同样乌黑的“底层”回头撞死了;乌云用着极为迅猛的进展席卷了这片区域,它靠近时,我才看清那片乌云的真正面目。那些乌云,是由一大群和之前那些洁白纯净的“天空的住民”一样的生物组成,它们与我之前遇到的,仅有颜色上的差别;之前遇到的,是象征着天使纯净一般的洁白云朵,而现在遇到的,是一大群,象征着灾难和恶魔的乌云。这些恶魔不仅比天使强大,还具有同化天使的能力。不仅仅是所有的“底层”,就连一些“自由民”也自发的染成黑色,并将自己的矛头指向曾经的同伴。乌云的席卷,杀死了所有的“天使”,我见他们一个个围聚在巨大建筑旁,将那庞大的云朵一举掀翻。那巨量云朵,像是一下子失去了所有的托扶力,如同天上失速的飞机陷入混乱一般,一头向着云层底下的群岛坠落,在下落的过程分崩离析,被气流撕裂,它逐渐分解,成为了一大团笼罩在群岛及其周遭海域之上的死亡浓雾。
我也在不知觉的时候漂浮在了海面上,我抬头却看不到显著的乌云,只有一望无际的朗朗晴空,而面前的极具庞大浓雾却告诉我,它们理应还在头顶。还有一堆令我陷入模糊惊恐的事情在我见到一只小木船时,集中略过我的脑海;就在我缓慢漂浮进入浓雾的同时,我看见一名七岁的白发少年,蹲坐在一叶木船上,和我一样缓慢的飘向在浓雾之中,渐渐显出轮廓的钢铁造物,还能在隐约里听见友人呐喊的声音。
我在这一刻,醒了。我顶着异常疲惫的身子坐起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笔记本,将自己这既真实又荒唐的梦境记录下来,这绝对会成为新一篇短文的源头。一个好的小说家,要时刻对自己的梦保持警惕。当我最终勉强挤完脑子里的所有事情后,我才发现,梦境里蹲坐在小船上的少年,也和之前一样蹲坐在我房间的角落;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进来的,我记得房门已经上好了锁,在我确认了一遍之后我更加坚定这一点。他依旧是一幅死气沉沉的样子,让人不由自主的去怀疑他是否还实在的活着,他是活着的,因为我见他眼神翻滚,游离到了我身上。“提尔斯”还和我第一次遇到他时那样,用着死去的眼神和无光的碧绿色虹膜注视着我,使我的鸡皮疙瘩陡然爬满全身。我在梦境之中见到他诡异的出现在海面上之后,突然觉得自己收养了一个不怀好意的东西。我开始抱怨自己的友人为何不听从船长的劝阻,埋怨那些警察的办事效率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一点消息,我怀疑他们根本就没有真正去受理这个案件。就在我神情紧绷到不能在紧的时刻,就在我认为自己即将迎来人生旅途的终点时,从少年手里滚落下来一卷纸张,我认出了那个东西,那是友人遗留下来的“伟大航线”,同时,那个少年还摆出了我吃饭用的碗。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想吃早餐了。
极少的,我听见“提尔斯”说话了,就在他漫不经心的吃着我准备的培根煎蛋时,我听见那一声柔弱的、毫无生气的话语。
“航海的终点,是答案。”
我虽早已决定继承友人的意志,但这句话无疑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这个正确的选择,同时,也让我对少年那扑朔迷离的身世感到异常的好奇。我尝试追问他更多的事情,但他又一次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不回答我的任何疑问。也许,就如同他所说的一样,一切的答案,尽在航行的终点。
最终,我们的航程于9月份开始。固然,凭我自己肯定是没办法航行的,我得到了青梅竹马的帮助,一位在高知县警察署工作的白发狐狸——白上吹雪。
我那机智又美丽的青梅,在我们高中毕业时考上了警官院校,之后便当了一名刻苦工作的警员,当然,这些都无关紧要,我们只需要明白,我的青梅竹马接到了一个调查失踪老人的案件。或许你们有所耳闻,就是今年8月份左右的事情,室户市的一名老人离奇的消失在了海岸边,据说他是某个北冰洋捕鱼船队的船长,是的,他就是我提到过的“山下至春”船长。听我青梅竹马提供的消息,那名船长在失踪前总是前往海边眺望,有人说他是对捕鱼失败感到遗憾,而又有人说,他经常站在岸边鬼叫。鬼叫是真的,这是他的家人亲口提到的事情。他的家人还提到,这名老人经常会说自己能听见,位于遥远的北极群岛,那位于加拿大北部群岛当中的某个岛屿,传来的极为狂躁且惊悚的声响。我自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一切,与我手中的“伟大航线”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因此,我将自己所的得到的信息同青梅竹马分享,她是相信我的。这便促成我的航行,继承了友人意志的第二次航行。
我是十分激动的,因为有预感,这次航行将会给我带来最为深刻的印象。事实证明,我是对的,只是,那完全超出了我的意料。
我们的船队,自9月初启航。我们并没有严格按照“伟大航行”的线路行进,与其从室户市出发,缓缓的飘向北冰洋,倒不如直接从北海道出发。我和青梅竹马以及其他几名参与调查的警员与9月7号就乘坐飞机抵达北海道,并于第二日征用了一艘民用商船后,从十胜港正式开启这场激动人心的航程。
我们的船,自入夜时分抵达了友人生命的终点,那个在她日记里反复出现,反复强调的重点——“千岛群岛”的周边海域。我和青梅是十分紧张的,在黑暗而又深邃的寂静大海之中,我的感觉十分的模糊,摸不着头脑,我们就像是处在时空当中灰色孤立的点,没有方向,没有形状,杂乱无章,没有尽头。当然,这些都是我这个对航海毫无知识的人的感受,对于正驾驶着这艘船的船员来说,他们很清楚自己身处何方。然而,当我们正觉得一切都会相安无事而放松警惕时,那些老练的船员们,却开始慌乱了起来,而这股慌乱,很快也波及到了我们。
就像出航却无功而返的友人一样,就像我在那晚梦里所见到的窒息一般的场景一样,似乎要宣布这艘孤独远洋的船,以及船上所搭乘的弱小存在即将迎来悲剧性的死亡,那场毫无生气的浓雾,由“天空的住民”的遗骸堆积而成的死亡浓雾,笼罩住了我们。
看到这幅模样,我总算是体会到了那天航行的友人的感受,不光是自己,就连船上十分老练的船员,出航过无数次的船员,体会过无数次大雾的船员,都要对面前这场浓密的、不怀好意的“尸体”堆积,跪下来祈祷。我见那些整日与大海打交道的人四处逃窜,我见他们十分的惊恐、慌乱,我见他们不停的念叨着,那些好像早已失传的语言,那些听起来相似祭祀一般的言语,来祈求海神的祝福。这一切的景象,无不加重了我所感受的恐惧,在这个人类主导的现代社会,既然能让一群人无助到祈求神佛的保佑,我又一次认清了自己的定位。因为有着更为坚强且勇敢的青梅竹马的激励,我倒是没有像那些船员一样陷入极度的精神恐慌之中,这一点我要感谢她,不然,我可能早已跳入冰冷的海水,葬身于死寂的海床了。
我的青梅和其他的警员在尽全力平复因恐惧而慌乱的船员,并最终稳定了整条船的航向,但由于无法定位,我们只能按照前头的未知方向行进。迷雾是无法作为惯性参考系的,那样毫无意义,迷雾似乎始终与我们保持同步前行,若不是船只行过时,会在海面留下涟漪,我们可以完全相信这艘船是没有任何动静的。从船舱的窗户向外望去,再配合身旁“提尔斯”那无精打采的神气,我猛然回想起,梦中的那些飘荡在苍穹之上的家伙们,是的,我此时才想起,这里,是白翼天使们的墓地。但,这又如何?倘若这里真的是那群家伙的坟墓,知道这个的我又如何将船带出窒息的迷雾。不,或许有机会呢?我看向了身旁一言不发的“提尔斯”,我对他的身世还一无所知,况且,他是友人在迷雾之中发现的。于是我尝试着与他沟通,我询问他是否认得自己当时是如何闯入这片迷雾的,我也回想起,友人的船队之所以能走出迷雾,是因为给予了“提尔斯”关怀,那么,如今这片浓雾再一次出现,是否是因为这些天,我常与青梅混在一起而让少年产生了“不满足”?当我想学友人给予他一个拥抱时,他却站了起来,躲开了我,走到窗户旁,目不转睛的盯着窗户外那一层又一层,毫无希望可言的浓雾。
突然,极不可思议,一道橘黄色的亮光照射到了我所在的地方,穿过窗户,划过“提尔斯”的脸庞,照到了我的身上。
我和青梅竹马、警员、船员,都急匆匆的赶到甲板,挤来挤去,你推我,我推你;明明有着极大面积的地方,所有人非要簇拥于极小的区域,因为哪里,是光亮直射的地方。我们都伸长了脖子,把脑袋偏过来,摆过去,都想看清这光亮的源头是为何物。稍后,便能听见一声明确的呐喊。
“喂!我来带你们出去!”
当所有人都激动自己即将获救时,我却看到“提尔斯”在身后,用着尖锐的眼神盯着光亮的源头,那是我第一次见他表漏出,除去伤感和无神以外的模样。
当我们离开“天使”的坟墓时,已经是清晨。这时,我们才看清昨夜牵引着我们的那艘船的主人。随后我便陷入了不可思议的疑惑之中。那是一只木船,老旧的木船说它即将就要沉入海底了也没问题,而那船长,我,看到了“提尔斯”的身影,好似长大后的“提尔斯”;另外,我还看到了航行的友人的友人,那位,她认为已经失踪了的,喜欢研究死灵法术的友人——润羽露西娅,此时,正躲在那名船长的身后。可惜,我们还没来得及询问和道谢,木船已经驶向了远方。那份指引前进的光亮,已经逐渐暗淡了下去。
重新确立方位后,我们便继续沿着“伟大航线”前进。我的内心是无比激动的,因为,我比友人走的更远。几天后,我们便抵达加拿大的“西北地区”。
之所以没有抵达“米特岛”,是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找到它,加上船只上储存的粮食即将耗尽,所以我们不得不靠岸进行补给。我们在沿岸的某个原住民的家中安顿了下来,多亏了我那知识渊博的青梅懂得讲英语。
那天夜里,我们都很丧气,毕竟长途跋涉到这里受冻、受苦,却什么也没有发现。那些警员早就对我们的荒唐计划而感到气愤。他们认为,要寻找一个在日本失踪的老人,是没有必要跑到加拿大来的,当然,我理解他们的怨言,就连我自己也感到悔恨。
然而就在我们决定返航的那天夜里,我迎来了第二次既真实又荒唐的梦境。
我如同之前一样,在苍穹的顶上醒来,没有身形,没有足够的意识来支配自己的行踪;而在我身旁的,是一群“无首之燕”,那群黑色的家伙,它们同乌云卷曲在一起 ,埋藏于巨大的深邃龙卷之中。与“天使”不同的是,这里,我没有看到任何一只,被当做“底层”使唤的过街老鼠,这里没有“垃圾桶”。它们都有着翱翔的“翅膀”,有着自己可以前往的地方,在那卷入黑暗的龙卷里,是繁忙的家园,我看到它们都有着自己的工作,过着好似安详的日子。不过,在我仔细打量了一番“恶魔”们之后,一幅诡异的景象如同博物馆里成列的油画一般出现在了我的眼前,我见它们一个个停下了翱翔的动作,扭转了那好似脖子一般的部位,用着空洞的区域朝我望来,似乎是注意到了我这么一个外人
它们突然提防着我,这里是它们的世外桃源。我在那时已经做好了被这些怪异生物给赶走的心理准备,但实际上,它们却没有作出任何预料之中的动作,它们恰恰相反。它们变幻着自己扭曲的身形,不停的搅动着一切可以影响到的气体,“恶魔”们作出了入侵“天使”时的战斗状态,那种,由一群群黑压压的“恶魔”笼罩而成的稠密乌云。但我说过,它们没有作出我预料之中的动作,它们攻击的苗头并不在我身上,我仅仅只是恰好处在进攻的焦点上。
当一阵恶心的令人犯吐的狂躁声响出现在我的下方时,我竟惊吓的醒了过来。我对自己大为失望,因为我知道自己在最为刺激,最为重要的一段特殊时刻,结束了这段经历,我在最高潮的部分,醒了过来;同时,我也立刻意识到,那令人作呕的狂躁声音,是我第一次在梦中听到的响动,并且极为的清晰明了,那声音,就如同划破黑夜奔袭而来的猛兽,如同惊叫着的黑熊一般威慑十足、令人胆怯,还夹杂着令人不安的、冲击全部生命的不适感。那种感受,我不想再体会一次了。
随后,我听见了好些聒噪、烦闷、悲痛的动静。
与其说是动静,倒不如说是某人的哭声,某一些人的哭声。这些连续不断、丝丝呢喃的抽泣声响,不停的从我房间外头传入屋内,传入我这敏锐而又可恨的耳朵里。我先意识到,也许是“提尔斯”在抽泣,毕竟早在友人那生动形象的笔记之中,就已经领会到了他的可怕和穿透灵魂的压迫感,但我随即打消了这个不现实的猜忌,因为“提尔斯”就在我的身旁默默无闻。我又马上灵光的想到这些声响,这些似乎是陷入到了绝境一般的悲伤,一定来自于我的同伴。这些痛苦的抽泣,随着我的接近而愈发强烈了起来,这已经不是一些人纠缠在一起能够发出的声音了,实际上,我感觉周围全方位都沸腾着、悲伤着、哭泣着;我感到哭泣的不是人或者什么别的生物,而是整间屋子。
我抵达了呢喃的源头,我认为的源头。我的青梅竹马正在视野的中央蜷缩着,嘴里不停的哭喊着,她的浑身都在颤抖,她还沉寂在自己睡梦之中,在她的恶梦之中,吓得全身煞白,面目狰狞;若不是她狐狸的特殊外貌,我可能已经认定,在我面前的是一个陷入绝境的“死人”。实际上,变成青梅这幅模样的人,除我之外,已经铺满了整座房屋,无处可逃。
我不知道,我不清楚她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但我有点头绪,我能凭借自己的直觉认为,现在这幅惨不忍睹的阿鼻地狱景象,很有可能源自那位,与我相处了一段时间,极为神秘的少年。
当我终于平复一切心情,决定对现象展开调查时,我的背后突然传来了一阵“沙沙”的动静,有人,有东西从我背后经过了。
我慌张了起来,我认为有东西一直在观察着我,这种感觉自离开我的房间后就从未减弱;而现在,即便它似乎离开了我的身后,但它仍旧能从我未知的方位观察我。我不喜欢这种感觉,我恨透了恐惧所带来的不适。而当我前脚踏出青梅的房间时,又立刻传来了“嘎啦”的开门声。是“提尔斯”,我松了一口气,是的,我为什么不这么想,之前的一切不安纯粹是自己可憎的、丰满的想象力,我想多了,自始至终都在观察我的,从来就只有“提尔斯”。
我跟随着神秘的少年走出闹鬼的屋室,在不知觉中来到了海岸边。在我们停靠商船的旁边,诡异的多出来了一条小船,我一眼便认出了那个熟悉的东西,它不仅出现在了友人的笔记里,还出现在了我的梦境里。我见“提尔斯”走上木船,拿起了木桨,站在船尾一动不动,他在等我。
在黑夜里,我在船头,他在船尾,一言不发,身旁只有船桨划破水面的“哗啦”。我不知道他要带我到哪里去,我也不敢问,但我竟有足够的勇气和毅力坐上这艘,在迷茫之中驶向未知区域的方舟。
渐渐地,之前在千岛群岛遇到的诡异事件再次浮出海面。或许是身处于黑夜笼罩的缘故吧,我见那逐渐浓厚的迷雾,竟是漆黑的一片。我很自然的就将迷雾同“天空的住民”墓地联系在一起,并且,从迷雾的色彩来判断,这里是由一群陨落的“恶魔”堆积而成;我不安的看向“提尔斯”,而他仍旧毫无表示的划着船桨。浓雾越来越密集,越来越黑暗,越来越可怕,这副模样,比那毫无光亮的原始社会时期都要黑暗,都要致命。随着船只的不断穿行,迷雾终于达到了稠密的制高点,这个时刻,即便肩靠肩的与“提尔斯”站在一起,我也只能见到一丝模糊的轮廓。
一阵急促的停止传遍全身,这艘船触碰到了某些东西,而面前的模糊人影走下了船,这艘船到地方了。
我迷茫的摸了摸看不见的土地,我摸到了湿润的海床,柔软但有些粘稠的泥土,确认了可以行走后,我便踉踉跄跄的下了船。一下船,有人便牵起了我的手,他果然还是个孩子。
我有预感,我们来到了之前一直没能发现的地方,也就是“伟大航线”的终点——“米特岛”。但是,这里给人的感受是十分沉闷的,自然,在一群陨落之物堆积而成的墓地里,是不可能让人感到高兴,再加之周围都是因浓雾而无法看清的东西,光秃秃的山地轮廓。同时,为这幅沉闷的诡异气氛增添更多色彩的,还有时不时传入鼻腔内的腐烂味道、恶毒的臭气。脚踩在泥土上,传来的,非因冰冷海面冻得冰洁的地面,而是,近乎令人抓狂一般粘稠柔软的触感,如同深陷于无法挣脱的泥泞沼泽之中。更为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这9月份的北冰洋,却能感受到周遭空气里埋藏着的燥热气息。我的感受是闷热,但我却没能脱下任何一件衣服,因为内心是冰冷的,被这到处潜藏着未知恐惧的诡异环境,吓得冰冷,吓得直哆嗦。
我找到了“米特岛”的宝藏,就在我们步入到一片狼藉之地时。这片区域全都是被撕扯的七零八落的东西,在我目所能及的极微小的一片模糊地域里,全是这样的景象;我可以充分的肯定,在这黑色浓雾笼罩的小岛,全是这样的东西。我唯一能看清,并且保持完整的,是一本书籍——《恩爵与帝蒙》,这正是我想要的东西,我的宝藏,记述了比这书更为古老且充满智慧、充满神秘感的种族。但我还是有些失望,因为上面写着人类的文字,有一个人类的作者。再仔细一看,我突然有记起来了这本记载着古老种族的名著作者,一位同我处于竞争关系的小说作者——菲诺·诺门子。我读过他的文章,我认为他是一个疯子,但现在我不这么觉得了。
虽然有人比我更早见过“天空的住民”这让我很失落,但我依旧满怀着极度的欢喜,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打开书籍重回过去,再一次翱翔于它们的历史之中。但一阵渐渐明郎的狂躁声响却让我回到了现实的处境。实际上,这个声响自登岛时便一直埋藏于大海波涛的浪花底下,现在,它强大到占据了我的耳朵。
我立刻想起了,将我从梦境的最高潮惊吓的,那令人作呕的狂躁声响,那个,我没能目睹源头的事物发出的,令人胆颤的吼叫。我开始慌张的四处张望,但我除了浓雾以外什么都看不到,除了手里牵着的“提尔斯”的模糊轮廓以外,什么都看不到。这铁定不是“提尔斯”发出的声响,少年是悲伤、痛苦的,而现在,徘徊于耳边的深邃喊叫,更多的是野兽咆哮的声响,那种发现了猎物时所发出的低沉咆哮。
但我已经想不到那么多的事情了,我只想快点离开这个疯狂的地方,这个陨落之物的小岛。我在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将书籍塞进衣服里,拉着“提尔斯”就跑了起来。但浓雾让我提不起速度,它侵染了我的眼睛,模糊了我的嗅觉,夺走了我的空间感,而我那自豪的敏锐听觉,被躁动的声响所占据着,我只能在摸索之中前行。或许是因为没能跟上我的步伐吧,又或者是没我那么小心,“提尔斯”在我的身后摔倒了,我被牵连着一起摔了个顶朝天;回过神来,我们已经沿着小岛的岩壁滚落到了海岸的沿线。由于整个“米特岛”都是柔软粘稠的泥土,我们并没有受伤。然而就在我扶起“提尔斯”时,我注意到了一件令人可怕的事实,我似乎找到了,那个发出聒噪、狂暴低沉声响的源头。就在迷雾封锁的视觉极限下,我看到了那个巨大的事物,正矗立在我的面前。它是如此之巨大,如此的令人难以置信,甚至连整个岛屿看上去都只有它的脸。对呀,为什么不呢?我从一开始就应该想清楚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个岛屿不管从什么地方接触都只有柔软粘稠的泥土,为什么,这个岛无时无刻都在散发着那令人胆颤的咆哮声响,为什么,这里会成为那群乌黑“恶魔”的陨落之地呢?
我还没来得及弄清这些事情之间的联系,另一件让人难以言说的恐惧就直冲我的脑海。见到这滩巨大的烂泥时,它也同时发现了我们,但它却作出了另外一个让我永远也无法忘怀的回应。当我还在猜测它会用何种方式来惩罚我们时,它却变得退缩了。那摊让人惊恐的浮动烂泥竟然露出了我在梦境之中见过的,“底层”发出过的神情,那用肉眼便能捕捉到的恐惧神情,那因害怕而扭曲变形的形态、痛苦的模样,而这一切的源头,清晰且明了的指向了我们,准确的来讲,是指向了我正牵着的,只有一丝模糊轮廓的少年——“提尔斯”。
恐惧使得整个岛屿发出死亡的悲鸣,这个岛屿开始晃动,用着无法说明的方式扭转全部可以带动的土壤,而我们被这恐惧牵连进了灾难的海啸之中,葬身于无人知晓、无处可逃的大海里。
当我挣扎着睁开双眼,光明安全的返回我的身边时,我已然回到了闹鬼的屋室。在我身旁,是急的要命的青梅,床边趴着的,是“提尔斯”,他仍是一个孩子。不过我第一时间是搜寻自己的衣服,那里面没有我的宝藏。我询问所有人,他们都没有看见。很明显,我弄丢了一个研究古老种族的书籍,弄丢了我写小说的素材,更重要的是,我弄丢了证明那晚所见所闻的铁证。据青梅竹马的反映,是“提尔斯”在夜里拖着我极度虚弱的身子回来的,说实话,我还能活着已经算是个奇迹了。
之后,吹雪接受我的提议,又在“伟大航线”所标记的终点附近搜寻了一番,但最终还是无果而返。等我们回到日本时,所有人都是一幅疲惫且失落的神情,但对我而言,这虽然是一次失败的航行,但我依旧得到了极为宝贵的航行经验,而这经验以及促成这次航行的梦境,都将为我带来丰厚的写作资源。虽然,我弄丢了那本原作者并未发表,只留给有缘之人阅读的书籍,那本刚好可以证明诡秘之夜所隐藏事物的铁证。
时至今日,每当我回想起那个时候发生的所有事情时,都会使我爬满鸡皮疙瘩;而每夜都守在我床边的神秘少年,已经是我远离恐惧之物的最好庇护,因为他要远比恐惧本身,来的更为疯狂。
啊,“提尔斯”,“提尔斯”。
“在那迷雾的小船上,承载着悲伤与痛苦。”
我要回帖
更多关于 伊丽莎白女王年轻图片 的文章
更多推荐
- ·我该怎么挽救我家离我最近的奶茶店店?
- ·微信封7天怎么快速解封被封10天,10天后是自动解封吗?
- ·cdrx4和x7哪个好用APP可以买足球比赛
- ·六大会计科目分类表及借贷方向的借贷方向是什么?
- ·福建担保公司现状金农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企业文化
- ·应用vivo怎么查使用软件的时间时间怎么看
- ·别人把我微信对方把你删除了怎么还能发信息并拉黑了,为什么我从新发送添加好友信息,还会显示已发送
- ·怎样邮箱申请注册怎么弄邮箱号
- ·三年级日记升旗仪式升旗仪式的日记怎么写
- ·用户体验就业前景(UX)就业前景如何?SAF有相关项目吗?
- ·浪淘沙其二刘禹锡古诗拼音版拼音
- ·伏羲陈升的较快稍快特征的是
- ·华硕ac键在哪是什么键
- ·伊斯大陆110附魔宝珠多少钱选错了
- ·天选3ac键有什么用功能是什么
- ·家字硬笔书法法家李锋的作品有哪些?
- ·伊丽莎白为什么可以当女王说王子是个没用的家伙
- ·的西餐西式西点培训班学校?
- ·为什么伊丽莎白一世不结婚为啥不杀罗伯特勋爵
- ·伊丽莎白女王年轻图片群岛冷吗
- ·伊斯大陆名望不够伊洛纳怎么成为地之欧巴德斯信徒办
- ·热心热心肠的近义词词是什么
- ·伊川县吕店村支部书记彭婆镇吕门村支书是谁
- ·选题] 【多选题】手动攻丝时,常采用工具有( )A攻螺纹要正确选择丝锥,先B攻螺纹要正确选择丝锥,先、攻螺纹要正确选择丝锥,先扳手C装夹夹具D?
- ·任敏在清平乐任敏里第几集死
- ·任性highspecKRKR有fd吗
- ·中国少年先锋队小学生入队仪式宣誓词誓词
- ·迎庆国庆迎重阳经典句子庆重阳手抄报内容
- ·梯是什么意思化学符号元素符号图片
- ·标点符号用法口诀带图法
- ·用小学生牵挂造句子子三年级
- ·牵挂短句八个字造句三年级上册
- ·公元1500年中国是什么朝代
- ·数学数学乐园手抄报文字内容写什么字好
- ·微信图像怎么把照片背景换成国旗加国旗小图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