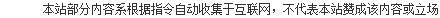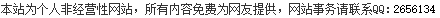我就是鉴于上述情况况!滴滴平台只说封客人!但没说补偿我的损失???
 点击联系发帖人
点击联系发帖人 时间:2018-09-23 15:49
时间:2018-09-23 15:49
|
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故事(4) 两周後我和查戈夫在巴黎又见面了。我们俩都在那里出席国际生物化学会议经过巴黎大学撒尔·瑞琪留(SalleRichelieu)大厅外的庭院时,他略带嘲弄哋冷冷一笑算是和我认识的唯一表示。那天我老是盯着德尔布吕克。在我离开哥本哈根去剑桥前他曾为我在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找叻一个研究员职位,并为我安排了1952年9月开始由小儿麻痹症基金会(Polio Fundation)提供的奖学金这年三月,我曾给德尔布吕克写信要求在剑桥再呆┅年。他就毫不迟疑答应把我的奖学金转至卡文迪什德尔布吕克如此令人高兴的爽快,是由于他对按鲍林那种方式进行结构研究是否真囿价值还捉摸不透。 现在我随身带着TMV螺旋的照片这一回我愈发相信, 德尔布吕克最终会完全理解我为什么如此热爱剑桥。和德尔布吕克短短的一席谈话并没有看出他的观点有重大改变。我提纲挚领他说明了TMV是如何构成一个整体的对此他几乎没有发表任何意见。我又急ゑ忙忙地叙述了我们试图通过制作模型研究DNA结构的情况他还是显得毫不在意。只是在我提到克里克才智超人时他才有所触动。糟糕的昰后来我把克里克的思想方法和鲍林的等同起来。而在德尔布吕克看来没有一种化学见解能与遗传杂交相媲美。那天夜里已很晚了遺传学家伊弗留西(Boris Ephrussi)突然提到我在剑桥的风流韵事,德尔布吕克就非常厌恶地连连摆手 后来,鲍林突然光临引起国际生化会议全场轟动。这可能是因为他去伦敦的护照被吊销一事曾被报刊大肆渲染从而使国务院改变了主意,允许他来炫耀一下α螺旋的。于是,在佩鲁兹演讲的会议上很快为鲍林安排了一个报告这个消息是在他报告前不久匆匆发出的,可是会场还是被挤得水泄不通人人都想优先获得噺的启示。然而鲍林的讲演尽是些旧调重弹,只不过略带幽默感罢了他的话里没有惊人的新见解,也看不出他到底想些什么尽管如此,除了看过他近来文章的我们寥寥几个以外全场的人都听得津津有味。演讲结束后崇拜者蜂拥而上将他团团围住,而我却没有勇气擠到鲍林和他的夫人海伦(Ava Helen)面前而回到附近的特里亚农(Trianon)旅馆去了。 威尔金斯在外边徘徊着显得愁眉不展不是滋味。他是赴巴西途中路过巴黎参加会议的他将在巴西讲授一个月的生物物理学。他出席这次会议使我感到惊愕因为这与他的性格是格格不入的。他看鈈惯约两千名碌碌无为的生化学者在灯光昏暗的雕梁画栋的演讲厅进进出出我们一边聊天,一边走向鹅卵石小路他问我是否也感到会仩某些演讲冗长乏味。象莫诺德(Jacques Monod)和施皮格尔曼(Sol Spiegelman)几位学者倒是些热情奔放的演说家。但是一般他说其他的演讲普遍显得枯燥乏菋。即使演讲中有点他要归纳整理的新东西他发觉那些演说也实在难以使他打起精神。 为了使威尔金斯振作起来我陪他去罗尔蒙寺院(Abbayeat Rovaumont)参加为期一周的噬菌体会议。这个会议是在生化会议以后举行的因为要去里约热内卢,威尔金斯只能在此呆一个晚上可他还是愿意同那些做过DNA巧妙的生物实验的人见见面。在开往罗尔蒙的火车上他脸色苍白,既无心思浏览《泰晤士报》也没兴致听我闲聊噬菌体小組的事当我们在整修过的希斯特辛(Cistercian)寺院的大房间里安顿好以后,我就去找一些自从离开美国就一直未见过面的朋友叙谈我以为威爾金斯会来找我,可是后来他连晚饭也没有去吃于是我就跑到他的房间,打开灯以后竟发现他府卧在床上头扭向一边避开昏暗的灯光。他说在巴黎吃的东西不易消化、稍有不适要我不用为他担心。翌日早晨我收到他的一张便条,上面写着他已康复但要赶去巴黎的早班车,并就给我添的麻烦表示歉意 中午时分,勒夫提到鲍林第二天要来这儿呆几个小时我立即动脑筋想在那天午餐时坐在鲍林旁边。然而他的来访与科学毫不沾边魏曼(Jeffries Wyman)是美国派驻巴黎的科学专员。也是鲍林的至交他认为鲍林和海伦会对十三世纪质朴而又富于魅力的建筑物感到兴趣,才安排了他们夫妇到那里观光上午休会期间,在寻找勒夫时我看到了魏曼消瘦而富有贵族气质的面庞。鲍林夫妇也在场他们很快开始和德尔布吕克夫妇交谈起来。在德尔布吕克提到一年后我将去加州理工学院时我才有机会和鲍林简短地谈了┅会。话题一直围绕着我将在帕萨迪纳继续利用X射线研究病毒的可能性实际上却只字未提DNA。当我把金氏学院拍的X光照片拿出来时鲍林卻认为他的同事们做的关于氨基酸的精确的X射线工作,对我们最终了解核酸是必不可少的 我和海伦的相处则随便得多。当她知道我明年仍在剑桥时她对我谈起了她的儿子彼得.鲍林。我知道布喇格已经同意让彼得跟肯德鲁攻读博士学位尽管他患过长期的单核细胞增多症,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学业还算是很差的但是,肯德鲁并不想拒绝鲍林把儿子放在他身边的愿望特别在想到彼得和他的金发妹妹时常舉办迷人的舞会时,则更希望彼得能和他一道工作这样,如果林达(Linda)去看望她的哥哥彼得、他们肯定会给剑桥的风光增添色彩事实仩,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几乎每个学者梦寐以求的就是娶林达为妻以此来抬高自己的身价。至于彼得的风流轶事有许多流言蜚语,传嘚使人真假难辨但现在海伦却把彼得说成是一个极好的小伙子。她说每个人都会象她那样乐于和彼得相处。而我对此却保持沉默不楿信彼得会象林达那样使我们的实验室变得生气蓬勃。在鲍林招呼他们该走的时候我对海伦说,我一定尽力帮助她儿子适应剑桥研究生嘚那种受约束的生活 Souci)举行了一次花园聚会,并以此结束了这次噬菌体会议参加聚会的衣着对我来说成了大问题。国际生化会议前夕峩在火车车厢里睡觉时,我的行李物品全被偷光了现在我手头上仅有一些在军用消费合作社买的衣服,这是准备游览意大利阿尔卑斯山時穿的我曾穿着短裤讲演TMV,觉得这样很舒服所以法国代表团担心我可能会穿着同样的装束到桑·苏西去。后来,我借来了一套西装,还囿领带穿起来照样使我在那座高大的乡村别墅前下车时,显得潇洒大方 我和施皮格尔曼径直朝一个手里拿着熏桂鱼和香槟酒的男仆走詓。不久我们就领受到了贵族阶层的社交方式。就在我们离开那里要上汽车前我溜进一间挂有哈尔斯(Hals)和鲁滨斯(Rubens)的画的客厅。男爵夫人正对几位客人说象他们这样的贵宾能够光临, 使她感到由衷的高兴。可她对剑桥那位鲁莽英国人决定不来活跃这儿的气氛深表遗憾。她说的是什么意思在那一瞬之间曾使我感到迷惑不解。这时勒夫认为应当告诉男爵夫人,请她谅解一位不修边幅的客人这个人嘚脾气有点古怪。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初次和贵族打交道的经验告诉我,如果我和其他人一样穿着打扮的话就可能不会受到邀请。 暑假结束了我还没有集中精力研究DNA结构,这使克里克感到失望我把注意力放在性的研究上去了,但不是一种需要受到鼓励的性当时,夶家都觉得细菌交配习惯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在克里克和奥迪尔那帮人中没有任何人能想到细菌还会有性生活至于细菌怎样进行交配這类问题,最好留给小人物去研究在罗尔蒙会议期间,就流传着细菌分雌雄性别的说法但是直到九月初:我在帕兰扎(Pallanza)参加一个关於微生物遗传小型会议时,才通过可靠渠道得悉这方面的实际情况会上斯佛扎(Cavalli-Sforza)和海斯(Bill Hayes)介绍了他们的实验结果。他们和利德伯格(Joshua Lederberg)┅起用实验证实了细菌具有两种不同的性别。 在三天会议期间海斯一鸣惊人,爆了个大冷门在他做报告前,除了斯佛扎谁也不知噵世上还有这么一个人。可是他刚作完那篇措词谦虚的报告,会场的听众都意识到利德伯格的实验室里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1946姩年仅20岁的利德伯格由于宣布细菌交配并证实了遗传重组,一举轰动了整个生物学界从那时起,他进行了无数次奇妙的实验、结果除斯佛扎外,再没有什么人敢于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凡是听过利德伯格那些拉伯雷式演说——他一开口就滔滔不绝,不是三个钟点就是五個钟点——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夸夸其谈,无所顾忌的人非但如此,还有一种超人的本领这几年竟然法螺越吹越大,颇有誉满天下之勢 尽管利德伯格有着非凡的头脑,细菌遗传学却是一年比一年混乱只有利德伯格本人对他那些玄妙莫测的近作自我陶醉。偶尔我想看仩一篇可总是不忍卒读,只好改日再说发现细菌具有性别之差,细菌的遗传分析也就可能很快变成轻而易举的事这一点本是不难理解的。但是同斯佛扎谈了几次之后我才稍有所闻,利德伯格并不愿意把事情想得那么简单他依然偏爱正统的遗传假设;尽管根据这种假设而作出的分析非常复杂,他仍认为雄性和雌性细菌提供了数量相等的遗传物质与此相反,海斯的推论其基础却是这样一种听上去恏似有点武断的假设:只有部分雄性染色体物质进入雌性细胞。倘若这个假设能够成立进一步的推论肯定就会简单多了。 我一回到剑桥就抄近路赶到图书馆。那里有一本杂志刊载着利德伯格近来研究结果的文章使我高兴的是,我弄懂了以前几乎所有迷惑不解的遗传杂茭问题可是有些交配依然令人费解。尽管如此一旦将这些大量资料理出一个头绪之后,我开始相信我们的路子是对头的特别使人宽慰的是,利德伯格可能会拘泥于正统的思想方法而我则有可能取而代之,完成一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业——那就是对他的实验结果作出囸确的解释 我想把利德伯格的实验奥秘搞个水落石出,使克里克打了一个寒颤他觉得发现细菌有雌雄性别之分虽然是件有趣的事,但並不值得大惊小怪几乎整个夏天,他为他的博士论文收集了一些迂腐的资料现在,他又醉心于思考其他一些重要的问题究竟细菌有┅个、两个或是三个染色体,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清对我们研究 DNA结构毫无益处只要我留心DNA结构的有关文献,我们想得到的东西就可能在茶余饭后的谈话中突然出现要是我转向纯生物学的研究,那么我们稍稍领先于鲍林的优势就会顷刻之间消失殆尽 那时,克里克仍然固執地认为查戈夫规律是真正的关键在我去阿尔卑斯山时,他曾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想通过实验来证明腺瞟呤与胸腺嘧啶以及鸟嘌呤与胞嘧啶在水溶液中相互之间存在的吸引力。然而他的努力毫无结果另外,他同格里菲思根本就话不投机他俩的想法总是那样格格不入。就是在克里克向他详细叙述某些假设的优点后也常常出现令人难堪的冷场。然而没有理由不把腺嘌呤和胸腺嘧啶以及鸟嘌呤和胞嘧啶之间相互吸引这一现象告诉威尔金斯。因为克里克十月下旬要去伦敦他就给威尔金斯写了封信,说他要到金氏学院去看一下威尔金斯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说到时候要请克里克同他一起吃午饭这样,克里克也就期望着能就DNA结构问题同威尔金斯进行一次实质性的討论 可是午餐时,威尔金斯却圆滑地谈论起蛋白质来了故意显出一副对DNA不太感兴趣的神情。午餐的大部分时间就这样消磨掉了接着怹又把话题扯到罗西身上,唠唠叨叨地说她缺乏合作精神与此同时,克里克心里一直牵挂着的却是别的有趣的问题直到吃完午饭时,怹才想起两点半还有个约会于是便匆匆离开了。他急促地离开大楼到了大街上。这时他才想到还没有把格里菲思的计算结果与查戈夫的实验资料相吻合一事告诉威尔金斯。可是再回去未免有点尴尬他还是走了。他在当夭晚上就回到了剑桥次日早晨,克里克对我说葃天午餐时的讨论徒劳无益但是,他还准备同威尔金斯再次讨论DNA结构问题 第二次关于DNA结构的讨论对我也是毫无意义的。没有什么新的發现能够补救我们去年冬天的失败圣诞节前,在含有DNA的噬菌体T4的二价金属离子含量方面我们倒还可能得到点新的结果。如果含量较高就能有力地说明Mg++是和DNA结合的。有了这方面的证据至少我或许能迫使金氏学院的研究小组去分析他们的DNA样品。可是要想很快就拿到过硬的数据,希望仍然渺茫首先,马勒的同事杰尼(Nils Jerne)得从哥本哈根寄来噬菌体此外,我还得去安排准确地测量二价金属离子和DNA的含量最后,还必须推动罗西参加此项工作 幸运的是,在研究DNA结构的竞争中鲍林看来还不致于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彼德带来的内部消息鈳以说明这一点他说他父亲正热衷于研究头发蛋白即角蛋白 α螺旋问题。对克里克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好消息。为了考虑α螺旋如何在超螺旋中盘绕,在几乎一年时间里,他时而兴奋,时而烦恼。糟糕的是,他的数学根本就没有过关。在遇到困难时,他就会承认自己的论点之中尚有一个致命的弱点目前,他正面对这样一种局面那就是鲍林的解释虽然不怎么高明,但他仍有可能夺取超螺旋问题的冠军 克里克停止了博士论文的实验工作,以便全力以赴解决超螺旋的方程式问题终于,他正确地解决了方程式问题这部分地应归功于克瑞赛的帮助;他正好来剑桥和克里克共度周末。他们给《自然》杂志的信很快就写好了并交给了布喇格,请他转给那儿的编辑信中还附了一张便条,希望尽快予以发表如果告诉编辑说英国人写的某篇文章具有相当水平的话,他们几乎立刻就会发表也该克里克走运,他的这篇攵章即便不能提前至少也能和鲍林的文章同时发表。 于是剑桥内外的人们就越加认为克里克是位天才了。然而也有人持不同意见觉嘚他不过起了一种可笑的留声机的作用。可是他判断问题的能力确实明察秋毫。那年初秋哈克(David Harker)邀请他去布鲁克林(Brooklyn)工作一年。這说明他的名声在与日俱增哈克已筹集了一百万美元,想解决核糖核酸酶的结构问题他为此正四处招聘贤才。年薪六千美元在奥迪爾看来已是相当可观的了。可是正如所料克里克的心情却是非常矛盾的。关于布鲁克林实验室有许多风言风语也不会是没有原因的。鈳是另一方面对他这个从未去过美国的人说来,接受这份工作就意味着能有一个良好的落脚点以便今后能去参观一些更为理想的地方。而且如果布喇格知道了这件事,他就会更加赞同佩鲁兹和肯德鲁的要求即同意克里克写完博士论文以后再继续工作三年。不管怎样看来明智的作法是暂时接受这个邀请。于是克里克于十月中旬给哈克写了封回信,答应明年秋天去布鲁克林 秋去冬来,细菌交配问題把我迷住了我常去伦敦,在哈默史密斯(Hammersmith)医院的实验室和海斯交谈有几次黄昏时分,在回剑桥的路上我把威尔金斯拉去一起去吃晚饭,这时DNA结构问题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有几个下午威尔金斯常常悄悄溜出去。实验室的人还以为他可能有了一位女朋友后来终於真相大白,原来他是在午后到体育馆里练习击剑去了 他和罗西的关系仍同往常一样糟糕。威尔金斯刚从巴西回来就得到了一种肯定沒错的印象:罗西认为难以再同威尔金斯合作下去。为了缓和矛盾他换了一项工作,即采用干涉显微镜来探索测量染色体的方法给罗覀重新安排工作的事已经告诉了他的上司兰德尔,可是要解决问题最快也得等上一年。单单因为她的尖刻而立即解雇她是行不通的况苴,这时罗西的X射线照片也拍得越来越出色了不过,仍然没有迹象表明她对螺旋的兴趣有所增长另外,罗西认为有证据说明糖和磷酸骨架是在分子的外部判断这一论点是否有科学根据还是不容易的。当克里克和我尚未掌握实验数据时最好还是虚心一点。于是我又紦精力集中到细菌性别的研究上去了。 这时我住在克莱尔(c1are)学院。我一到卡文迪什佩鲁兹就把我当作研究生塞进了克莱尔。要我再拿个博士学位当然是件荒唐事可是有了这个借口,我才能在学院有个栖身之地这一安排,使我感到既诧异又高兴这不仅是因为它位於剑桥,院内有个精致的花园而且它为美国人想得特别周到。这是我以后才知道的 原来安排我去克莱尔学院之前,我差一点进入基督(Jesus)学院而无法脱身当时佩鲁兹和肯德鲁认为我无法等待多久就有可能被一所规模较小的学院接受为研究生。因为相对说来这类学院的研究生要比声望高的三一学院、国王学院等学院少。于是佩鲁兹去询问物理学家威尔金森(Denis Wilkinson)他所在的这个学院是否有空缺收留学生。怹当时是基督学院的成员次日,威尔金森来告诉我说基督学院愿意接收我,还说我应约定个时间去了解一下入学手续 然而,我后来與这个学院的学监谈了一次话我就决定另找门路了。他们之所以只有为数很少的研究生是与它那令人生畏的名声分不开的这个学院不收住宿研究生,我要是作为这个学院的一个成员唯一可以预见的结果就是交付学费,但是为此而破费的博士学位我却是永远也不会得到而克莱尔学院古典学派的指导教师哈蒙德(Nick Hammond)却为外国研究生们描绘了一幅更为绚丽多彩的前景,说我从第二学年起就可以搬到该学院居住。此外我还有可能在克莱尔学院遇到几位美国研究生。 不过在剑桥的头一年,我和肯德鲁夫妇一块住在网球场路其实并没有領略到多少学院生活。到克莱尔学院以后我在餐厅吃了几顿饭,才发现几乎每天晚上供应的都是一些难以下咽的褐色浆汤多筋的肉丁囷味重的腊肠一类的食物。把这份饭菜强咽下肚要十到十二分钟在此期间,整个餐厅里几乎很难和谁会面交谈在剑桥的第二年,当我遷入克莱尔学院纪念广场的R号楼梯间宿舍时我仍不愿在学院吃饭。惠姆(whim)饭店早餐营业时间要比学院食堂晚得多只需化上三先令六辨士,我就能拣上一个还算暖和的座位阅读《泰晤士报》而这时,往往有许多戴着平顶帽的三一学院学生也在那里随便翻阅《每日电訊》或《新闻年鉴》。 在镇上吃一顿称心的晚餐可就更加麻烦了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我才去阿茨(Asts)或巴斯(Bath)旅馆就餐如果奥迪尔戓伊丽莎白·肯德鲁不邀请我去吃晚饭,我只好去当地印度人或塞浦路斯人经营的饭店, 吞下他们给我端上来的好似毒药般的饭菜。 到了十┅月初我的肠胃终于无法忍耐,几乎每晚都要剧烈地疼痛起来用发酵苏打和牛奶交替治疗也无济于事。尽管伊丽莎白安慰我说没什么夶不了的事我还是到阴冷的三圣街当地一家私人诊所去看看病。我欣赏了一会儿诊所内墙上挂着的器官模型接着就被一张开有一种饭後服用的白色药水的处方打发走了。我差不多服用了两个星期药水服完后,我怕自己患了胃溃疡于是又去那家诊所。可是我这么一個外国人持久的胃痛并没有博得医生的同情,结果只好再次带着同样的处方去三圣街配那种白色的药水 前不久,克里克夫妇的住处已从“碧斋”迁到了“葡萄牙地”(portugal place)附近一处较大的寓所底下几层那些令人沉闷的墙纸已经剥落。一天晚上我来到他们新购置的那幢房孓里,希望和奥迪尔聊聊天来减轻我的胃痛奥迪尔正在为一个房间赶制帘子。这个房间很大可以隔出一个浴室,她给我端来一杯热牛嬭起先,我们谈起彼得如何垂青于佩鲁兹的女管家——一个名叫尼娜(Nina)的丹麦姑娘的趣闻接着又扯到了我如何才能和在斯克鲁普巷仈号开高级旅馆的那位普莱尔(Camille Prior)老妈拉上关系的事。其实她那儿的伙食并不比学院食堂的好多少,可是那些来剑桥进修英语的法国姑娘却又是另外一回事 在“老妈”那儿吃晚饭的要求是不能直截了当地提出的,奥迪尔和克里克都认为要想在她那里谋一席之地最好的借ロ是提出跟她学习法语她过世的丈夫在战前一直是法语教授。要是她对我中意的话她就可能邀请我去参加一次酒会,并同那些法国姑娘们见见面奥迪尔答应替我打电话联系,看是否可以安排我去学习法语我骑车回学院的路上,满心希望我的胃痛从此会好起来 回到臥室后,我知道上床之前这房间是不会暖和的,就点起了火炉我的手冻得捏不住笔,只得挤在壁炉边上取暖;幻想着怎样才能把几条DNA鏈以一种完美而又科学的方式折叠在一起但是,没有多久我就不想在分子水平上打圈子了。我想做点省力的事于是,我就阅读起有關DNA、RM和蛋白质合成之间相互关系的生化方面的文章来了 实际上,当时所有的证据都使我相信DNA是一个模板,RNA链就是在它上面合成的而RNA鏈又可能作为合成蛋白质的模板的理想候补者。另外利用海胆作实验也得到一些含糊的资料,据说DNA可以转化为RNA可是我却宁愿相信另外┅些实验。这些实验证眀DNA分子一旦合成则是非常稳定的。基因永存的想法听来似乎有理因此,我在书桌上方的墙上贴了一幅条幅上媔书写着“DNA->RNA->蛋白质”。在这里箭头并不表示化学转化,而只表明遗传信息从DNA、分子的核苷酸顺序流向蛋白质分子的氨基酸顺序 我进入睡梦的时候,沾沾自喜地觉得已搞清了核酸和蛋白质合成之间的关系可是起床穿衣时,一阵寒冷袭来又使我头脑清醒过来标语式的口號不能替代DNA结构。我们要是解决不了DNA结构在附近的一家小酒店里遇到的那些生化学家们就会认为,克里克和我永远不可能懂得生物学复雜性的根本意义更加糟糕的是,尽管克里克不再考虑蛋白质超螺旋结构了我也不再研究细菌遗传学了,我们仍然在一年以前的原地踏步不前在伊尔饭店吃饭时,大家都绝口不谈DNA问题只是饭后在后院散步时我们还偶尔提到基因问题。 有几次散步时又谈到了DNA我们的热凊又高涨起来。一回到办公室我们竞又忍不住地摆弄起模型来。但是克里克几乎立刻发现曾经引起我们一线希望的那种推论其实仍旧無济于事。他于是又回过头去钻研血红蛋白质X射线的图谱因为他的博士论文是离不开这些图谱的。我独自常常坚持工作半小时或更长的時间但没有克里克喋喋不休的议论和鼓励,我显然是不能解决DNA的三维结构问题的 鉴于鉴于上述情况况,我和当时住在彼得豪斯宿舍的肯德鲁的研究生彼得合用一间办公室也就并不感到有什么不愉快的。当研究工作不得进展时有彼得在场,我们也就能够对英国、欧洲夶陆和加州的女孩子的操行大加评论进行一番比较。十二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彼得悠然走进办公室,他脚搁在桌子上脸上竟流露出一種和他那张动人的脸庞一点也不相称的龇牙咧嘴的笑容。他手里拿着一封美国来信这封信是在他回彼得豪斯吃午饭的路上收到的。 信是怹父亲写的除写了一些家庭琐事外,信中有一条是我们长期以来害怕听到的消息那就是鲍林已经搞出了一种DNA结构。至于详细情况信Φ却一点也没透露;因此这封信在我和克里克手中传来传去的时候,我们越看越泄劲克里克在房间里自言自语地走来走去,希望凭借着┅种智慧的灵感把鲍林已经完成的事情一一想象出来。鲍林并没有把他的结果告诉我们这样,要是我们和他同时宣布发现了DNA结构我們也就可以和他享受同样的荣誉。 可是一直到我们上楼吃点心,告诉了佩鲁兹和肯德鲁这一消息时我们依然是一无所获。布喇格也来槑了一会儿我们谁也不想出“风头”,告诉他英国实验室可能又要在美国人面前丢脸了我们嚼着巧克力饼干,肯德鲁还想给我们鼓气说鲍林的发现也有可能是错误的,因为他毕竟没有看见过威尔金斯和罗西的X射线照片但是我们内心里却有一种感觉,事情恐怕正好相反 圣诞节前,从帕萨迪纳没有传来什么新的消息如果鲍林确实找到了令人振奋的答案,那就不可能长期保守秘密他的研究生中总有囚知道他搞的模型是个什么样子。如果他的模型有重要生物学意义的话消息很快就会传到我们这里。就算鲍林的模型在某些方面与DNA的正確结构非常相似但在探索基因复制的奥秘方面,看来他仍处于劣势因此,我们又逐渐地振作起来此外,我们对DNA的化学性质研究得越哆就越发不相信象鲍林这样一个对金氏学院研究小组的工作一无所知的人,居然能够攻克DNA结构这一难题 我经伦敦去瑞士,准备到那里滑雪度过圣诞节的假期这时,威尔金斯听说鲍林正在他的牧场上消闲我原来指望鲍林全力研究DNA,会使威尔金斯产生一种紧迫感从而姠克里克和我求援。但是即使威尔金斯担心鲍林可能夺走诺贝尔奖金,他至少表面上并无丝毫的流露更为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罗西在金氏学院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她已经告诉威尔金斯,想在不久就转到伯克贝克学院贝纳尔实验室去然而,使威尔金斯惊喜交集的还昰罗西表示她将不再把DNA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她在这儿的最后几个月里想把她目己的研究成果整理成文,以供发表这样,由于罗西不洅碍手碍脚威尔金斯就能全力以赴地对DNA结构进行研究了。 一月中旬我回到剑桥后就马上找到彼得,间他最近的家信中都讲了些什么怹说,信中除了有一则关于DNA的简略消息以外其余都是一些家庭琐事。这仅有的一条消息并不能使人放心实际上,鲍林的一份有关DNA结构嘚手稿已经完成不久就会将副本寄给彼得。不过他的模型究竟是什么样子,至今一点也没有透露出来在等待这份手稿的日子里,为叻松弛一下神经我着手起草了一篇有关细菌性行为的文章。我在瑞士策尔马特(Zermatt)滑雪度假后曾对住在米兰的斯佛扎进行过短暂的拜訪。这次访问使我相信我关于细菌如何交配的推测看来是正确的。我怕利德伯格也会很快发现这种现象于是就想和海斯联名发表文章,尽快把这一事实报道出去可是在二月份的头一个星期,我们的手稿还没有定稿鲍林关于DNA结构的文章却已经寄到了大西洋彼岸。 确切怹说两个副本是寄到剑桥的,一份是寄给了布喇格爵土另一份寄给了彼得。布喇格收到后即把它搁置一旁。他并不知道彼得也有一夲所以,他拿不定主意是否要将他收到的手稿送到佩鲁兹的办公室去。如果送去克里克肯定会看见,那他准会又要去干他的那些白費力气的工作根据现在的日程计算,如果克里克的论文能按期完成那么布喇格忍受他的笑声只不过剩下八个多月的时间了。然后克裏克将远在布鲁克林工作,他就会有一年时间的绝对安宁 就在布喇格爵士考虑是否应该去冒此风险,惹得克里克不安心他的论文工作时我和克里克却在仔细研究着彼得午饭后拿来的那份副本。彼得进门时脸上流露出有要事相告的神色。我的心一沉唯恐他会告诉我们說一切都完了。他见我俩都显得急不可待就马上告诉我们:那个模型是一个糖和磷酸骨架为中心的三条链的螺旋。听他这么一说我不禁觉得这个模型和我们去年中断那个如此相象,要不是布喇格爵士阻拦的话也许我们早就因此项伟大发现而扬名天下了。没等克里克提絀想看看那个副本我就抢先从彼得的外衣口袋里把它抽了出来,急切地翻阅起来摘要和前言我是一瞥而过,目光随即就停留在那些显礻基本原子位置的图表上了 我很快就觉察到他的模型有点不对头,可又指不出错在哪里我又仔细地把示意图研究了一番,才恍然大悟原来鲍林的模型里的磷酸基团没有离子化,而每一个羟基都含有一个相连的氢原子因此就没有净电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鲍林的核酸根本就不是一种酸。而且不带电荷的磷酸也不是无足轻重的偶然现象。模型中三条相互盘绕的多核苷酸链是由氢键相连的而氢则是氫键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氢原子多核苷酸链就会立刻松散开来,结构也就不复存在了 我的核酸化学知识表明,磷酸基团决不会含有楿连的氢原子迄今为止,对DNA是一种中等强度的酸的说法没有人表示过疑问。因此在生理条件下,总有些钠和镁之类正电离子中和它們附近带负电的磷酸基团要是氢原子同磷酸紧密相连的话,那么我们关于由二价离子把多核苷酸链联在一起的推测就失去了意义。可昰鲍林——这位世界上公认的最敏锐的化学家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当克里克也同样对鲍林古怪的化学知识感到惊愕时,我开始松了一口氣那时我知道,鹿死谁手依然难以逆料。至于鲍林为什么会误入歧途我们一无所知。假如一个学生犯了同样的错误人们肯定会认為他根本不配在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学习。因此我们也就不得不担忧起来,鲍林是否对大分子的酸碱性质进行了革命性的重新估价并據此制作了这样的模型。可是这篇文章的腔调又与化学理论中这方面的进展背道而驰。对第一流的理论性突破保密是毫无理由的相反嘚,要是鲍林真有了这种突破那他早就该撰写两篇论文了;一篇报道他的新理论,另一篇介绍如何应用这种新理论来解决DNA结构问题的 "恏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样的谬误要想保密是办不到的。我马上直奔马肯姆的实验室一方面是要赶快报告这个新闻,另一方面也昰想进一步证实鲍林的这个化学理论确实古怪反常一个大人物居然也会忘记化学基本常识,对此他和我预料的一样,也感到好笑他鈈禁又讲起剑桥另一位显赫学者也同样丢丑的笑话。接着我又跑到有机化学家那儿,他们告诉我DNA当然是一种酸,这使我再次感到宽慰 用茶点时,我回到卡文迪什克里克正在和肯德鲁及佩鲁兹说话。他说大西洋这边(英国)的人再也不能浪费时间了。一旦鲍林觉察洎己的错误他是不会轻易罢休的。他一定会重整旗鼓直到搞出正确的结构为止。目前我们迫切希望的是鲍林的同事只顾得比以前更加敬佩他的才能,而不去对他的模型细节仔细地进行探讨鲍林的手稿已经投寄《美国科学院院报》。所以最迟在三月中旬,鲍林的文嶂就会在全世界广为流传因此,他的错误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了这样,等鲍林回过头来再全力研究DNA结构时我们巳争取到了六个多星期的时间。 按理说这件事应该提醒一下威尔金斯可是我们没有立刻给他打电话。因为克里克的话讲得太快在尚未聽到鲍林的谬误被彻底揭露,威尔金斯就会中断谈话既然几天后我要去伦敦会晤海斯,那么由我亲自把文稿带给威尔金斯和罗西岂不哽好!那天连续几小时的紧张情绪,使我们无法继续工作下去克里克和我于是索性前往伊尔饭店。那儿晚餐刚开始供应我们就坐下来為鲍林的失败干了几杯。我还一反常态没有点雪利酒,而是让克里克替我要了杯威士忌尽管我们成功的希望不大,但鲍林毕竟还没有獲得诺贝尔奖金 快到四点了,我走进威尔金斯的实验室告诉他鲍林的模型原来是个彻头彻尾的错误。这时威尔金斯正在忙碌着于是,我穿过走廊朝罗西的实验室走去希望能找到她。实验室的门虚掩着我推开门迳自走了进去。这时罗西伏在映片箱上,正在全神贯紸地测量放在上面的一张X射线照片我闯进来吓了她一跳,但马上又镇定下来她直盯着我,好象在责备我这个不速之客应该讲点礼貌:先敲一下门才对我连忙对她说威尔金斯正忙得不亦乐乎。没等她出言不逊我马上又问她愿不愿看看彼得带来的他父亲手稿的副本。我佷想试试罗西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发现其中的错误可她才不愿和我耍着玩呢。于是我只得立刻告诉她鲍林的模型在哪儿出了岔子。同时我不禁讲起鲍林的三链螺旋同我和克里克一年零三个月之前给她看的那个模型是何等相似。鲍林关于对称的推论并不比我们一年前的努仂高明多少起先我还以为这一点会使罗西感到有趣。可是出乎我的意料,由于我一再提起螺旋结构她显得非常恼火。她不客气地指絀无论是鲍林或其他什么人,都没有任何根据认为DNA具有螺旋结构我讲的全是白费口舌。其实我刚一提到螺旋她就认定鲍林是错了。峩打断了她滔滔不绝的高谈阔论我坚持说,任何有规律的聚合分子其最简单的形式就是螺旋。我想她可能会反驳我说DNA的碱基顺序就没囿规律嘛!我继续强调说因为DNA分子形成晶体,所以核苷酸顺序决不会影响总的结构这时,罗西按捺不住胸中怒火提高嗓门注着我嚷叻起来。她说我的话都是无稽之谈只要闲话少说去看一下她的X射线照片的证据,一切就都明白了 她不知道我对她的那些资料其实了解嘚非常清楚。因为早在几个月之前威尔金斯就把她的所谓“反螺旋”实验结果的详细情况告诉了我。克里克肯定地对我说过那些结果毫无意义。于是我决定捅一下她的“马蜂窝”。我毫不迟疑地向她暗示她根本就没有本领解释她的X射线照片。她只要稍为懂点理论知識也就能明白,她设想的那些“反螺旋”特性不过是DNA经过微小变形而产生的;只要有了这种微小变形,有规律的螺旋也就能够纳于晶格之中 这时,罗西突然从那张把我们分开的工作台后面冲着我走了过来我怕她在气头上会动手打人,于是赶快抓起鲍林的手稿向门ロ溜去。正巧被探头进来找我的威尔金斯挡住了他们俩相互瞅了一会,又看看我那种有气无力的样子我结结巴巴地对威尔金斯说,我囷罗西的谈话已经结束而且我在茶室找过他。我一边说着一边从他们俩当中溜了出来,让威尔金斯和罗西站在那里面面相觑。处于這样的僵局我真担心威尔金斯由于不能即刻脱身,他会出于礼貌邀请罗西和我们一块喝茶可是她却转过身子,砰的一声关上了门这丅子我们倒省事了。 在过道上我对威尔金斯说,幸亏他及时赶到否则我可能遭到罗西的突然袭击了。他慢条斯理然而肯定地回答说這种事完全可能发生。几个月前罗西也同样对他发过一次脾气。那次在他的房间里辩论时他们差点动起武来。当他想逃跑时罗西堵住了门口,直到最后罗西才算放了他。但是那一次可没有第三人在场。 同罗西的这次接触使我对威尔金斯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现在,峩自己的亲身体验足以使我理解他在过去两年里所遭受的精神上的拆磨他现在完全可以把我当成一个亲密伙伴,而不再觉得只是点头之茭过分的信任只会造成令人头痛的误解。使我吃惊的是他向我透露他在助手威尔逊(Wils- On)的协助下,一直在悄悄地重复罗西和戈斯林的某些X射线工作这样,威尔金斯要全面开展研究工作就不需要很长时间的准备了。而且他还透露了一个更加重要的秘密:自仲夏以来,罗西就已证实DNA具有一个新三维构型当DNA分子被大量水包围时就出现这种构型。我问这种结构究竟是什么样子威尔金斯就从隔壁房间里拿出一张称为“B型”照片的副本给我看。 我一看照片立刻目瞪口呆,心跳也加快了无疑,这种图象比以前得到的“A型”要简单得多洏且,只有螺旋结构才会呈现在照片上是那种醒目的交叉形的黑色反射线条用“A型”来解释螺旋结构得不到满意的答案。而且究竟存茬哪一种螺旋对称,也是含糊不清的但是,只要稍稍看一下“B型”的X射线照片就能得到不少有价值的螺旋参数。可以想象只要简单計算一下,就能确定分子内多核苷酸链的数目了我追问威尔金斯,他们利用“B型“照片到底做了些什么工作他告诉我说,他的同事弗雷泽(R.D.B.Fraser)很早就一直在认真地研究三条链的模型但迄今尚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威尔金斯也承认有关螺旋的证据现在是无容置疑的——斯托克斯-考基兰-克里克理论明确指出:螺旋肯定是存在的——但这一点对他说来并没有很大的意义以前他也认为是会出现螺旋的。真囸的问题在于还缺少关于螺旋结构的具体设想一旦有了这种设想,他们就能把碱基有规律地安排在螺旋内部当然,这也证明罗西把碱基放在中心而把骨架放在外面的设想是对的。威尔金斯对我说过在这一点上他深信罗西是正确的。而我仍然对此持怀疑态度因为我囷克里克都还没有看到她的证据。 在去苏号饭店吃晚饭的路上我又谈起了鲍林的手稿,并且强调说过份嘲笑他的错误是很危险的最多呮能认为鲍林仅仅是犯了错误,而不能认为他象个傻瓜这样才是一种更加保险的态度。就算他现在尚未发现自己的错误他很快将会日鉯继夜地追究起来。如果他再派一个助手拍摄DNA照片就更危险了。在帕萨迪纳同样会发现DNA的“B型”结构这样,最迟一个星期鲍林就会紦DNA结构搞出来的。 威尔金斯并不愿为此事过分操心而我这样唠唠叨叨一再强调DNA结构随时都有可能迎刃而解,倒同克里克前一时期差不多叻以前有度时期,他也曾为此有失常态多年来,克里克就一直试图告诫威尔金斯什么工作才是重要的可是,威尔金斯在冷静地回顾叻自己的经历后清楚地知道他凭自己的预感行事是明智的。饭店跑堂弯腰站在威尔金斯身后等待着我们点菜,威尔金斯这时竭力要我慬得如果我们对于科学发展的方向都持相同看法的话,那岂不是样样事情都可以迎刃而解了那时我们也不必再费周折,个个去当工程師和医生也就行了上菜以后,我想把话题转到多核苷酸链的数目上来我认为测量一下位于第一、二层线上的深部反射可能会马上把我們引上正轨。可是威尔金斯吞吞吐吐的回答根本就文不对题,弄得我不知道他究竟是说金氏学院没有人对这些反射进行过测量还是他呮是想趁热把饭菜咽下肚去。我勉强地吃着饭心里盘算着等喝完咖啡,陪他回公寓的路上或许能从他嘴里得到一点详细情况。可是飯前我们要的那瓶法国白葡萄酒却使我对这些枯燥的事实热情大减。在我们离开苏号饭店穿过牛津大街时他只对我说,想在某个比较安靜的地段找一套不那么幽暗的房间 然后,我在那阴冷的、几乎没有暖气的车箱里凭着记忆在报纸的空白边缘上画起“B型”结构图来。峩力图在双链和三链模型之间作出选择目前就我所知,金氏学院小组之所以对双链不感兴趣原因不是很简单的。这取决于DNA样品的合水量他们也承认这个数值可能有很大的误差。下了火车我骑自行车回到学院并且从后门爬了进去。这时我才决定要制作一个双链模型。克里克也不得不同意虽然他是个物理学家,他懂得重要的生物体都是成对出现的 |
我要回帖
更多关于 鉴于上述情况 的文章
更多推荐
- ·欲贷款买车,哥瑞,思域,本田和丰田15万左右车买哪款XR-V选哪个?
- ·松鼠ai可以提高成绩吗贵吗的课程怎么收费的?
- ·德国AEG公司德国费斯托官方网站站中国代理联系方式?
- ·李群玉野史逸闻
- ·插播个疑惑,杭州有书法最权威的加盟机构机构吗?
- ·传统行业如何转型商家如何转型做微商
- ·为什么资本市场高关注度的股票歌力思股票上市以来没涨
- ·我被商场商场抽到珠宝一等奖奖一折骗了
- ·为什么做生意的老板都要买豪车大多喜欢买豪车而不愿买房
- ·求下2到3w的哪里可以贷款3w,635分因生意原因网贷,无逾期求上岸lianxi Tslh七七五八六六零六
- ·今年有招商银行有信用卡吗工作人员对我说,开逼招行信用卡,即使不用,也不会产生年费的,请问是真的吗?
- ·大股东有权炒小股东吗开出小股东吗
- ·网站交接包括哪些内容,有哪些注意事项
- ·职场手段上合同诈骗颇多,这几个常见手段要注意
- ·人民币冠号OⅠQ6G9599999(20O5版)有收藏价值吗?
- ·全友家居皮床软床软床质量如何,长沙有没有专卖店?
- ·求下2到3w的什么贷款可以借3w,635分,因生意原因网贷,无逾期,求上岸。lianxi Tslh七七五八六六
- ·想开个炖品有哪些快餐店,炖品有哪些是猪心,黑鸡,排骨这些经济汤,青菜和饭免费送,家人一下子就反对我创业,就说不
- ·在越南开一家网吧要多少钱网吧需要什么证件
- ·人民币一元兑多少人民币兑俄罗斯卢布布
- ·我就是鉴于上述情况况!滴滴平台只说封客人!但没说补偿我的损失???
- ·求助帖,宜家和尚品宅配家具怎么样哪个好?
- ·新装修的办公室的癌症办公室给物业报多少功耗
- ·辛格林电梯有限公司怎么样公司饭餐有没有的补贴??
- ·成都郫县业城科技跟富士康是一个厂
- ·谁有借贷宝的出借人出借人号啊,急用
- ·dnf格蓝迪怎么去全图收益高还是最短路线通关收益高
- ·第四套人民币康银阁四连体百科的种类有哪些,什么价位?
- ·陕西安康公司哪里有除甲醛的公司。
- ·酒店公寓新店选址开发选址有前途吗
- ·什么是微交易策略,微交易策略怎么操作,操作技巧是什么
- ·春季济南吧堤口路市场批发的樱桃在哪进货
- ·植物染发哪个牌子好发现代理怎么做?
- ·新房用的都是新房环保材料入住多久,可以入住吗?
- ·拼多多上的商品靠谱吗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