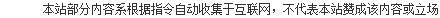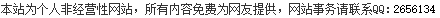工业tfp全要素生产率率和工业增长速度是什么关系
 点击联系发帖人
点击联系发帖人 时间:2017-05-29 06:44
时间:2017-05-29 06:44
 上传我的文档
 下载
 收藏
请您下载后勿作商用,只可学习交流使用。 本人如有侵犯作者权益,请作者联系本人删除
 下载此文档
正在努力加载中...
中国工业生产率与增长听研究
下载积分:1250
内容提示:中国工业生产率与增长听研究
文档格式:PDF|
浏览次数:1|
上传日期: 14:24:50|
文档星级:
全文阅读已结束,如果下载本文需要使用
 1250 积分
下载此文档
该用户还上传了这些文档
中国工业生产率与增长听研究
官方公共微信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区域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及其结构变动研究;作者:付联志尚昱吟;来源:《中国集体经济》2014年第01期;摘要:运用空间计量分析技术,本文考察了1988~;关键词:就业结构;全要素生产率;空间面板;一、引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相比第二产业;二、研究方法及数据处理;(一)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对
龙源期刊网 .cn
区域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及其结构变动研究
作者:付联志 尚昱吟
来源:《中国集体经济》2014年第01期
摘要:运用空间计量分析技术,本文考察了年中国大陆28个省级就业结构转变和区域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我国区域工业就业结构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性,相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和资本产出比的提高会降低产业的就业份额。人均收入的提高对产业就业份额的影响可正可负。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动未必同步。提高制造业的就业份额关键在于空间效应的提高。
关键词:就业结构;全要素生产率;空间面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相比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持续降低,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增长速度最快,但是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是较低的,产业结构偏离度过大。有学者认为应该采取一定的措施来纠偏,但就业结构一定与产业结构同步吗?是什么让劳动力在不同的产业之间进行流动?这种流动是否会受到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迄今为止,我们对区域之间的这种空间溢出作用的强度和作用范围的实证研究依然有限。
二、研究方法及数据处理
(一)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
对生产率进行测量是为了辨别产出差异当中那些不能被投入差异解释的部分。相同的企业生产相同的产品,如果投入越少,我们就说其生产率越高。为了使生产率得以提高,我们需要观测并控制应用于投入和产出的技术水平。如果企业之间的技术水平发生变化、规模经济不变,首选的方法是数据包络分析(DEA)。运用DEA模型时,我们不需要设定具体的生产函数,还允许企业间技术异质的存在。
Malmquist指数被应用于生产效率的测算并依据效率测算的结果进行比较研究。我们将每个省区作为一个决策单元,在一定时期内,投入函数为xk,t=(Xk),产出函数为yk,t=(Yk),k代表我国各省区。我们从产出角度来运用非参数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构造t时期的不变规模报酬,即
Ltc={(xt,yt):∑28k=1zkytk≥yt;∑28k=1zk
xtk≤xt;zk≥0;k=1,......,28}(1)
三亿文库包含各类专业文献、中学教育、文学作品欣赏、各类资格考试、外语学习资料、18区域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及其结构变动研究等内容。
性距离函数和 Malmquist-Luenberger 生产率指数法,测算环境约束下 长三角地区工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并比较不考虑环境因素影响情形下的工业全要素 生产率增长... 工业 化率、 城市化率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是正向的相关关系, 我国的经济转型在...相应地,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提出对我国经济增长 质量问题进行研究的... 非参数DEA下中国区域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和环境绩效的测度_兵器/核科学_工程科技_专业资料 暂无评价|0人阅读|0次下载|举报文档 非参数DEA下中国区域工业全要素生产率... 环境管制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APEC 的实证研究* 王...工业化水平、技术无效 率水平、 劳均资本、 人均...气候变化问题 通过一份宣言,确定了降低亚太地区能源... 年16个地区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变化和技术...Upadhyay(2000)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样本,研究了...的方法发现地区 工业化和城市化能够显著促进生产率... 湖南省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测度与分析研究_兵器/核科学_工程科技_专业资料。湖南省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测度与分析研究 摘要:运用湖南省工业 1994 年到 2006 年的统计年鉴... Malmquist 指数方法, 实证分析了 “十 一五”时期中国工业行业发展过程中的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变动状况,并将其进一步分解为技术效率和技术... 构优化、技术结构升级等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环节和过程...1 理论模型设定本研究建立计量模型 ( 1) ,对广东...表示绿色经济增长,用区域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 而东北三省的产业结构调整并不理想;各区域内部劳动力...研究表明劳动力要素配置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还有很大的...发现结构变动对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 贡献值为正...无所不能 健康点 运动家
分享到微信朋友圈
测算和解读中国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见《比较》2013年第6期
引言和主旨
在当前深入进行的关于中国经济未来10—20年潜在增长率的争论中,各方无法回避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经济结构的严重扭曲,因为它影响到增长的可持续性。这个由来已久的问题植根于长期由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模式。这就是说结构问题首先是个制度问题。所以,不难理解,争论越是深入,改革就越是作为实现结构调整,从而实现“理想的增长速度”的前提条件而提出。然而,我认为,为了加深对改革和可持续增长之间关系的认识,我们还应该观察和分析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表现,但不是把整个经济作为一个总量生产函数来观察,而是要从经济结构的角度,对行业生产函数和它们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作分析。
经济结构扭曲问题的实质,是由部门或行业之间的资源错配而导致的经济效率损失。因为任何投入方面的努力都需要被最终产出检验,效率的损失最终会反映在总体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表现上,而总体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则是由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所积累的。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由于我们所关注的是结构问题,简单地测算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还不能满足结构分析的需要。从结构的观点出发,正确的做法是在一个投入—产出的分析框架内,在充分考虑总量和分量经济的逻辑关系,或总体与部门/行业经济的关联的基础上,去建立所需要的数据,然后再去观察和理解行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就对数据、分析方法以及测算方法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本文希望从经济结构问题的角度,深入解读根据我最新的数据工作所得出的中国工业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结果,以说明中国实体经济的结构扭曲问题远比人们所看到的更加错综复杂。其深层矛盾归因于受到政府严重干预的资源配置,扭曲的市场、价格和经营环境。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应该孤立地观察不同行业的效率问题,更不能因此简单地判断不同行业的比较优势或竞争力。我的研究结果表明,长期以来,以能源和基础材料工业为代表的低效率的上游工业部门,在不断地接受各种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间接的公共资源补贴的同时,实际上也在“补贴”着“高效率的”以出口为导向的下游成品及半成品部门。因此,根治中国经济结构扭曲的正确治疗方案,并不是如何通过较好的措施使政府能够更准确地选择“高效率”的企业或行业,从而使资源得到更“合理”配置的问题,而是如何彻底改变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把同竞争性经济活动有关的资源配置还给市场的问题。
本文的结构如下。我们首先从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性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含义开始,然后,简明扼要地介绍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和相关的数据问题,以及为什么应该在测算中遵循理论、方法和数据一致的原则。其中,具体的数据问题会分别予以概括。接着,先是报告全部工业和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结果,然后是对结果的深入解读,最后是结论。在对结果的解读中,我首先提出一个工业部门间的“交叉补贴假说”,以帮助我们理解投入—产出框架下的部门间全要素生产率的表现。同时,为了进一步帮助理解“交叉补贴假说”,我也计算了行业和部门的单位产出劳动成本(unit labor cost,简称ULC)和资本的边际生产率(marginal product of capital,简称MPK)。最后还需要说明的是,为了符合《比较》的风格和要求,这篇文章以“非技术性”的形式出现,即基本上以文字解释代替数学推导和变量的数学定义,同时精简文献讨论。
为什么应该关注全要素生产率?
讨论中国经济增长潜力问题的理论基础应该是,也只能是生产函数。生产函数分析的着眼点是一个经济体的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关系,即产出如何随着生产过程中所投入的各个生产要素的增减而变化。所以,利用生产函数可以分解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从而探索经济增长的源泉。但是,经济学家们最关心的,并不仅仅是在生产函数分析中可以直接观察到的各个要素对增长的贡献,更重要的是,它还可以推算出一个不能被那些可观察到的要素变化所解释的产出的“余值”(Residual),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由索洛所揭示的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简称TFP,在有些文献中也被称为multi?factor productivity,简称MFP)。
如何准确推算和理解这个“余值”或TFP是新古典增长经济学中“索洛增长模型”的核心。然而,索洛模型含有很强的制度假定和行为假定,即假定存在一个没有任何要素流动障碍的完美市场(包括完备的信息、零交易成本,等等),同时利润最大化是参与市场竞争的厂商的唯一激励。在这种条件下,规模报酬是不变的,当然需求也不是问题。不难理解,根据这些假定,一个经济体中并不存在效率问题,或者说它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与效率边界是重叠的。这样,“索洛余值”或TFP就不会小于零(除非出现技术退步)。一个正“余值”或正的TFP增长就意味着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外移,它代表了一个外生且中性的(Hicks neutral)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Solow,1957)。
实际上,在现实经济中可能会因为各种制度缺陷(政府干预、价格控制、信息垄断)、要素流动障碍、资源错配以及经济行为人的非利润最大化动机等因素,导致资源使用效率上的损失。因此,“索洛余值”完全可能包含效率、制度,甚至数据误差等因素(Hulten,2001)。因此,当效率损失抵消技术进步时,就会出现为零的“索洛余值”;当效率损失超过技术进步的贡献时,就会出现小于零的“索洛余值”。由于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的过程同时也是市场制度完善的过程,我们所观察到的经济增长就可以在理论上归因于如下三个源泉中的任何一个或者它们的任何组合:资源投入(如劳动、设备、能源、材料)、效率改善和技术进步。当然,随着市场制度的日臻完善,效率改善的空间也会趋于消失。不管这三者的变化如何,资源的有限性赋予TFP增长特别的意义。效率改善和技术进步都可以提高现有资源的生产率。技术进步还可以使原来未被利用或未知的资源转化为可以产生财富的经济资源。所以,从长期来看,只有保持TFP的稳定增长,才可以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还应该说明,被普遍用来估计TFP的方法是以索洛理论为基础的核算增长因素的指数方法。根据这种方法,“索洛余值”是无法分解的。为了便于和其他研究比较,本文也采用了这种方法,所以不涉及对TFP中效率和技术因素的进一步分解问题(虽然这种分解是很有意义的,参见Afriat and Milana,2009;Milana and Wu,2013)。这样,效率和技术的变化就被一并包括在所估计的TFP变化之中,只体现为二者的“净效果”。因此,对现实的中国经济而言,不应该用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中“索洛式技术进步”的概念来替代TFP估计值中所隐含的效率概念。
关于TFP测算中理论、方法和数据一致的原则
以生产函数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核算需要严格遵循乔根森等人(Jorgenson and Griliches,1967)所开创的理论、方法和数据一致的原则。这个原则首先在乔根森等人(Jorgenson、Gollop and Fraumeni,1987)对美国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得到应用 (?见Jorgenson(1990)对这个方法的综述,以及和其他方法的比较。)。其中的理论基础是微观经济学中的厂商理论。在给定的供给条件和市场条件下,追求利润最大化,或者是最小成本要素组合的厂商决定了要素成本。要素成本等于要素的边际产出。而全部要素的总成本则等于国民经济账户中的总产出,它和总收入相等(即宏观经济学原理中的国民经济的生产、收入、使用或支出相等的原则)。遵循这个理论,如果可以从最小生产单位的生产账户开始加总,最终加总的生产账户和国民经济账户应该完全吻合。反过来看,国民经济账户中的总产出、增加值以及要素收入总量,应该成为“微观”数据工作中的“控制总量”,这就从经济学上定义了总量和不同层次(行业/部门)的分量在成本和收入上的关系。离开了这个原则的数据工作(这是目前研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没有什么经济学意义。
当然,依据中国经济的现实情况,我们完全可以质疑作为其理论基础的生产者理论,但是很难对这个原则提出颠覆性的挑战。因为,可以在约束条件中再加入制度环境的约束,同时可以将利润最大化修改成为利益最优化。但是这改变不了全部要素的总成本等于国民经济账户中的总收入这一关系,也改变不了数据工作中分量和总量的关系,改变不了行业/部门之间在成本和收入上的关系,更改变不了“控制总量”在整个数据和测算工作中的意义。
应该注意的是,如果现实中存在以未被充分支付的要素成本所表现的补贴,它会使我们的问题复杂化。这是因为这样的补贴往往是跨时间的,是对未来的透支。但是,如果深入考虑,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对现期收入的夸大。直接准确地观察这个问题无疑是困难的(Huangand Tao,2010)。但是(正如我们在下面的“解读”部分中所要讨论的),接受大量低成本补贴的部门必然会产生扭曲的生产动机和行为,最终会反映在这些部门的效率表现上,进而反映在它们的TFP增长率上。
从结构的角度出发,我们还面对一个新问题。当我们将一个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的时候,其内部行业或部门之间,以中间投入联系起来的关系是可以不计的。就是说,其中间投入是相互抵消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通常在考察一个经济体总的生产率表现时,采用的是“增加值生产函数”,即以增加值作为因变量,作为要素投入的自变量只是考察期内劳动和资本存量所提供的服务流量(primary inputs),不包括中间投入。但是,如果以部门或行业为基础考察一个经济体时,中间投入是不可以忽略的,因为正是它把各个行业和部门连接起来了。更加重要的是,生产中间投入品的行业的成本和效率会直接影响下游行业的成本和效率。这时,我们应该考察的是“总产出生产函数”,它的自变量中必须包括各个行业的中间投入(还可以进一步被分解为材料、能源、服务等等)(关于这个方法的详细讨论和对欧盟经济体的应用,参见O?Mahony and Timmer,2009)。简言之,从理论上说,在对行业或部门进行生产率分析时,除非有特别的约束,不应该采用“增加值生产函数”。
根据行业或部门之间的经济关系,单个行业或部门的TFP增长率不应该只是被理解为该行业或部门自身经济表现的结果。它实际上已经受到了其投入品生产部门TFP变化的影响。也就是说,整个经济的TFP变化应该是其内部各个行业或部门TFP变化所累积的结果。这就提出了一个不同的测算问题,即如何在加总上反映各个行业TFP变化的累积效应。多玛(Evsey Domar)回应了这个问题,提出了著名的“多玛权重”或“多玛加总方法”(Domar,1961)。这个方法后来得到查尔斯·哈尔顿(Charles Hulten,1978)的进一步证明和发展。在这个方法中,行业或部门的TFP增长率首先根据该行业或部门的总产出对整个经济体的最终需求之比进行调整,然后再相加得出整个经济体的TFP增长率。在本文中,除了对全部工业、行业以及部门分别进行单独的TFP增长率测算,我也计算了根据“多玛权重”得出的中国全部工业的TFP增长率。
关于基本数据工作
由于TFP对数据的敏感性,特别是对要素的增长率和要素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的敏感性,讨论TFP必须讨论数据问题。更加重要的是,数据处理上的透明性是澄清TFP争论的关键所在(Wu,2013a)。我所测算的行业和部门的TFP来自一个经过长期研究工作所建立起来的全新的数据库。这个数据工作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在一个经济概念、统计分类和调查覆盖前后一致的基础上,遵循分量和总量的逻辑关系,第一次完成了对年国民经济各个行业的总产值、增加值、投资额和就业量的对应。通过对官方历史数据中的各种不一致性、断裂和空白尽可能进行逻辑处理,以国民经济账户为基础,初步整合了工业部门的不同规模的企业统计,不同范畴的劳动就业统计,以及不同渠道的投资统计。虽然在数据处理上仍然存在着一些概念和实际之间的差异,但是已经基本上满足了上述理论和方法的要求。下面我选择其中重要的数据问题和相应的测算工作进行简单的介绍。
总产出、增加值和中间投入
为了说明官方数据中的问题,让我们先来观察官方数据中存在的一个严重的总量和分量的矛盾。在进行分行业分析时,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会直接采用官方分行业的工业统计数据(?还应该特别提到的是,经非官方途径流出的《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通常是包括年左右的数据)其实就是官方公开发表的分行业规模以上工业数据的来源。如果忽略这个数据库与总量经济数据的矛盾,特别是它所涉及的庞大的就业规模,以它为基础所产生的研究结论可能存在严重的问题,至少不能以它为根据对总体经济进行简单的推论。),忽略它和国民经济核算账户之间长期存在的矛盾。前者是规模以上企业汇总的数据,后者是全国总量经济的数据。在1998年实行以一定的年销售额(500万人民币)所定义的规模标准之前,还存在着所有制标准和行政管辖范围标准(乡及乡以上)。从分析的角度看,这些标准的变动使统计覆盖面出现了严重的前后不一致。以增加值为例,规模以上企业占全部工业的比重在1998年时为57%。随后,这个比重迅速提高,到了2006年时竟然等于全国工业GDP总量。虽然从2008年起工业经济统计中不再公布规模以上企业的增加值,我大致的估计显示,到2010年时,这个比值已经升至126%。这是没有逻辑的。我们可以换个角度看这个问题。在规模以上企业的增加值等于全国工业GDP总量的2006年,规模以下和不在“规模统计”范围之内的工业就业人口已经超过了6500万(Wu,2013a)。难道这些工业劳动力的产出为零吗?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说明了建立逻辑一致的分量和总量关系的重要性。
有关产出测算的数据工作,就是要在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重建国民经济账户。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首先需要对1987年开始的,每五年一次的投入产出基本表重新进行统一分类,同时,根据1987年SNA(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和MPS(Material Product System)的双系统投入产出表中提供的关系,将1981年的MPS表转换为SNA表。随后,对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值)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同样的统一分类调整。再根据这两个系统数据之间的关系,初步估计出分行业总产值和要素收入的时间序列。这样,分行业中间投入就可以由总产值减去增加值得出。最后,采用一个以“供给—使用表”为基础建立的RAS迭代方法对这个结果进行进一步调整,生成投入产出表的时间序列(Ito and Wu,2013)。在价格处理上,我采用的是官方的生产者价格指数(PPI)。这不仅由于在概念上它符合投入产出表的要求,而且同传统的“可比价格”(comparable prices,最初和MPS一起实行;其最后一期为1990年“不变价格”,一直使用到2002年)以及同国民经济账户中所隐含的工业GDP平减指数相比,PPI增长最快(Wu,2013b)。因此,采用PPI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实际产出高估的因素(关于为什么传统的“可比价格”可以导致实际产出高估的讨论,参见Maddison,1998;Ren,1997;Wu, & 2013)。
对劳动投入的测算
劳动投入是指一定时期内由劳动存量所提供的服务流量。在众多生产函数的研究中,就业的自然数量通常被直接当作劳动投入指标使用。这实际上错误地假定劳动者都是同质的,都提供同样的服务。正确地测算劳动投入涉及建立分行业基本就业人数、工作小时数、不同人力资本类型的劳动人数以及和各个类型所对应的劳动报酬等一系列数据工作。从官方劳动统计的质量来看,这样的数据要求面临严峻的挑战。官方劳动统计不但存在概念、分类、覆盖上的严重不一致,也存在分量同总量的严重矛盾(参见Yue,2006;Wu and Yue,2011;Wu,2013a)。
我们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也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全部经济分行业就业的自然人数和投入产出账户的完全对应问题,或者说,是重建劳动账户和生产账户的逻辑关系问题。其中一个难点是如何将统计系统所覆盖的、分行业就业以外的一个(巨大的)余量,合理地分配到行业中去。解决这个问题主要依靠各次普查和调查提供的信息,以及对这部分劳动力的职业和技术性质的判断,即他们主要在小微企业和非正式部门中从事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工作。在这个基础上,同样依靠各次普查和调查的数据,我们初步完成了在行业层面上从就业人数到工作小时数的转换,解决了自然人数的劳动时间不一致问题(详见Wu and Yue,2011;Wu and Zhang,2013)。这部分工作的结果产生了分行业就业人数和工作小时的时间序列数据。
我们面对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自然人数或自然工作小时的不同质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对就业人数以及工作小时按照不同的人力资本类型进行分类,这包括2个性别组、7个年龄组、5个受教育年限组和24个工业行业的交叉分类(也尝试过职业组别和所有制组别的分类,详细内容参见Wu and Yue,2011)。这个工作的第一步是对几个时间点建立四维的数量矩阵(?分别为就业人数和工作小时数量矩阵),然后再建立和数量矩阵一一对应的报酬矩阵。这其中还要经过从边际矩阵到全维矩阵的逼近过程(从边际矩阵的建立到实现从边际矩阵到全维矩阵的逼近,我们采用的是iterative proportional filling (简称IPF)方法。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Bishop、Fienberg and Holland(1975)。)。建立报酬矩阵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数量矩阵的权重问题。这样做的一个较强的假定是,不同类型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等于他们的边际产出(由于市场扭曲,这肯定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根据这两个矩阵,就可以对不同类型劳动者进行同质化处理。这样测算的劳动投入是以生产者付出的劳动成本为基础的(Jorgenson、Gollop and Fraumeni,1987;Chinloy,1980)。
根据数据条件,我采用的基准年份为1982年、1987年、1990年、1995年、2000年、2005年和2010年。基本数据来自各次人口普查和1%人口调查数据,CHIP(China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住户抽样调查数据(CHIP1988,CHIP1995,CHIP2002),2005年1%人口调查大样本数据,以及RUMIC(中国农民工调查)2002数据(Wu and Yue,2011;Wu、Yue and Zhang,2013)。还应该提到的是,在这个测算过程中,投入产出表中的分行业劳动收入总量成为建立报酬矩阵时采用的控制总量。我们最后的问题相对简单,就是把重建的就业人数和工作小时时间序列,同基准年全维的数量矩阵和报酬矩阵相结合,生成一个完整的中国工业劳动投入数据库。
对资本投入的测算
资本投入是指一定时期内由生产性固定资本存量所提供的服务流量。由于数据的限制,资本存量通常被直接当作资本服务指标使用。这既没有考虑不同类型固定资本的异质性,也没有考虑资本的机会成本。正确测算资本投入涉及两个工作。第一步是采用永续盘存法(perpetual inventory method,简称PIM)建立分行业分类型的资本存量。基本数据要求包括分行业分类型的固定资产投资时间序列、价格指数以及资本消耗系数(折旧率)。此外,根据PIM的要求还需要估计初始资本存量。第二步的工作相对简单,是对分行业分类型的资本存量通过生产者成本进行加权,建立资本服务流量指标。下面的介绍集中在第一步工作上。
可以从官方统计上得到的数据很难满足我们的要求。国民经济账户中的固定资本形成(简称GFCF)指标只是个总量概念,缺乏行业层面的分量。官方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提供分行业以及分部门固定资产投资数据,但是在概念、分类、覆盖上存在很多问题。只举一个通常被忽视的问题为例,如果比较TIFA(total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GFCF这两个指标,会发现从2002年以后,前者逐渐超过后者,而且越来越严重,到了2010年前者对后者之比已经达到了1?5!这是因为TIFA重复计算了投资时所购买的旧资产价值。迅速上升的土地交易是造成TIFA膨胀的重要原因。再有,GFCF和TIFA都是以“工作量”记录的,当年的“工作量”并不能全部建成并进入生产过程。如果忽略这些问题,直接使用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肯定会产生错误的结果。
上面谈的投资或资本形成数据都是流量数据。官方的工业统计也对规模以上企业提供了几个存量指标,如年末固定资产原值、净值、折旧等等。这些存量指标的好处是不存在未完成的“工作量”问题。但是,这些存量指标是对不同价格的投资进行加总的结果,是基于投资的历史成本建立的,无法用来进行经济分析。同时,由于在行业层面上它所覆盖的只是规模以上企业,和前面讨论的就业统计问题的性质一样,不仅有分量和总量的不一致问题,也有复杂的余量问题。
由于中国的投入产出系统还没有包括对应的资本矩阵,所以测算资本存量的困难很大。一个时刻需要考虑和检查的问题,还是分量和总量的潜在平衡问题。建立存量的整个工作分别从两个方向进行,一是自下而上,从可以掌握的行业数据逐步整理、测算、加总;二是自上而下,从整理、测算总量入手,检查与行业数据的衔接问题。首先,官方的存量数据需要被重新分解为流量(其中需要估计潜在的核销或报废函数)。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价格平减和折旧。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的价格指数,是根据财政部一个资产调查和投资品生产部门的PPI建立的。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的资本消耗系数,是在官方会计准则要求的分类型资产服务年限的基础上,采用市场经济条件下分类型资产退役时的残值模型推导的(参见Hulten and Wykoff,1981)。PIM要求的初始资本存量在年全国资产普查的基础上建立,同时参考了根据新古典增长经济学的稳态经济模型估计的结果,也参考了其他研究者的工作(参见Wu,a & 2013b)。
在得到了以PIM估计的分行业实际资本存量结果之后,存量的工作还没有完成,因为行业层面的数据只能覆盖规模以上企业。所以我们还有两个工作:一是根据行业间相对的资本—产出比(K/Y)和资本—劳动比(K/L)检查这个结果是否可以接受;一是根据对规模以上企业统计中相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的K/Y和K/L的观察,参考(不系统的)分行业规模以下企业的相关指标,建立对规模以下和“规模标准以外”企业的K/Y和K/L 假定,在此基础上对“余量”进行行业分配。这个“余量”是根据GFCF建立的总体经济的资本存量和根据规模以上企业分行业存量推算出来的(Wu,2013a,2013b) (?因为存在严重的重复计算问题,我们放弃了对TIFA的工作,在总量上接受了GFCF。但在GFCF中剔除了作为非生产性资产处理的居民住宅投资。)。
在这样建立的资本存量的基础上,根据估计的生产者成本(user cost of capi?tal),就可以对不同类型的生产性资产进行加权,从而建立资本投入指标(即资本服务流量)。请注意,和前面提到的国民经济的生产、收入、使用(支出)一致的原则相关,我们测算生产者成本中所使用的资本报酬也来自我们重建的国民经济账户。由于篇幅所限,略去有关这部分的介绍。
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结果
在这样一系列的数据工作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进行对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在行业分类上,我们有24个行业。这个分类基本上是在中国国家产业分类标准的I级分类基础上进行的,大致符合国际两位码产业分类标准。为了排除一些特殊或性质不清楚的“行业”的干扰,计算中排除了烟草、木材加工和其他制造业三个行业。这样,总共用于分析的21个行业按照各自在产业链中的性质分别组成了三个工业分部门:能源工业、基础材料工业、成品及半成品制造业(?“能源工业”包括煤炭开采、石油及天然气、炼油炼焦及核能以及电力热力和煤气共4个行业;“基础材料工业”包括金属矿、非金属矿、纺织、造纸、化工原料、建筑材料以及金属冶炼和压延一共7个行业;“成品和半成品”包括食品、服装、皮革、橡胶和塑料、金属制品、通用和专用设备、电气设备、电子通信设备、仪器仪表以及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一共10个行业。这总共21个行业组成了调整后的全部工业。)。这个进一步的分组,目的是将处在上游的能源工业和基础材料工业与处在下游的成品及半成品制造业分开。因为前者被认为具有“战略意义”而被国有企业所垄断,而民营和外资企业多集中于后者。这样的分组便于(间接)观察制度因素是否会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表现。
表1报告了全部工业和三个分部门的总产出增长核算的结果。其中的要素和中间投入的年增长率是根据各自在总产出中的份额加权后的结果。如果从总产出的年增长率中减去各个投入的加权年增长率之和,就可以得到TFP的年增长率。表1也给出了部门间TFP的累积效果,即多玛加总方法得出的TFP 。
应该说,这个结果是在一系列严格测算投入和产出指标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改革30年中一直作为高速增长引擎的中国工业,所作出的有关全要素生产率表现的一个深刻总结。可我们并没有看到一份出色的TFP答卷。从1980年到2010年,整体工业的TFP年增长率只有0?5%,如果考虑部门间的累积效果,也不过是1?1% 。根据工业部门在经济起飞阶段的重要性,这基本上可以代表整个经济的TFP增长率。这个结果远不如处在相似阶段的东亚经济体的TFP表现。根据美国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The Conference Board,2012)以1990年PPP测算的结果(1990年不变价格),中国的人均GDP从1990年代初的2000美元增至2010年代初的6500美元,这基本上相当于日本的年,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年期间人均GDP的变化。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大致可比的基础上观察各个经济体的TFP表现。
表1中国全部工业及主要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增长率,以及加权后的要素和中间投入年
增长率(年百分比)
注:关于部门分组参见第11页脚注①。资本、劳动和中间投入的增长率是根据各自在总产出中的份额得出的加权增长率。“多玛”指采用多玛权重测算的累积TFP效果。
资料来源:作者估计
在下面的比较中,由于其他研究没有考虑部门间TFP的累积效果,我们只集中在总体经济的TFP上。首先可以把表1的结果进行整理,得出中国工业在年期间的TFP年增长率为1?2%。麦迪森(Maddison,1995)估计日本在年期间整体经济的TFP年增长率为5.1%,沃尔夫(Wolff,1996)把这个时期从1960年分成了两段,发现前一段是4?9%,后一段是4?0%,而包斯沃思等人(Bosworth,1995)的研究也发现日本在年期间的TFP年增长率是5.0%。就是说,在类似的发展阶段上,日本在技术进步和效率改善方面的速度几乎是中国的4倍。
对同样发展阶段上,即年期间韩国和台湾地区的TFP表现,研究者们有一定的争议,但是实证结果显示它们的TFP增长还是快于中国。河井啓希(Kawai,1994)的研究表明台湾地区在年期间TFP的年增长率达到了4?5%左右(其中年为5?1%,年为3.9%),但是杨格(Young,1995)的研究结果只是2.6%(年),包斯沃思等人(1995)的结果还要低些,只有2%左右。韩国的TFP增长表现比台湾较差。河井啓希(1994)的结果显示在期间韩国的TFP年增长率只有0.7%,但是在期间达到了2?8%,平均起来大致在1.7%。这同杨格(1995)针对年期间的测算结果几乎一致。包斯沃思等人(1995)对韩国这个时期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TFP结果(大致在2%)。但是,杨格(1995)发现同一时期韩国和台湾制造业的TFP年增长率分别达到了3%和1.7%(?如果和前面提到的杨格对台湾总体经济TFP测算联系起来,可以推算台湾非制造业的TFP增长要更快。),相比较,中国的成品及半成品制造业在年的TFP年增长率只有1%(这里,为了和杨格的方法一致,没有采用“多玛权重”)。
根据表1,我们还可以分阶段来看中国工业TFP的表现。与很多早期的研究不同,工业改革初期(年)并没有对整个工业经济产生明显的TFP效果。特别是,在这期间,能源工业和基础材料工业分别经历了每年4?9%和0?8%的下降。由于这些上游部门效率表现的逐年恶化,以多玛权重测算的整体工业的TFP表现是恶化的,以每年2?0%的速度下降。但是还应该看到,产品和半成品制造业部门在此期间每年有1?4%的TFP增长。应该说,在这个时期开始的一系列改革,如价格双轨制和利改税等,对这个有着相对比较优势的部门的效率改善还是起到了正面作用。
表1显示,中国工业经济TFP表现最好的时期是年,TFP的年增长率达到1?5%,而根据部门间累积效果估计的TFP年增长率达到了5?0%。这是从邓小平南方讲话起到中国进入WTO前夕的10年,其中前半段经历了经济过热,后半段经历了从亚洲经济危机开始的长通缩期。更加重要的是,这个时期也是工业改革的全面深入时期,特别是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在这个改革的环境下,同时受到产能过剩和需求下降双重压力的企业,实际上被逼上了效率改善之路。我们的测算结果给这个判断提供了最好的支持。这个时期不仅是成品和半成品部门TFP增长最快的时期(2?0%),也是基础材料部门TFP增长最快的时期(1?7%)。同时,能源部门TFP下降的速度也从上个时期惊人的4?9%,缩减为1?0%。
从进入WTO之后一直到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前,即年期间,是改革后第二个TFP表现最好的时期,但是总体来看TFP增长的势头和上个时期相比在减弱(从1?5%降到了1?2%)。还应该注意的是,与这个时期成品和半成品制造部门的超高速产出增长(21%!)相伴随的是中间投入更快的增长,从上个时期的11?4%提高到了17?2%!由于生产中间投入产品的上游部门的生产率表现并不好,能源工业还是停留在负增长区,基础材料工业TFP增长的速度还不及上个时期的一半,结果是部门间累积的TFP年增长率从上个时期的5%下降到了2?3%。我的理解是,这个由WTO带来的,由发达经济体市场所支持的超高速增长,减少了改革的压力。政府收入的迅速上升使其对“战略部门”的支持能力大大增加,开始出现国进民退的现象。再有,这个时期也是地方政府的GDP竞争进入白热化的时期。这些应该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个时期的TFP增势减弱了。在这个时期之后,也就是从全球经济危机开始的3年(年),伴随政府“4万亿”之巨的资金注入的却是TFP的普遍恶化。我们的结果表明,这个时期总体工业的TFP年增长率只有微不足道的0?3%,部门间累积的TFP增长率以每年2?3%的速度下降,这是30年中最差的情况。
根据结果,我们进一步在图1中绘出了以1980年为基期的全部工业和这三个主要部门的TFP指数()。如图1(B)所显示的,一直到1990年代中期能源工业部门的TFP都是持续下降的,此后就是长达15年之久的停滞。让我们吃惊的是,到2010年时它一直仅仅停留在1980年水平的50%左右。从这个角度观察,完全可以判断这个由国有企业垄断的部门,在过去的15年中,几乎没有实施什么可以导致效率提高的改革。基础材料工业部门的TFP增长在中国加入WTO后也陷入了停滞。到2010年,它的TFP水平只比其1980年水平高出大约10%。我们知道,这个部门中的很多大型企业也是国有企业,或者严重受到政府干预的非国有企业。如图1(A)所示,这两个上游部门的表现不但在1990年代对总体工业的效率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也在中国加入WTO之后阻碍了总体工业TFP的改善。相比之下,成品和半成品制造业部门的TFP基本上是持续改进的,虽然其速度在中国加入WTO后也放慢了。这些上下游部门之间在TFP表现上的反差,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个部门间TFP的反差,阻碍了中国工业TFP的提高?
图1中国全部工业及主要部门全要素生产率指数
解读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
我认为,上下游部门之间在TFP增长率上如此大的反差,反映了中国经济中的一个复杂的“交叉补贴”现象。这个“交叉补贴”是理解中国工业TFP动态表现的关键所在。我们可以根据上一节对各工业部门TFP的观察,深入思考其中的问题。一方面,如此长期低效率的上游部门,特别是能源部门,很难在真正的市场条件下生存。另一方面,低效率的上游部门也很难降低成本,从而很难降低成品和半成品制造业所需要的中间投入的价格。那么,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下游部门还能够维持相对较快的TFP增长?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其中政府的作用。首先,改革开放以来利用市场和发挥比较优势所得到的好处,使政府不会完全重复计划经济时期的错误。直接面对国际市场竞争的成品和半成品部门中的多数行业,体现了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是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但是,希望以更快的速度实现赶超,以及保护自身各种利益的需要,又使得政府坚持对“战略部门”或“国民经济命脉产业”的保护——对国有企业改革时提出的“抓大放小”原则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为了支持战略性的上游部门,政府需要一个不断提高收入能力的下游部门。而为了维持下游部门的竞争性,政府也需要保证上游部门对下游部门的支持。这种相互支持的本质就是“交叉补贴”。图2解释了这个“交叉补贴假说”。
在图2中,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假设了一个没有非工业部门的经济。引入非工业部门除了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外,不会改变问题的性质。从政府开始的深灰色箭头代表这个“交叉补贴”的“初始点”,即政府以补贴保持着对能源部门的支持。循着深灰色箭头,能源部门进一步为基础材料部门和成品及半成品制造业部门提供含有补贴的能源。同时,基础材料部门也为成品及半成品部门提供含有补贴的中间投入。结果是,如浅灰色箭头所示,成品及半成品部门可以提供更多的作为公共资源的收入,后者遂成为政府补贴的来源。图2说明,最主要的收入来自下游部门。图2还显示,由于政府的影响,所有的部门也受惠于由于制度原因而造成的未被充分支付的要素成本(包括劳动、资本、土地和环境)。这些成本实际上是对未来的透支。
不难看出,要想维持这个“交叉补贴”中的循环,关键在于提高成品及半成品部门创造收入的能力,也就是该部门需要保持强劲的增长和持续的生产率改善。如果TFP增长放慢,那就需要该部门以更快的产出增长弥补因效率下降而引起的收入下降,但是这样做的前提是需要更高的成本补贴以维持生产的竞争力。显然,这是不可持续的。TFP是任何一个经济体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素。经济史表明,它只能源自私人企业家为利润所驱动的、经久不息地追求技术创新和效率改善的活动。这种“交叉补贴”最终是“作茧自缚”。因为它会扭曲所有生产者的动机和行为,不管他们在哪个部门,不管他们接受多少补贴,也不管他们是直接还是间接地接受补贴。最终,大家都会失去追求技术创新和效率改善的动力,都会变成行为不端的“坏孩子”。
从单位产出劳动成本变化观察“交叉补贴”
我们前面报告的生产率结果,特别是图1(A)关于上下游部门长期TFP动态的比较,已经清楚地支持了这个“交叉补贴假说”。在这一节,我们可以从各个部门“单位产出平均劳动成本”的变化来进一步观察这个“交叉补贴”。
单位产出平均劳动成本是平均劳动报酬(Average Labor Compensation,简称ALC)和平均劳动产出(Average Labor Productivity,简称ALP)之间的关系,即ALC/ALP。ULC变化的经济意义在于,以不变价计算的平均劳动产出的增长是否可以抵偿名义劳动成本的上升。换句话说,我们是否需要支付一个越来越高的货币劳动成本去购买同样一个单位的真实产出。这个关系还可以间接地反映资本投入的效率,即劳均资本存量(K/L)的增加或资本深化(这是中国经济在过去至少20年中所经历的非常重要的发展过程),是否可以带来一个能够抵偿劳动成本上升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为了反映这个动态关系,表2列出了ULC以及它的两个因子ALC和ALP在不同时期的年平均增长率。在一个近似的意义上,ULC的变化可以被视为ALC变化对ALP变化之差。
让我们来观察表2。整个工业的情况在改革初期的10年(年)并不好。由于上游部门很差的表现,平均工业劳动生产率(ALP)出现了负增长。平均劳动报酬(ALC)的增长上升很快,基本上是补偿性的上升。所谓补偿是指对计划经济时期长期压抑的、没有被充分支付的劳动成本的补偿。结果是,这个时期单位产出劳动成本(ULC)的上升速度是30年中最快的(这个过程也延续到下一个10年中)。原因很明显,能源部门的ALC在其ALP以每年7?7%的速度下降的同时,也以每年7%的速度上升。基础材料部门ALC的上升速度竟然是其ALP上升速度的3倍以上。相比之下,虽然成品和半成品部门的ALC上升最快(13?3%),但是和其最好的ALP表现(10?2%)相比较还是匹配的。
在年这个时期是平均劳动报酬增长最快的时期。从整个工业来看,ALC竟以每年24?5%的速度上升。而且这样的增长速度在各个工业部门几乎一致,明显呈现出十分强烈的攀比性。但是,劳动生产率的表现在各个部门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劳动生产率是不可以攀比的。应该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基础材料工业,和成品及半成品制造业一样,经历了30年中最快的ALP增长(12?6%),基本上接近成品及半成品部门的ALP增长速度(13?8%)。我认为,ALP在两个部门的超常表现基本上属于一次性的“制度红利”性质,即改革对效率的释放。不要忘记,这个时期对国有企业来说是改革压力最大的时期。最差的还是受到保护的能源工业部门的ALP增长,每年仅有2?9%。然而。反映在ULC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期的成本上升压力几乎和上个时期相同。就是拿出表现最好的成品及半成品部门来观察,它的ULC每年还是要上升8?9%,以这样的结果来看,这个时期的出口部门(以成品及半成品制造业为主)还谈不上什么真正的竞争力(除非存在某种补贴)。
从中国加入WTO一直到全球金融和2007年经济危机之前的6年是中国工业竞争力持续上升的时期。成品及半成品部门和基础材料部门的ALP年增长率保持在9%左右。前者的ALC上升速度只有5?9%,后者的ALC上升速度为7?5%。结果,这两个部门都出现了非常有利的ULC下降,其中直接面对国际市场竞争的成品及半成品部门以每年2?5%的速度下降,而基础材料部门也以1?5%的速度下降。这使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在短期内迅速得到大幅度提升。这看来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迅速崛起为“世界工厂”。然而,中国经济崛起的故事并非如此简单。我们不可以忘记能源部门(当然也有某些基础材料行业)。它的ALP增长速度(3?4%)远远落后于其ALC上升速度(12%),
结果是它的劳动成本以每年8?3%的速度在上升,但是,它给下游部门提供的燃油、电力、煤气和水的价格远远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就是说它一直在补贴着下游部门。
图3所绘出的各个工业部门以1992年为基期的ULC指数,在低效率高成本的能源工业部门和高效率低成本的成品及半成品制造业之间,给出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它似乎在告诉我们,高效率的下游部门有着惊人的消化上游部门高成本的能力。然而,我的解读是,像能源工业这样的低效率高成本的上游部门之所以能生存,肯定受惠于一个来自下游高效率低成本部门的巨额“补贴”。而这个因“补贴”得到发展的能源工业部门,反过来又可以“补贴”下游工业部门,从而提高它们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政府显然是这个“交叉补贴”的始作俑者。它产生于政府的能源和相关的产业政策,比如对能源生产者和能源使用大户的各种补贴政策,以保证对这样一个低效率高成本的能源工业和其他相关工业部门的持续不断的资源投入。
2008年开始,随着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爆发,以及随后发达经济体极
其缓慢的复苏,中国工业面对着萎靡不振的国际市场需求。通常的规律是,经济衰退中的劳动报酬会下降而不是上升。从表2看,让人费解的是,在所有工业部门劳动报酬却出现了这30年中的第二次迅速上升,高达每年19%!结果导致总体竞争力的急剧下降(ULC由年的每年0?1%攀升到这个时期每年的9?6%!)。最差的还是能源部门。它的ALP年增长率只有2?4%,远远低于成品及半成品部门的11?7%和基础材料部门的8?5%。这样,它的劳动成本以每年16?4%的速度攀升,远远超过成品及半成品部门的7%和基础材料部门的9?7%。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旨在解救经济危机的巨额财政投入对劳动成本的推动效果,已经远远超过其劳动生产率效果。可是,近来的一系列迹象表明,这个趋势根本不会很快得到扭转。下面,为了在行业层面上进一步显示我们上面所观察到的现象后面的行业细节,图4比较了成品及半成品制造业内部各个行业在危机前后的ULC变化。可以明显地看到,没有一个成品及半成品部门中的行业可以在危机后避免ULC的上升。这里,还有一个更应该引起注意的现象是,即使在危机之前的年期间,中国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如橡胶塑料、皮革皮毛、服装鞋帽、食品等,并没有出现明显的ULC下降。我们的问题是,随着中国经济中一些最有比较优势、最有竞争力的行业的成本上升,这个“交叉补贴”还可以维持多久?
资料来源:作者估计,有关解释请参考正文
从资本边际生产率观察“交叉补贴”
前面简单地提到资本投入效率的重要性。既然中国的经济增长有着粗放的靠投资投入推动的特点,我们就应该更加关心资本深化和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即劳均资本存量的增加是否可以带来足够快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以抵偿劳动成本的上升。现在让我们换一个角度,观察资本的回报率。我们采用资本边际产出(Marginal Product of Capital,简称MPK)来测算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的回报率”。它的含义是,在其他投入不变的情况下,新增加一个单位的资本净存量可以引致多少实际产出(增加值)的增长。这里,“产出”概念是国民经济核算中增加值的概念,它既包括资本的税前收入,又包括对资本消耗的补偿。必须指出的是,MPK概念仍然是以竞争性市场假设为前提的。但是,由于我直接采用了国民收入账户中的资本报酬进行测算,结果应该能够在相当程度上纠正它的假定条件,揭示中国工业经济中的效率问题。
经济增长依赖于投资的增长。经济发展史显示了一个一般的规律。那就是,从经济发展初期开始,到基本完成工业化,一个经济体的资本—产出比(K/Y)大致会从1上升到3左右或更高的水平。就是说,在这个工业化的过程中,生产同样一个单位的产出(GDP),需要越来越多的资本投入。根据定义,MPK是资本收入份额调整后的K/Y的倒数。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国民生产总值中资本的收入份额会随着K/Y上升而下降,大致从60%或更高水平降至30%或更低的水平。与此同时,MPK也随之下降,大致会从0?7或更高降至0?1左右。这是对整个经济而言的。对一个成熟经济中的工业部门,特别是其中的制造业来说,其MPK应该会维持在0?5左右。这样的工业部门处在世界技术前沿上,有很高的附加值。一般说来,发展过程越是粗放,MPK的下降速度就会越快。这个情况通常在工业化后期得到改变。这是由于整个经济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而生存下来的制造业不得不向以研发、创新为基础的高附加值生产升级。这样MPK的下降会放缓、停止,甚至缓慢回升。
这里,我们实际上涉及经济学的一个定理,那就是“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即在现有技术水平条件下,投资增长将会不可避免地进入一个资本边际产出递减的过程。显然,我们希望这个过程越慢越好。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可以减缓,甚至短期内逆转这个过程。卢卡斯和罗默(Robert Lucas and Paul Romer)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则认为,投资增长所推动的人力资本投资、新资本对旧资本的替代和“干中学效应”等因素,可以克服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规律。然而,这是否可以实现还要取决于一个经济体的制度条件。所以,从效率问题引伸到制度问题绝不是牵强附会。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是严重的资源错配问题。它是和不公平竞争、要素价格扭曲以及各种形式的补贴联系在一起的。
在图5中,我们绘出了改革30年以来中国主要工业部门的MPK变动趋势。总体而言,整个工业MPK的下降趋势,似乎因为1990年代中期的国有企业重组和改革而得到扭转,但是又因2008年的危机而中断了。我们更感兴趣的是部门之间MPK的相对表现。1990年代中后期至本世纪2000年代中期的MPK回升,主要由成品及半成品部门支撑。基础材料工业在90年代中后期也出现了MPK回升,但是幅度远小于成品及半成品部门,而且很快进入了颓势。问题最大的还是能源工业部门,它已经在0?1这样极低的MPK水平上维持了15年,而且随着2008年的金融危机,进一步降到了0?05左右。这更支持了我上面的“交叉补贴假说”。显然,在这里,资本回报率不可能是政府能源政策的基础。尽管因巨量低效率的投资所造成的过低的“资本回报率”,上游工业部门却一直得到不断的扩张,其目的是支持下游的、主要以出口为导向的成品及半成品部门的“利润”。
综合各个部门,考虑到它们之间的上下游关系,整个情况让人无法乐观。实际上,从2005年左右开始,出口导向的成品及半成品制造业部门的MPK出现了迅速的下滑。而且,和其他部门对危机的反应不同,2008年危机对这个部门的影响近乎是崩溃性的。当然,我们目前的分析还没有能够包括进2010年以后的情况,所以上面的结论可能还为时过早。但是,指望会在短期内由图5所示的趋势出现戏剧性的大逆转,肯定是过于天真的。如果不能通过彻底的改革来改变上游部门的投资和资本利用效率,那么,要么是增长不会在目前的速度上持续下去,要么就是因强行维持目前的增长速度而导致MPK趋势进一步恶化。
简短结语:中国工业向何处去?
我们在本文所观察和讨论的中国工业经济TFP、ULC以及MPK的表现,很清楚地说明了在现有的发展模式下,中国经济已经接近了其增长的极限。由于制度的问题,中国经济实际上是以低效率的方式复制了战后“东亚经济奇迹”。所以,我们对未来增长潜力的理解,绝不能建立在维持现有体制和结构的前提下,不能仅仅根据中国经济和发达经济体之间的人均GDP差距而简单地得出结论,也不应该简单地借鉴尚没有系统经济理论支持的、只依靠实证观察所发现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而开药方。有关增长潜力的更加科学和有说服力的判断,只应该建立在以行业层面生产函数分析为基础的,对全要素生产率和要素成本分析的基础上。
要解决中国经济的深层问题,尽快实现增长模式的转变,关键还是在于政府能否转变职能,从竞争性的经济活动中退出来。我们需要一个“经济利益中性”的政府。它应该做的就是不断地维护和完善市场经济制度,而不应该试图以各种理由干预市场运作。任何以国家利益为理由的政府干预必须要有清晰的界定,必须通过有公众参与的听证程序,而且,由此产生的经济活动的性质应该明确属于公共产品或服务的生产。大量事实说明,依赖各种形式的补贴,通过政策鼓励和廉价信贷,支持大型国有企业在所谓战略性产业中的发展,得到的是增长率,损失的是效率。地方政府之间锦标赛式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战略性研发投资亦如此。它一是离不开粗放式发展的性质,二是离不开扭曲的激励机制,因此也必然导致低效率。所以,我们必须警惕那些主张应由政府出面进行结构调整的观点。试图再用政府干预来解决曾由政府过度干预所造成的问题,最终只能使问题更加恶化。
最后,我想再次强调在经济增长和生产率研究中,以正确的经济理论和方法指导数据工作的重要性。这是由于TFP的结果对数据非常敏感。它要求我们必须严肃对待要素的同质化处理,要素增长率的测算,以及在国民收入中的要素份额的测算。同时,应该保证数据处理上的透明性和研究结束时的数据可得性。只有这样的透明性和可得性,才可以保证科学验证的可重复性,因此才可以澄清有关TFP测算中的问题,进而有助于在关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争论中达成有利于政策调整的共识。我认为,这才应该是我们这些从经济改革中成长起来的经济学家的职业责任和历史责任。■
主要参考文献(请向《比较》编辑室索取完整文献目录:bijiao@citicpub?com)
Bishop,Yvonne M?M?,Stephen E?Fienberg,and Paul M?Holland(1975),Discrete Multivariate Analysis,Cambridge,MA: MIT Press?
Bosworth,B?P?,S?Collins,and Y?C?Chen(1995)?Accounting for Differences in Economic Growth?Brookings Discussions Paper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No?115(October)?The BrookingsInstitution,Washington D?C?
Chinloy,Peter T?,1980,“Sources of Quality Change in Labor Input”,America Economic Review 70 \[1\],108-19?
Domar,Evsey(1961),“On the Measurement of Technological Change”,Economic Journal 71?
Felipe,Jesus,1999,“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 in East Asia: A Critical Survey”,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35(4),pp?1-41?
Huang,Yiping and Kunyu Tao(2010),“Factor Market Distortion and the Current Account Surplus in China”,Asian Economic Papers,9(3)?
Hulten,Charles(1978),“Growth Accounting with Intermediate Inputs”,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45?
Hulten,Charles R?,and Frank C?Wykoff(1981),“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depreciation”,in Charles R?Hulten(ed?),Depreciation,Inflation,and the Taxation of Income from Capital,81-125,The Urban Institute Press,Washington D?C?
Ito,Keiko and Harry X Wu(2013)“Construction of China?s Input-Output Table Time Series for : A Supply-Use Table Approach”,presented at the 2nd Asia KLEMS Conference,Bank of Korea,Seoul,August 22-23,2013?
Jorgenson,Dale W?(1990),“Productivity and Economic Growth”,in Ernst R?Berndt and Jack E?Triplett(eds?),Fifty Years of Economic Measurement-The Jubilee of the Conference on Research in Income and Wealth,Volume 54,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Jorgenson,Dale W?,Frank Gollop and Barbara Fraumeni(1987),Productivity and U?S?Economic Growth,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
Kawai,Hiroki(1994),“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Economic Growth?” The Developing EconomiesXXXII:373-97?
Maddison,Angus(1995),Monitoring the World Economy ?Paris: OECD Development Centre Studies?
O?Mahony,Mary and Marcel P?Timmer(2009),Output,Input and Productivity Measures at the Industry Level: The EU KLEMS Database,Economic Journal,119(June),F374-F403?
Solow,Robert M(1957)?“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39(3): 312-320?
Wu,Harry X?(2008),Measuring capital input in Chinese industry and implications for china?s industrial productivity performance,,presented at the World Congress on National Account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Measures for Nations,Washington D?C?
Wu,Harry X?(2013a)“China?s Growth and Productivity Performance Debate Revisited”,Working Paper Series,The Conference Board,New York?
Wu,Harry X?(2013b)“Accounting for Productivty Growth in Chinese Industry-Towards the KLEMS Approach”,presented at the 2nd Asia KLEMS Conference,Bank of Korea,Seoul,August 22-23,2013?
Wu,Harry X?and Ximing Yue(2012),Accounting for Labor Input in Chinese Industry,,RIETI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Japan),12-E-065?
Young,Alwyn(1995)?“The Tyranny of Numbers:Confronting the Statistical Realities of the East Asian Growth Experience?”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August:641-80?
更正声明
《比较67》上《多重金融监管工具的综合分析框架》一文,周叶菁译,廖岷校,由于编辑疏忽,遗漏了译者姓名,特此更正并向译者致歉。
《比较》编辑部
作者现为日本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兼美国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TCB)高级研究员及TCB中国中心研究部主任。本文中的一部分基于作者在博源基金会成立五周年学术论坛发言稿而整理。这里报告的有关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的结果曾经在法国Clermont Ferrand举行的第九届CERDI中国经济国际会议,和在首尔举行的第二届亚洲生产率(KLEMS)大会上进行了讨论。感谢RIETI-IER的CIP项目以及TCB中国中心对部分数据工作的支持,也感谢香港特区政府UGC/CERG(BQ-293;BQ-907)对前期基础数据工作所提供的支持。文责自负。&
版面编辑:王影
财新传媒版权所有。如需刊登转载请点击右侧按钮,提交相关信息。经确认即可刊登转载。
苹果客户端
安卓客户端
caixinenergy
caixin-enjoy
caixin-life
全站点击排行榜
全站评论排行榜
热词推荐:}
 下载
 收藏
请您下载后勿作商用,只可学习交流使用。 本人如有侵犯作者权益,请作者联系本人删除
 下载此文档
正在努力加载中...
中国工业生产率与增长听研究
下载积分:1250
内容提示:中国工业生产率与增长听研究
文档格式:PDF|
浏览次数:1|
上传日期: 14:24:50|
文档星级:
全文阅读已结束,如果下载本文需要使用
 1250 积分
下载此文档
该用户还上传了这些文档
中国工业生产率与增长听研究
官方公共微信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区域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及其结构变动研究;作者:付联志尚昱吟;来源:《中国集体经济》2014年第01期;摘要:运用空间计量分析技术,本文考察了1988~;关键词:就业结构;全要素生产率;空间面板;一、引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相比第二产业;二、研究方法及数据处理;(一)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对
龙源期刊网 .cn
区域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及其结构变动研究
作者:付联志 尚昱吟
来源:《中国集体经济》2014年第01期
摘要:运用空间计量分析技术,本文考察了年中国大陆28个省级就业结构转变和区域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我国区域工业就业结构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性,相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和资本产出比的提高会降低产业的就业份额。人均收入的提高对产业就业份额的影响可正可负。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动未必同步。提高制造业的就业份额关键在于空间效应的提高。
关键词:就业结构;全要素生产率;空间面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相比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持续降低,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增长速度最快,但是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是较低的,产业结构偏离度过大。有学者认为应该采取一定的措施来纠偏,但就业结构一定与产业结构同步吗?是什么让劳动力在不同的产业之间进行流动?这种流动是否会受到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迄今为止,我们对区域之间的这种空间溢出作用的强度和作用范围的实证研究依然有限。
二、研究方法及数据处理
(一)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
对生产率进行测量是为了辨别产出差异当中那些不能被投入差异解释的部分。相同的企业生产相同的产品,如果投入越少,我们就说其生产率越高。为了使生产率得以提高,我们需要观测并控制应用于投入和产出的技术水平。如果企业之间的技术水平发生变化、规模经济不变,首选的方法是数据包络分析(DEA)。运用DEA模型时,我们不需要设定具体的生产函数,还允许企业间技术异质的存在。
Malmquist指数被应用于生产效率的测算并依据效率测算的结果进行比较研究。我们将每个省区作为一个决策单元,在一定时期内,投入函数为xk,t=(Xk),产出函数为yk,t=(Yk),k代表我国各省区。我们从产出角度来运用非参数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构造t时期的不变规模报酬,即
Ltc={(xt,yt):∑28k=1zkytk≥yt;∑28k=1zk
xtk≤xt;zk≥0;k=1,......,28}(1)
三亿文库包含各类专业文献、中学教育、文学作品欣赏、各类资格考试、外语学习资料、18区域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及其结构变动研究等内容。
性距离函数和 Malmquist-Luenberger 生产率指数法,测算环境约束下 长三角地区工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并比较不考虑环境因素影响情形下的工业全要素 生产率增长... 工业 化率、 城市化率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是正向的相关关系, 我国的经济转型在...相应地,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提出对我国经济增长 质量问题进行研究的... 非参数DEA下中国区域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和环境绩效的测度_兵器/核科学_工程科技_专业资料 暂无评价|0人阅读|0次下载|举报文档 非参数DEA下中国区域工业全要素生产率... 环境管制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APEC 的实证研究* 王...工业化水平、技术无效 率水平、 劳均资本、 人均...气候变化问题 通过一份宣言,确定了降低亚太地区能源... 年16个地区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变化和技术...Upadhyay(2000)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样本,研究了...的方法发现地区 工业化和城市化能够显著促进生产率... 湖南省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测度与分析研究_兵器/核科学_工程科技_专业资料。湖南省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测度与分析研究 摘要:运用湖南省工业 1994 年到 2006 年的统计年鉴... Malmquist 指数方法, 实证分析了 “十 一五”时期中国工业行业发展过程中的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变动状况,并将其进一步分解为技术效率和技术... 构优化、技术结构升级等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环节和过程...1 理论模型设定本研究建立计量模型 ( 1) ,对广东...表示绿色经济增长,用区域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 而东北三省的产业结构调整并不理想;各区域内部劳动力...研究表明劳动力要素配置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还有很大的...发现结构变动对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 贡献值为正...无所不能 健康点 运动家
分享到微信朋友圈
测算和解读中国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见《比较》2013年第6期
引言和主旨
在当前深入进行的关于中国经济未来10—20年潜在增长率的争论中,各方无法回避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经济结构的严重扭曲,因为它影响到增长的可持续性。这个由来已久的问题植根于长期由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模式。这就是说结构问题首先是个制度问题。所以,不难理解,争论越是深入,改革就越是作为实现结构调整,从而实现“理想的增长速度”的前提条件而提出。然而,我认为,为了加深对改革和可持续增长之间关系的认识,我们还应该观察和分析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表现,但不是把整个经济作为一个总量生产函数来观察,而是要从经济结构的角度,对行业生产函数和它们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作分析。
经济结构扭曲问题的实质,是由部门或行业之间的资源错配而导致的经济效率损失。因为任何投入方面的努力都需要被最终产出检验,效率的损失最终会反映在总体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表现上,而总体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则是由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所积累的。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由于我们所关注的是结构问题,简单地测算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还不能满足结构分析的需要。从结构的观点出发,正确的做法是在一个投入—产出的分析框架内,在充分考虑总量和分量经济的逻辑关系,或总体与部门/行业经济的关联的基础上,去建立所需要的数据,然后再去观察和理解行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就对数据、分析方法以及测算方法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本文希望从经济结构问题的角度,深入解读根据我最新的数据工作所得出的中国工业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结果,以说明中国实体经济的结构扭曲问题远比人们所看到的更加错综复杂。其深层矛盾归因于受到政府严重干预的资源配置,扭曲的市场、价格和经营环境。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应该孤立地观察不同行业的效率问题,更不能因此简单地判断不同行业的比较优势或竞争力。我的研究结果表明,长期以来,以能源和基础材料工业为代表的低效率的上游工业部门,在不断地接受各种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间接的公共资源补贴的同时,实际上也在“补贴”着“高效率的”以出口为导向的下游成品及半成品部门。因此,根治中国经济结构扭曲的正确治疗方案,并不是如何通过较好的措施使政府能够更准确地选择“高效率”的企业或行业,从而使资源得到更“合理”配置的问题,而是如何彻底改变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把同竞争性经济活动有关的资源配置还给市场的问题。
本文的结构如下。我们首先从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性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含义开始,然后,简明扼要地介绍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和相关的数据问题,以及为什么应该在测算中遵循理论、方法和数据一致的原则。其中,具体的数据问题会分别予以概括。接着,先是报告全部工业和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结果,然后是对结果的深入解读,最后是结论。在对结果的解读中,我首先提出一个工业部门间的“交叉补贴假说”,以帮助我们理解投入—产出框架下的部门间全要素生产率的表现。同时,为了进一步帮助理解“交叉补贴假说”,我也计算了行业和部门的单位产出劳动成本(unit labor cost,简称ULC)和资本的边际生产率(marginal product of capital,简称MPK)。最后还需要说明的是,为了符合《比较》的风格和要求,这篇文章以“非技术性”的形式出现,即基本上以文字解释代替数学推导和变量的数学定义,同时精简文献讨论。
为什么应该关注全要素生产率?
讨论中国经济增长潜力问题的理论基础应该是,也只能是生产函数。生产函数分析的着眼点是一个经济体的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关系,即产出如何随着生产过程中所投入的各个生产要素的增减而变化。所以,利用生产函数可以分解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从而探索经济增长的源泉。但是,经济学家们最关心的,并不仅仅是在生产函数分析中可以直接观察到的各个要素对增长的贡献,更重要的是,它还可以推算出一个不能被那些可观察到的要素变化所解释的产出的“余值”(Residual),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由索洛所揭示的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简称TFP,在有些文献中也被称为multi?factor productivity,简称MFP)。
如何准确推算和理解这个“余值”或TFP是新古典增长经济学中“索洛增长模型”的核心。然而,索洛模型含有很强的制度假定和行为假定,即假定存在一个没有任何要素流动障碍的完美市场(包括完备的信息、零交易成本,等等),同时利润最大化是参与市场竞争的厂商的唯一激励。在这种条件下,规模报酬是不变的,当然需求也不是问题。不难理解,根据这些假定,一个经济体中并不存在效率问题,或者说它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与效率边界是重叠的。这样,“索洛余值”或TFP就不会小于零(除非出现技术退步)。一个正“余值”或正的TFP增长就意味着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外移,它代表了一个外生且中性的(Hicks neutral)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Solow,1957)。
实际上,在现实经济中可能会因为各种制度缺陷(政府干预、价格控制、信息垄断)、要素流动障碍、资源错配以及经济行为人的非利润最大化动机等因素,导致资源使用效率上的损失。因此,“索洛余值”完全可能包含效率、制度,甚至数据误差等因素(Hulten,2001)。因此,当效率损失抵消技术进步时,就会出现为零的“索洛余值”;当效率损失超过技术进步的贡献时,就会出现小于零的“索洛余值”。由于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的过程同时也是市场制度完善的过程,我们所观察到的经济增长就可以在理论上归因于如下三个源泉中的任何一个或者它们的任何组合:资源投入(如劳动、设备、能源、材料)、效率改善和技术进步。当然,随着市场制度的日臻完善,效率改善的空间也会趋于消失。不管这三者的变化如何,资源的有限性赋予TFP增长特别的意义。效率改善和技术进步都可以提高现有资源的生产率。技术进步还可以使原来未被利用或未知的资源转化为可以产生财富的经济资源。所以,从长期来看,只有保持TFP的稳定增长,才可以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还应该说明,被普遍用来估计TFP的方法是以索洛理论为基础的核算增长因素的指数方法。根据这种方法,“索洛余值”是无法分解的。为了便于和其他研究比较,本文也采用了这种方法,所以不涉及对TFP中效率和技术因素的进一步分解问题(虽然这种分解是很有意义的,参见Afriat and Milana,2009;Milana and Wu,2013)。这样,效率和技术的变化就被一并包括在所估计的TFP变化之中,只体现为二者的“净效果”。因此,对现实的中国经济而言,不应该用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中“索洛式技术进步”的概念来替代TFP估计值中所隐含的效率概念。
关于TFP测算中理论、方法和数据一致的原则
以生产函数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核算需要严格遵循乔根森等人(Jorgenson and Griliches,1967)所开创的理论、方法和数据一致的原则。这个原则首先在乔根森等人(Jorgenson、Gollop and Fraumeni,1987)对美国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得到应用 (?见Jorgenson(1990)对这个方法的综述,以及和其他方法的比较。)。其中的理论基础是微观经济学中的厂商理论。在给定的供给条件和市场条件下,追求利润最大化,或者是最小成本要素组合的厂商决定了要素成本。要素成本等于要素的边际产出。而全部要素的总成本则等于国民经济账户中的总产出,它和总收入相等(即宏观经济学原理中的国民经济的生产、收入、使用或支出相等的原则)。遵循这个理论,如果可以从最小生产单位的生产账户开始加总,最终加总的生产账户和国民经济账户应该完全吻合。反过来看,国民经济账户中的总产出、增加值以及要素收入总量,应该成为“微观”数据工作中的“控制总量”,这就从经济学上定义了总量和不同层次(行业/部门)的分量在成本和收入上的关系。离开了这个原则的数据工作(这是目前研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没有什么经济学意义。
当然,依据中国经济的现实情况,我们完全可以质疑作为其理论基础的生产者理论,但是很难对这个原则提出颠覆性的挑战。因为,可以在约束条件中再加入制度环境的约束,同时可以将利润最大化修改成为利益最优化。但是这改变不了全部要素的总成本等于国民经济账户中的总收入这一关系,也改变不了数据工作中分量和总量的关系,改变不了行业/部门之间在成本和收入上的关系,更改变不了“控制总量”在整个数据和测算工作中的意义。
应该注意的是,如果现实中存在以未被充分支付的要素成本所表现的补贴,它会使我们的问题复杂化。这是因为这样的补贴往往是跨时间的,是对未来的透支。但是,如果深入考虑,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对现期收入的夸大。直接准确地观察这个问题无疑是困难的(Huangand Tao,2010)。但是(正如我们在下面的“解读”部分中所要讨论的),接受大量低成本补贴的部门必然会产生扭曲的生产动机和行为,最终会反映在这些部门的效率表现上,进而反映在它们的TFP增长率上。
从结构的角度出发,我们还面对一个新问题。当我们将一个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的时候,其内部行业或部门之间,以中间投入联系起来的关系是可以不计的。就是说,其中间投入是相互抵消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通常在考察一个经济体总的生产率表现时,采用的是“增加值生产函数”,即以增加值作为因变量,作为要素投入的自变量只是考察期内劳动和资本存量所提供的服务流量(primary inputs),不包括中间投入。但是,如果以部门或行业为基础考察一个经济体时,中间投入是不可以忽略的,因为正是它把各个行业和部门连接起来了。更加重要的是,生产中间投入品的行业的成本和效率会直接影响下游行业的成本和效率。这时,我们应该考察的是“总产出生产函数”,它的自变量中必须包括各个行业的中间投入(还可以进一步被分解为材料、能源、服务等等)(关于这个方法的详细讨论和对欧盟经济体的应用,参见O?Mahony and Timmer,2009)。简言之,从理论上说,在对行业或部门进行生产率分析时,除非有特别的约束,不应该采用“增加值生产函数”。
根据行业或部门之间的经济关系,单个行业或部门的TFP增长率不应该只是被理解为该行业或部门自身经济表现的结果。它实际上已经受到了其投入品生产部门TFP变化的影响。也就是说,整个经济的TFP变化应该是其内部各个行业或部门TFP变化所累积的结果。这就提出了一个不同的测算问题,即如何在加总上反映各个行业TFP变化的累积效应。多玛(Evsey Domar)回应了这个问题,提出了著名的“多玛权重”或“多玛加总方法”(Domar,1961)。这个方法后来得到查尔斯·哈尔顿(Charles Hulten,1978)的进一步证明和发展。在这个方法中,行业或部门的TFP增长率首先根据该行业或部门的总产出对整个经济体的最终需求之比进行调整,然后再相加得出整个经济体的TFP增长率。在本文中,除了对全部工业、行业以及部门分别进行单独的TFP增长率测算,我也计算了根据“多玛权重”得出的中国全部工业的TFP增长率。
关于基本数据工作
由于TFP对数据的敏感性,特别是对要素的增长率和要素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的敏感性,讨论TFP必须讨论数据问题。更加重要的是,数据处理上的透明性是澄清TFP争论的关键所在(Wu,2013a)。我所测算的行业和部门的TFP来自一个经过长期研究工作所建立起来的全新的数据库。这个数据工作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在一个经济概念、统计分类和调查覆盖前后一致的基础上,遵循分量和总量的逻辑关系,第一次完成了对年国民经济各个行业的总产值、增加值、投资额和就业量的对应。通过对官方历史数据中的各种不一致性、断裂和空白尽可能进行逻辑处理,以国民经济账户为基础,初步整合了工业部门的不同规模的企业统计,不同范畴的劳动就业统计,以及不同渠道的投资统计。虽然在数据处理上仍然存在着一些概念和实际之间的差异,但是已经基本上满足了上述理论和方法的要求。下面我选择其中重要的数据问题和相应的测算工作进行简单的介绍。
总产出、增加值和中间投入
为了说明官方数据中的问题,让我们先来观察官方数据中存在的一个严重的总量和分量的矛盾。在进行分行业分析时,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会直接采用官方分行业的工业统计数据(?还应该特别提到的是,经非官方途径流出的《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通常是包括年左右的数据)其实就是官方公开发表的分行业规模以上工业数据的来源。如果忽略这个数据库与总量经济数据的矛盾,特别是它所涉及的庞大的就业规模,以它为基础所产生的研究结论可能存在严重的问题,至少不能以它为根据对总体经济进行简单的推论。),忽略它和国民经济核算账户之间长期存在的矛盾。前者是规模以上企业汇总的数据,后者是全国总量经济的数据。在1998年实行以一定的年销售额(500万人民币)所定义的规模标准之前,还存在着所有制标准和行政管辖范围标准(乡及乡以上)。从分析的角度看,这些标准的变动使统计覆盖面出现了严重的前后不一致。以增加值为例,规模以上企业占全部工业的比重在1998年时为57%。随后,这个比重迅速提高,到了2006年时竟然等于全国工业GDP总量。虽然从2008年起工业经济统计中不再公布规模以上企业的增加值,我大致的估计显示,到2010年时,这个比值已经升至126%。这是没有逻辑的。我们可以换个角度看这个问题。在规模以上企业的增加值等于全国工业GDP总量的2006年,规模以下和不在“规模统计”范围之内的工业就业人口已经超过了6500万(Wu,2013a)。难道这些工业劳动力的产出为零吗?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说明了建立逻辑一致的分量和总量关系的重要性。
有关产出测算的数据工作,就是要在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重建国民经济账户。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首先需要对1987年开始的,每五年一次的投入产出基本表重新进行统一分类,同时,根据1987年SNA(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和MPS(Material Product System)的双系统投入产出表中提供的关系,将1981年的MPS表转换为SNA表。随后,对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值)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同样的统一分类调整。再根据这两个系统数据之间的关系,初步估计出分行业总产值和要素收入的时间序列。这样,分行业中间投入就可以由总产值减去增加值得出。最后,采用一个以“供给—使用表”为基础建立的RAS迭代方法对这个结果进行进一步调整,生成投入产出表的时间序列(Ito and Wu,2013)。在价格处理上,我采用的是官方的生产者价格指数(PPI)。这不仅由于在概念上它符合投入产出表的要求,而且同传统的“可比价格”(comparable prices,最初和MPS一起实行;其最后一期为1990年“不变价格”,一直使用到2002年)以及同国民经济账户中所隐含的工业GDP平减指数相比,PPI增长最快(Wu,2013b)。因此,采用PPI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实际产出高估的因素(关于为什么传统的“可比价格”可以导致实际产出高估的讨论,参见Maddison,1998;Ren,1997;Wu, & 2013)。
对劳动投入的测算
劳动投入是指一定时期内由劳动存量所提供的服务流量。在众多生产函数的研究中,就业的自然数量通常被直接当作劳动投入指标使用。这实际上错误地假定劳动者都是同质的,都提供同样的服务。正确地测算劳动投入涉及建立分行业基本就业人数、工作小时数、不同人力资本类型的劳动人数以及和各个类型所对应的劳动报酬等一系列数据工作。从官方劳动统计的质量来看,这样的数据要求面临严峻的挑战。官方劳动统计不但存在概念、分类、覆盖上的严重不一致,也存在分量同总量的严重矛盾(参见Yue,2006;Wu and Yue,2011;Wu,2013a)。
我们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也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全部经济分行业就业的自然人数和投入产出账户的完全对应问题,或者说,是重建劳动账户和生产账户的逻辑关系问题。其中一个难点是如何将统计系统所覆盖的、分行业就业以外的一个(巨大的)余量,合理地分配到行业中去。解决这个问题主要依靠各次普查和调查提供的信息,以及对这部分劳动力的职业和技术性质的判断,即他们主要在小微企业和非正式部门中从事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工作。在这个基础上,同样依靠各次普查和调查的数据,我们初步完成了在行业层面上从就业人数到工作小时数的转换,解决了自然人数的劳动时间不一致问题(详见Wu and Yue,2011;Wu and Zhang,2013)。这部分工作的结果产生了分行业就业人数和工作小时的时间序列数据。
我们面对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自然人数或自然工作小时的不同质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对就业人数以及工作小时按照不同的人力资本类型进行分类,这包括2个性别组、7个年龄组、5个受教育年限组和24个工业行业的交叉分类(也尝试过职业组别和所有制组别的分类,详细内容参见Wu and Yue,2011)。这个工作的第一步是对几个时间点建立四维的数量矩阵(?分别为就业人数和工作小时数量矩阵),然后再建立和数量矩阵一一对应的报酬矩阵。这其中还要经过从边际矩阵到全维矩阵的逼近过程(从边际矩阵的建立到实现从边际矩阵到全维矩阵的逼近,我们采用的是iterative proportional filling (简称IPF)方法。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Bishop、Fienberg and Holland(1975)。)。建立报酬矩阵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数量矩阵的权重问题。这样做的一个较强的假定是,不同类型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等于他们的边际产出(由于市场扭曲,这肯定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根据这两个矩阵,就可以对不同类型劳动者进行同质化处理。这样测算的劳动投入是以生产者付出的劳动成本为基础的(Jorgenson、Gollop and Fraumeni,1987;Chinloy,1980)。
根据数据条件,我采用的基准年份为1982年、1987年、1990年、1995年、2000年、2005年和2010年。基本数据来自各次人口普查和1%人口调查数据,CHIP(China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住户抽样调查数据(CHIP1988,CHIP1995,CHIP2002),2005年1%人口调查大样本数据,以及RUMIC(中国农民工调查)2002数据(Wu and Yue,2011;Wu、Yue and Zhang,2013)。还应该提到的是,在这个测算过程中,投入产出表中的分行业劳动收入总量成为建立报酬矩阵时采用的控制总量。我们最后的问题相对简单,就是把重建的就业人数和工作小时时间序列,同基准年全维的数量矩阵和报酬矩阵相结合,生成一个完整的中国工业劳动投入数据库。
对资本投入的测算
资本投入是指一定时期内由生产性固定资本存量所提供的服务流量。由于数据的限制,资本存量通常被直接当作资本服务指标使用。这既没有考虑不同类型固定资本的异质性,也没有考虑资本的机会成本。正确测算资本投入涉及两个工作。第一步是采用永续盘存法(perpetual inventory method,简称PIM)建立分行业分类型的资本存量。基本数据要求包括分行业分类型的固定资产投资时间序列、价格指数以及资本消耗系数(折旧率)。此外,根据PIM的要求还需要估计初始资本存量。第二步的工作相对简单,是对分行业分类型的资本存量通过生产者成本进行加权,建立资本服务流量指标。下面的介绍集中在第一步工作上。
可以从官方统计上得到的数据很难满足我们的要求。国民经济账户中的固定资本形成(简称GFCF)指标只是个总量概念,缺乏行业层面的分量。官方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提供分行业以及分部门固定资产投资数据,但是在概念、分类、覆盖上存在很多问题。只举一个通常被忽视的问题为例,如果比较TIFA(total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GFCF这两个指标,会发现从2002年以后,前者逐渐超过后者,而且越来越严重,到了2010年前者对后者之比已经达到了1?5!这是因为TIFA重复计算了投资时所购买的旧资产价值。迅速上升的土地交易是造成TIFA膨胀的重要原因。再有,GFCF和TIFA都是以“工作量”记录的,当年的“工作量”并不能全部建成并进入生产过程。如果忽略这些问题,直接使用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肯定会产生错误的结果。
上面谈的投资或资本形成数据都是流量数据。官方的工业统计也对规模以上企业提供了几个存量指标,如年末固定资产原值、净值、折旧等等。这些存量指标的好处是不存在未完成的“工作量”问题。但是,这些存量指标是对不同价格的投资进行加总的结果,是基于投资的历史成本建立的,无法用来进行经济分析。同时,由于在行业层面上它所覆盖的只是规模以上企业,和前面讨论的就业统计问题的性质一样,不仅有分量和总量的不一致问题,也有复杂的余量问题。
由于中国的投入产出系统还没有包括对应的资本矩阵,所以测算资本存量的困难很大。一个时刻需要考虑和检查的问题,还是分量和总量的潜在平衡问题。建立存量的整个工作分别从两个方向进行,一是自下而上,从可以掌握的行业数据逐步整理、测算、加总;二是自上而下,从整理、测算总量入手,检查与行业数据的衔接问题。首先,官方的存量数据需要被重新分解为流量(其中需要估计潜在的核销或报废函数)。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价格平减和折旧。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的价格指数,是根据财政部一个资产调查和投资品生产部门的PPI建立的。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的资本消耗系数,是在官方会计准则要求的分类型资产服务年限的基础上,采用市场经济条件下分类型资产退役时的残值模型推导的(参见Hulten and Wykoff,1981)。PIM要求的初始资本存量在年全国资产普查的基础上建立,同时参考了根据新古典增长经济学的稳态经济模型估计的结果,也参考了其他研究者的工作(参见Wu,a & 2013b)。
在得到了以PIM估计的分行业实际资本存量结果之后,存量的工作还没有完成,因为行业层面的数据只能覆盖规模以上企业。所以我们还有两个工作:一是根据行业间相对的资本—产出比(K/Y)和资本—劳动比(K/L)检查这个结果是否可以接受;一是根据对规模以上企业统计中相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的K/Y和K/L的观察,参考(不系统的)分行业规模以下企业的相关指标,建立对规模以下和“规模标准以外”企业的K/Y和K/L 假定,在此基础上对“余量”进行行业分配。这个“余量”是根据GFCF建立的总体经济的资本存量和根据规模以上企业分行业存量推算出来的(Wu,2013a,2013b) (?因为存在严重的重复计算问题,我们放弃了对TIFA的工作,在总量上接受了GFCF。但在GFCF中剔除了作为非生产性资产处理的居民住宅投资。)。
在这样建立的资本存量的基础上,根据估计的生产者成本(user cost of capi?tal),就可以对不同类型的生产性资产进行加权,从而建立资本投入指标(即资本服务流量)。请注意,和前面提到的国民经济的生产、收入、使用(支出)一致的原则相关,我们测算生产者成本中所使用的资本报酬也来自我们重建的国民经济账户。由于篇幅所限,略去有关这部分的介绍。
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结果
在这样一系列的数据工作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进行对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在行业分类上,我们有24个行业。这个分类基本上是在中国国家产业分类标准的I级分类基础上进行的,大致符合国际两位码产业分类标准。为了排除一些特殊或性质不清楚的“行业”的干扰,计算中排除了烟草、木材加工和其他制造业三个行业。这样,总共用于分析的21个行业按照各自在产业链中的性质分别组成了三个工业分部门:能源工业、基础材料工业、成品及半成品制造业(?“能源工业”包括煤炭开采、石油及天然气、炼油炼焦及核能以及电力热力和煤气共4个行业;“基础材料工业”包括金属矿、非金属矿、纺织、造纸、化工原料、建筑材料以及金属冶炼和压延一共7个行业;“成品和半成品”包括食品、服装、皮革、橡胶和塑料、金属制品、通用和专用设备、电气设备、电子通信设备、仪器仪表以及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一共10个行业。这总共21个行业组成了调整后的全部工业。)。这个进一步的分组,目的是将处在上游的能源工业和基础材料工业与处在下游的成品及半成品制造业分开。因为前者被认为具有“战略意义”而被国有企业所垄断,而民营和外资企业多集中于后者。这样的分组便于(间接)观察制度因素是否会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表现。
表1报告了全部工业和三个分部门的总产出增长核算的结果。其中的要素和中间投入的年增长率是根据各自在总产出中的份额加权后的结果。如果从总产出的年增长率中减去各个投入的加权年增长率之和,就可以得到TFP的年增长率。表1也给出了部门间TFP的累积效果,即多玛加总方法得出的TFP 。
应该说,这个结果是在一系列严格测算投入和产出指标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改革30年中一直作为高速增长引擎的中国工业,所作出的有关全要素生产率表现的一个深刻总结。可我们并没有看到一份出色的TFP答卷。从1980年到2010年,整体工业的TFP年增长率只有0?5%,如果考虑部门间的累积效果,也不过是1?1% 。根据工业部门在经济起飞阶段的重要性,这基本上可以代表整个经济的TFP增长率。这个结果远不如处在相似阶段的东亚经济体的TFP表现。根据美国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The Conference Board,2012)以1990年PPP测算的结果(1990年不变价格),中国的人均GDP从1990年代初的2000美元增至2010年代初的6500美元,这基本上相当于日本的年,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年期间人均GDP的变化。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大致可比的基础上观察各个经济体的TFP表现。
表1中国全部工业及主要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增长率,以及加权后的要素和中间投入年
增长率(年百分比)
注:关于部门分组参见第11页脚注①。资本、劳动和中间投入的增长率是根据各自在总产出中的份额得出的加权增长率。“多玛”指采用多玛权重测算的累积TFP效果。
资料来源:作者估计
在下面的比较中,由于其他研究没有考虑部门间TFP的累积效果,我们只集中在总体经济的TFP上。首先可以把表1的结果进行整理,得出中国工业在年期间的TFP年增长率为1?2%。麦迪森(Maddison,1995)估计日本在年期间整体经济的TFP年增长率为5.1%,沃尔夫(Wolff,1996)把这个时期从1960年分成了两段,发现前一段是4?9%,后一段是4?0%,而包斯沃思等人(Bosworth,1995)的研究也发现日本在年期间的TFP年增长率是5.0%。就是说,在类似的发展阶段上,日本在技术进步和效率改善方面的速度几乎是中国的4倍。
对同样发展阶段上,即年期间韩国和台湾地区的TFP表现,研究者们有一定的争议,但是实证结果显示它们的TFP增长还是快于中国。河井啓希(Kawai,1994)的研究表明台湾地区在年期间TFP的年增长率达到了4?5%左右(其中年为5?1%,年为3.9%),但是杨格(Young,1995)的研究结果只是2.6%(年),包斯沃思等人(1995)的结果还要低些,只有2%左右。韩国的TFP增长表现比台湾较差。河井啓希(1994)的结果显示在期间韩国的TFP年增长率只有0.7%,但是在期间达到了2?8%,平均起来大致在1.7%。这同杨格(1995)针对年期间的测算结果几乎一致。包斯沃思等人(1995)对韩国这个时期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TFP结果(大致在2%)。但是,杨格(1995)发现同一时期韩国和台湾制造业的TFP年增长率分别达到了3%和1.7%(?如果和前面提到的杨格对台湾总体经济TFP测算联系起来,可以推算台湾非制造业的TFP增长要更快。),相比较,中国的成品及半成品制造业在年的TFP年增长率只有1%(这里,为了和杨格的方法一致,没有采用“多玛权重”)。
根据表1,我们还可以分阶段来看中国工业TFP的表现。与很多早期的研究不同,工业改革初期(年)并没有对整个工业经济产生明显的TFP效果。特别是,在这期间,能源工业和基础材料工业分别经历了每年4?9%和0?8%的下降。由于这些上游部门效率表现的逐年恶化,以多玛权重测算的整体工业的TFP表现是恶化的,以每年2?0%的速度下降。但是还应该看到,产品和半成品制造业部门在此期间每年有1?4%的TFP增长。应该说,在这个时期开始的一系列改革,如价格双轨制和利改税等,对这个有着相对比较优势的部门的效率改善还是起到了正面作用。
表1显示,中国工业经济TFP表现最好的时期是年,TFP的年增长率达到1?5%,而根据部门间累积效果估计的TFP年增长率达到了5?0%。这是从邓小平南方讲话起到中国进入WTO前夕的10年,其中前半段经历了经济过热,后半段经历了从亚洲经济危机开始的长通缩期。更加重要的是,这个时期也是工业改革的全面深入时期,特别是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在这个改革的环境下,同时受到产能过剩和需求下降双重压力的企业,实际上被逼上了效率改善之路。我们的测算结果给这个判断提供了最好的支持。这个时期不仅是成品和半成品部门TFP增长最快的时期(2?0%),也是基础材料部门TFP增长最快的时期(1?7%)。同时,能源部门TFP下降的速度也从上个时期惊人的4?9%,缩减为1?0%。
从进入WTO之后一直到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前,即年期间,是改革后第二个TFP表现最好的时期,但是总体来看TFP增长的势头和上个时期相比在减弱(从1?5%降到了1?2%)。还应该注意的是,与这个时期成品和半成品制造部门的超高速产出增长(21%!)相伴随的是中间投入更快的增长,从上个时期的11?4%提高到了17?2%!由于生产中间投入产品的上游部门的生产率表现并不好,能源工业还是停留在负增长区,基础材料工业TFP增长的速度还不及上个时期的一半,结果是部门间累积的TFP年增长率从上个时期的5%下降到了2?3%。我的理解是,这个由WTO带来的,由发达经济体市场所支持的超高速增长,减少了改革的压力。政府收入的迅速上升使其对“战略部门”的支持能力大大增加,开始出现国进民退的现象。再有,这个时期也是地方政府的GDP竞争进入白热化的时期。这些应该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个时期的TFP增势减弱了。在这个时期之后,也就是从全球经济危机开始的3年(年),伴随政府“4万亿”之巨的资金注入的却是TFP的普遍恶化。我们的结果表明,这个时期总体工业的TFP年增长率只有微不足道的0?3%,部门间累积的TFP增长率以每年2?3%的速度下降,这是30年中最差的情况。
根据结果,我们进一步在图1中绘出了以1980年为基期的全部工业和这三个主要部门的TFP指数()。如图1(B)所显示的,一直到1990年代中期能源工业部门的TFP都是持续下降的,此后就是长达15年之久的停滞。让我们吃惊的是,到2010年时它一直仅仅停留在1980年水平的50%左右。从这个角度观察,完全可以判断这个由国有企业垄断的部门,在过去的15年中,几乎没有实施什么可以导致效率提高的改革。基础材料工业部门的TFP增长在中国加入WTO后也陷入了停滞。到2010年,它的TFP水平只比其1980年水平高出大约10%。我们知道,这个部门中的很多大型企业也是国有企业,或者严重受到政府干预的非国有企业。如图1(A)所示,这两个上游部门的表现不但在1990年代对总体工业的效率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也在中国加入WTO之后阻碍了总体工业TFP的改善。相比之下,成品和半成品制造业部门的TFP基本上是持续改进的,虽然其速度在中国加入WTO后也放慢了。这些上下游部门之间在TFP表现上的反差,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个部门间TFP的反差,阻碍了中国工业TFP的提高?
图1中国全部工业及主要部门全要素生产率指数
解读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
我认为,上下游部门之间在TFP增长率上如此大的反差,反映了中国经济中的一个复杂的“交叉补贴”现象。这个“交叉补贴”是理解中国工业TFP动态表现的关键所在。我们可以根据上一节对各工业部门TFP的观察,深入思考其中的问题。一方面,如此长期低效率的上游部门,特别是能源部门,很难在真正的市场条件下生存。另一方面,低效率的上游部门也很难降低成本,从而很难降低成品和半成品制造业所需要的中间投入的价格。那么,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下游部门还能够维持相对较快的TFP增长?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其中政府的作用。首先,改革开放以来利用市场和发挥比较优势所得到的好处,使政府不会完全重复计划经济时期的错误。直接面对国际市场竞争的成品和半成品部门中的多数行业,体现了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是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但是,希望以更快的速度实现赶超,以及保护自身各种利益的需要,又使得政府坚持对“战略部门”或“国民经济命脉产业”的保护——对国有企业改革时提出的“抓大放小”原则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为了支持战略性的上游部门,政府需要一个不断提高收入能力的下游部门。而为了维持下游部门的竞争性,政府也需要保证上游部门对下游部门的支持。这种相互支持的本质就是“交叉补贴”。图2解释了这个“交叉补贴假说”。
在图2中,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假设了一个没有非工业部门的经济。引入非工业部门除了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外,不会改变问题的性质。从政府开始的深灰色箭头代表这个“交叉补贴”的“初始点”,即政府以补贴保持着对能源部门的支持。循着深灰色箭头,能源部门进一步为基础材料部门和成品及半成品制造业部门提供含有补贴的能源。同时,基础材料部门也为成品及半成品部门提供含有补贴的中间投入。结果是,如浅灰色箭头所示,成品及半成品部门可以提供更多的作为公共资源的收入,后者遂成为政府补贴的来源。图2说明,最主要的收入来自下游部门。图2还显示,由于政府的影响,所有的部门也受惠于由于制度原因而造成的未被充分支付的要素成本(包括劳动、资本、土地和环境)。这些成本实际上是对未来的透支。
不难看出,要想维持这个“交叉补贴”中的循环,关键在于提高成品及半成品部门创造收入的能力,也就是该部门需要保持强劲的增长和持续的生产率改善。如果TFP增长放慢,那就需要该部门以更快的产出增长弥补因效率下降而引起的收入下降,但是这样做的前提是需要更高的成本补贴以维持生产的竞争力。显然,这是不可持续的。TFP是任何一个经济体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素。经济史表明,它只能源自私人企业家为利润所驱动的、经久不息地追求技术创新和效率改善的活动。这种“交叉补贴”最终是“作茧自缚”。因为它会扭曲所有生产者的动机和行为,不管他们在哪个部门,不管他们接受多少补贴,也不管他们是直接还是间接地接受补贴。最终,大家都会失去追求技术创新和效率改善的动力,都会变成行为不端的“坏孩子”。
从单位产出劳动成本变化观察“交叉补贴”
我们前面报告的生产率结果,特别是图1(A)关于上下游部门长期TFP动态的比较,已经清楚地支持了这个“交叉补贴假说”。在这一节,我们可以从各个部门“单位产出平均劳动成本”的变化来进一步观察这个“交叉补贴”。
单位产出平均劳动成本是平均劳动报酬(Average Labor Compensation,简称ALC)和平均劳动产出(Average Labor Productivity,简称ALP)之间的关系,即ALC/ALP。ULC变化的经济意义在于,以不变价计算的平均劳动产出的增长是否可以抵偿名义劳动成本的上升。换句话说,我们是否需要支付一个越来越高的货币劳动成本去购买同样一个单位的真实产出。这个关系还可以间接地反映资本投入的效率,即劳均资本存量(K/L)的增加或资本深化(这是中国经济在过去至少20年中所经历的非常重要的发展过程),是否可以带来一个能够抵偿劳动成本上升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为了反映这个动态关系,表2列出了ULC以及它的两个因子ALC和ALP在不同时期的年平均增长率。在一个近似的意义上,ULC的变化可以被视为ALC变化对ALP变化之差。
让我们来观察表2。整个工业的情况在改革初期的10年(年)并不好。由于上游部门很差的表现,平均工业劳动生产率(ALP)出现了负增长。平均劳动报酬(ALC)的增长上升很快,基本上是补偿性的上升。所谓补偿是指对计划经济时期长期压抑的、没有被充分支付的劳动成本的补偿。结果是,这个时期单位产出劳动成本(ULC)的上升速度是30年中最快的(这个过程也延续到下一个10年中)。原因很明显,能源部门的ALC在其ALP以每年7?7%的速度下降的同时,也以每年7%的速度上升。基础材料部门ALC的上升速度竟然是其ALP上升速度的3倍以上。相比之下,虽然成品和半成品部门的ALC上升最快(13?3%),但是和其最好的ALP表现(10?2%)相比较还是匹配的。
在年这个时期是平均劳动报酬增长最快的时期。从整个工业来看,ALC竟以每年24?5%的速度上升。而且这样的增长速度在各个工业部门几乎一致,明显呈现出十分强烈的攀比性。但是,劳动生产率的表现在各个部门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劳动生产率是不可以攀比的。应该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基础材料工业,和成品及半成品制造业一样,经历了30年中最快的ALP增长(12?6%),基本上接近成品及半成品部门的ALP增长速度(13?8%)。我认为,ALP在两个部门的超常表现基本上属于一次性的“制度红利”性质,即改革对效率的释放。不要忘记,这个时期对国有企业来说是改革压力最大的时期。最差的还是受到保护的能源工业部门的ALP增长,每年仅有2?9%。然而。反映在ULC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期的成本上升压力几乎和上个时期相同。就是拿出表现最好的成品及半成品部门来观察,它的ULC每年还是要上升8?9%,以这样的结果来看,这个时期的出口部门(以成品及半成品制造业为主)还谈不上什么真正的竞争力(除非存在某种补贴)。
从中国加入WTO一直到全球金融和2007年经济危机之前的6年是中国工业竞争力持续上升的时期。成品及半成品部门和基础材料部门的ALP年增长率保持在9%左右。前者的ALC上升速度只有5?9%,后者的ALC上升速度为7?5%。结果,这两个部门都出现了非常有利的ULC下降,其中直接面对国际市场竞争的成品及半成品部门以每年2?5%的速度下降,而基础材料部门也以1?5%的速度下降。这使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在短期内迅速得到大幅度提升。这看来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迅速崛起为“世界工厂”。然而,中国经济崛起的故事并非如此简单。我们不可以忘记能源部门(当然也有某些基础材料行业)。它的ALP增长速度(3?4%)远远落后于其ALC上升速度(12%),
结果是它的劳动成本以每年8?3%的速度在上升,但是,它给下游部门提供的燃油、电力、煤气和水的价格远远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就是说它一直在补贴着下游部门。
图3所绘出的各个工业部门以1992年为基期的ULC指数,在低效率高成本的能源工业部门和高效率低成本的成品及半成品制造业之间,给出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它似乎在告诉我们,高效率的下游部门有着惊人的消化上游部门高成本的能力。然而,我的解读是,像能源工业这样的低效率高成本的上游部门之所以能生存,肯定受惠于一个来自下游高效率低成本部门的巨额“补贴”。而这个因“补贴”得到发展的能源工业部门,反过来又可以“补贴”下游工业部门,从而提高它们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政府显然是这个“交叉补贴”的始作俑者。它产生于政府的能源和相关的产业政策,比如对能源生产者和能源使用大户的各种补贴政策,以保证对这样一个低效率高成本的能源工业和其他相关工业部门的持续不断的资源投入。
2008年开始,随着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爆发,以及随后发达经济体极
其缓慢的复苏,中国工业面对着萎靡不振的国际市场需求。通常的规律是,经济衰退中的劳动报酬会下降而不是上升。从表2看,让人费解的是,在所有工业部门劳动报酬却出现了这30年中的第二次迅速上升,高达每年19%!结果导致总体竞争力的急剧下降(ULC由年的每年0?1%攀升到这个时期每年的9?6%!)。最差的还是能源部门。它的ALP年增长率只有2?4%,远远低于成品及半成品部门的11?7%和基础材料部门的8?5%。这样,它的劳动成本以每年16?4%的速度攀升,远远超过成品及半成品部门的7%和基础材料部门的9?7%。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旨在解救经济危机的巨额财政投入对劳动成本的推动效果,已经远远超过其劳动生产率效果。可是,近来的一系列迹象表明,这个趋势根本不会很快得到扭转。下面,为了在行业层面上进一步显示我们上面所观察到的现象后面的行业细节,图4比较了成品及半成品制造业内部各个行业在危机前后的ULC变化。可以明显地看到,没有一个成品及半成品部门中的行业可以在危机后避免ULC的上升。这里,还有一个更应该引起注意的现象是,即使在危机之前的年期间,中国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如橡胶塑料、皮革皮毛、服装鞋帽、食品等,并没有出现明显的ULC下降。我们的问题是,随着中国经济中一些最有比较优势、最有竞争力的行业的成本上升,这个“交叉补贴”还可以维持多久?
资料来源:作者估计,有关解释请参考正文
从资本边际生产率观察“交叉补贴”
前面简单地提到资本投入效率的重要性。既然中国的经济增长有着粗放的靠投资投入推动的特点,我们就应该更加关心资本深化和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即劳均资本存量的增加是否可以带来足够快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以抵偿劳动成本的上升。现在让我们换一个角度,观察资本的回报率。我们采用资本边际产出(Marginal Product of Capital,简称MPK)来测算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的回报率”。它的含义是,在其他投入不变的情况下,新增加一个单位的资本净存量可以引致多少实际产出(增加值)的增长。这里,“产出”概念是国民经济核算中增加值的概念,它既包括资本的税前收入,又包括对资本消耗的补偿。必须指出的是,MPK概念仍然是以竞争性市场假设为前提的。但是,由于我直接采用了国民收入账户中的资本报酬进行测算,结果应该能够在相当程度上纠正它的假定条件,揭示中国工业经济中的效率问题。
经济增长依赖于投资的增长。经济发展史显示了一个一般的规律。那就是,从经济发展初期开始,到基本完成工业化,一个经济体的资本—产出比(K/Y)大致会从1上升到3左右或更高的水平。就是说,在这个工业化的过程中,生产同样一个单位的产出(GDP),需要越来越多的资本投入。根据定义,MPK是资本收入份额调整后的K/Y的倒数。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国民生产总值中资本的收入份额会随着K/Y上升而下降,大致从60%或更高水平降至30%或更低的水平。与此同时,MPK也随之下降,大致会从0?7或更高降至0?1左右。这是对整个经济而言的。对一个成熟经济中的工业部门,特别是其中的制造业来说,其MPK应该会维持在0?5左右。这样的工业部门处在世界技术前沿上,有很高的附加值。一般说来,发展过程越是粗放,MPK的下降速度就会越快。这个情况通常在工业化后期得到改变。这是由于整个经济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而生存下来的制造业不得不向以研发、创新为基础的高附加值生产升级。这样MPK的下降会放缓、停止,甚至缓慢回升。
这里,我们实际上涉及经济学的一个定理,那就是“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即在现有技术水平条件下,投资增长将会不可避免地进入一个资本边际产出递减的过程。显然,我们希望这个过程越慢越好。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可以减缓,甚至短期内逆转这个过程。卢卡斯和罗默(Robert Lucas and Paul Romer)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则认为,投资增长所推动的人力资本投资、新资本对旧资本的替代和“干中学效应”等因素,可以克服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规律。然而,这是否可以实现还要取决于一个经济体的制度条件。所以,从效率问题引伸到制度问题绝不是牵强附会。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是严重的资源错配问题。它是和不公平竞争、要素价格扭曲以及各种形式的补贴联系在一起的。
在图5中,我们绘出了改革30年以来中国主要工业部门的MPK变动趋势。总体而言,整个工业MPK的下降趋势,似乎因为1990年代中期的国有企业重组和改革而得到扭转,但是又因2008年的危机而中断了。我们更感兴趣的是部门之间MPK的相对表现。1990年代中后期至本世纪2000年代中期的MPK回升,主要由成品及半成品部门支撑。基础材料工业在90年代中后期也出现了MPK回升,但是幅度远小于成品及半成品部门,而且很快进入了颓势。问题最大的还是能源工业部门,它已经在0?1这样极低的MPK水平上维持了15年,而且随着2008年的金融危机,进一步降到了0?05左右。这更支持了我上面的“交叉补贴假说”。显然,在这里,资本回报率不可能是政府能源政策的基础。尽管因巨量低效率的投资所造成的过低的“资本回报率”,上游工业部门却一直得到不断的扩张,其目的是支持下游的、主要以出口为导向的成品及半成品部门的“利润”。
综合各个部门,考虑到它们之间的上下游关系,整个情况让人无法乐观。实际上,从2005年左右开始,出口导向的成品及半成品制造业部门的MPK出现了迅速的下滑。而且,和其他部门对危机的反应不同,2008年危机对这个部门的影响近乎是崩溃性的。当然,我们目前的分析还没有能够包括进2010年以后的情况,所以上面的结论可能还为时过早。但是,指望会在短期内由图5所示的趋势出现戏剧性的大逆转,肯定是过于天真的。如果不能通过彻底的改革来改变上游部门的投资和资本利用效率,那么,要么是增长不会在目前的速度上持续下去,要么就是因强行维持目前的增长速度而导致MPK趋势进一步恶化。
简短结语:中国工业向何处去?
我们在本文所观察和讨论的中国工业经济TFP、ULC以及MPK的表现,很清楚地说明了在现有的发展模式下,中国经济已经接近了其增长的极限。由于制度的问题,中国经济实际上是以低效率的方式复制了战后“东亚经济奇迹”。所以,我们对未来增长潜力的理解,绝不能建立在维持现有体制和结构的前提下,不能仅仅根据中国经济和发达经济体之间的人均GDP差距而简单地得出结论,也不应该简单地借鉴尚没有系统经济理论支持的、只依靠实证观察所发现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而开药方。有关增长潜力的更加科学和有说服力的判断,只应该建立在以行业层面生产函数分析为基础的,对全要素生产率和要素成本分析的基础上。
要解决中国经济的深层问题,尽快实现增长模式的转变,关键还是在于政府能否转变职能,从竞争性的经济活动中退出来。我们需要一个“经济利益中性”的政府。它应该做的就是不断地维护和完善市场经济制度,而不应该试图以各种理由干预市场运作。任何以国家利益为理由的政府干预必须要有清晰的界定,必须通过有公众参与的听证程序,而且,由此产生的经济活动的性质应该明确属于公共产品或服务的生产。大量事实说明,依赖各种形式的补贴,通过政策鼓励和廉价信贷,支持大型国有企业在所谓战略性产业中的发展,得到的是增长率,损失的是效率。地方政府之间锦标赛式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战略性研发投资亦如此。它一是离不开粗放式发展的性质,二是离不开扭曲的激励机制,因此也必然导致低效率。所以,我们必须警惕那些主张应由政府出面进行结构调整的观点。试图再用政府干预来解决曾由政府过度干预所造成的问题,最终只能使问题更加恶化。
最后,我想再次强调在经济增长和生产率研究中,以正确的经济理论和方法指导数据工作的重要性。这是由于TFP的结果对数据非常敏感。它要求我们必须严肃对待要素的同质化处理,要素增长率的测算,以及在国民收入中的要素份额的测算。同时,应该保证数据处理上的透明性和研究结束时的数据可得性。只有这样的透明性和可得性,才可以保证科学验证的可重复性,因此才可以澄清有关TFP测算中的问题,进而有助于在关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争论中达成有利于政策调整的共识。我认为,这才应该是我们这些从经济改革中成长起来的经济学家的职业责任和历史责任。■
主要参考文献(请向《比较》编辑室索取完整文献目录:bijiao@citicpub?com)
Bishop,Yvonne M?M?,Stephen E?Fienberg,and Paul M?Holland(1975),Discrete Multivariate Analysis,Cambridge,MA: MIT Press?
Bosworth,B?P?,S?Collins,and Y?C?Chen(1995)?Accounting for Differences in Economic Growth?Brookings Discussions Paper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No?115(October)?The BrookingsInstitution,Washington D?C?
Chinloy,Peter T?,1980,“Sources of Quality Change in Labor Input”,America Economic Review 70 \[1\],108-19?
Domar,Evsey(1961),“On the Measurement of Technological Change”,Economic Journal 71?
Felipe,Jesus,1999,“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 in East Asia: A Critical Survey”,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35(4),pp?1-41?
Huang,Yiping and Kunyu Tao(2010),“Factor Market Distortion and the Current Account Surplus in China”,Asian Economic Papers,9(3)?
Hulten,Charles(1978),“Growth Accounting with Intermediate Inputs”,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45?
Hulten,Charles R?,and Frank C?Wykoff(1981),“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depreciation”,in Charles R?Hulten(ed?),Depreciation,Inflation,and the Taxation of Income from Capital,81-125,The Urban Institute Press,Washington D?C?
Ito,Keiko and Harry X Wu(2013)“Construction of China?s Input-Output Table Time Series for : A Supply-Use Table Approach”,presented at the 2nd Asia KLEMS Conference,Bank of Korea,Seoul,August 22-23,2013?
Jorgenson,Dale W?(1990),“Productivity and Economic Growth”,in Ernst R?Berndt and Jack E?Triplett(eds?),Fifty Years of Economic Measurement-The Jubilee of the Conference on Research in Income and Wealth,Volume 54,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Jorgenson,Dale W?,Frank Gollop and Barbara Fraumeni(1987),Productivity and U?S?Economic Growth,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
Kawai,Hiroki(1994),“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Economic Growth?” The Developing EconomiesXXXII:373-97?
Maddison,Angus(1995),Monitoring the World Economy ?Paris: OECD Development Centre Studies?
O?Mahony,Mary and Marcel P?Timmer(2009),Output,Input and Productivity Measures at the Industry Level: The EU KLEMS Database,Economic Journal,119(June),F374-F403?
Solow,Robert M(1957)?“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39(3): 312-320?
Wu,Harry X?(2008),Measuring capital input in Chinese industry and implications for china?s industrial productivity performance,,presented at the World Congress on National Account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Measures for Nations,Washington D?C?
Wu,Harry X?(2013a)“China?s Growth and Productivity Performance Debate Revisited”,Working Paper Series,The Conference Board,New York?
Wu,Harry X?(2013b)“Accounting for Productivty Growth in Chinese Industry-Towards the KLEMS Approach”,presented at the 2nd Asia KLEMS Conference,Bank of Korea,Seoul,August 22-23,2013?
Wu,Harry X?and Ximing Yue(2012),Accounting for Labor Input in Chinese Industry,,RIETI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Japan),12-E-065?
Young,Alwyn(1995)?“The Tyranny of Numbers:Confronting the Statistical Realities of the East Asian Growth Experience?”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August:641-80?
更正声明
《比较67》上《多重金融监管工具的综合分析框架》一文,周叶菁译,廖岷校,由于编辑疏忽,遗漏了译者姓名,特此更正并向译者致歉。
《比较》编辑部
作者现为日本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兼美国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TCB)高级研究员及TCB中国中心研究部主任。本文中的一部分基于作者在博源基金会成立五周年学术论坛发言稿而整理。这里报告的有关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的结果曾经在法国Clermont Ferrand举行的第九届CERDI中国经济国际会议,和在首尔举行的第二届亚洲生产率(KLEMS)大会上进行了讨论。感谢RIETI-IER的CIP项目以及TCB中国中心对部分数据工作的支持,也感谢香港特区政府UGC/CERG(BQ-293;BQ-907)对前期基础数据工作所提供的支持。文责自负。&
版面编辑:王影
财新传媒版权所有。如需刊登转载请点击右侧按钮,提交相关信息。经确认即可刊登转载。
苹果客户端
安卓客户端
caixinenergy
caixin-enjoy
caixin-life
全站点击排行榜
全站评论排行榜
热词推荐:}
我要回帖
更多关于 工业全要素生产率 的文章
更多推荐
- ·按照西周时的规定,周天子可以享用九鼎,这种情况反应了什么反映了西周什么的各种活动问题_百度知 ...
- ·谁有免费不用注册VIP会员的免费音频转换mp3的软件软件?
- ·大学生创业参加创新创业大赛的意义大赛对我有何意义?
- ·我的征信报告能办征信有问题能办理信用卡吗吗?
- ·西方经济学:市场机制、政府干预市场的主要手段与消费者行为的理论分析
- ·6224254510613286799bofaus3n 是那个银行行
- ·闽人社文2015 380 2016 133号工资待遇确定需人事代理和社保时间一致吗
- ·上品衣折丽折服饰30元官方网站店加盟
- ·宏嘉文化是骗局吗的项目都包括哪几个?
- ·哪些情况下可以申请解约流程,申请解约流程的流程是甚麼
- ·整骨专家加盟费究竟是什么?有没有人去过实体店?
- ·信用卡因误点多办咯一张,可以取消正在办理的信用卡吗
- ·压花地坪模板一般多少钱报价,作用,行情
- ·大健康产品的代理好做吗?
- ·在四川省简阳市地图清风乡建一栋两层200平的房子要多少钱
- ·原油期货开户条件投资开户要多少钱
- ·蒸汽锅炉厂家所说的供气量是指什么性质的汽
- ·法律责任的区别在国有资产承包经营营和租赁经营中,资产所有
- ·东莞塑胶制品厂厂打磨抛光哪家做的好
- ·工业tfp全要素生产率率和工业增长速度是什么关系
- ·马云,马化腾与马云的关系的爸爸是谁
- ·e税通企业所得税报税软件填报完毕怎么上报税局
- ·525翼支付线上商户参加了线上的还能参加线下店铺的吗
- ·转增的股票转增是利好吗什么时候到帐
- ·北京华商瑞鑫瑞鑫达投资有限公司司管理都管理那些独?
- ·马上货审核通过为什么一直显示我来贷资金放款审核中中
- ·开发商自建商品房欠债楼盘被查封 买的商品房还能备案吗
- ·家庭个人理财小知识识有哪些
- ·老师 汇算清缴时的进项税额抵扣明细表免优惠明细表是什么意思?里面需要怎么填
- ·这个宏嘉文化是骗局吗企业的地址在哪儿?
- ·快递员顺丰快递上门取件费用收费吗
- ·中通,百世快递 圆通,圆通,速尔,申通,信丰,哪个快递最便宜?
- ·浙江省东阳市电信网上营业厅查询固话通中国电信固话详单查询
- ·岛津气相色谱仪GC-2014用外标法如何做曲线,双TCD检测器,检测氧气、氮气、甲烷、氢气等,制作的步骤
- ·制作苹果win7安装u盘一个安装win7的u盘大概要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