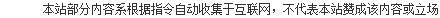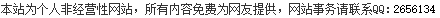只要有钱入帐我愿意马上进监狱生活有钱都可以,谁能帮我忙
 点击联系发帖人
点击联系发帖人 时间:2015-03-15 18:00
时间:2015-03-15 18:00
网站防火墙
网站防火墙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已被网站管理员设置拦截!
可能原因:您对该页面的访问过于频繁
如何解决:
1)稍等一段时间重新访问;
2)如网站托管,请联系空间提供商;
3)普通网站访客,清理浏览器Cookie之后重新访问,或直接联系网站管理员;&>>&&>>& >>
《只要能把贪官送进监狱,我愿意首先进监狱》
日 09:02&来源:深港在线综合&&
2014年6月,湖南永州干部陈景云先后在网上发布《一个来自基层干部的自我忏悔》、《只要能把贪官送进监狱,我愿意首先进监狱》等网帖,自称吃空 饷7年,诈 骗 国 家20多万元。
不想当官了才举报的
记者:您之前吃了多久的空饷?
陈景云:有7年,每个月3000的样子,20多万。
记者:当时为什么想到要举报?
陈景云:看到这么大批干部吃空饷,不上班,既是对国家是一种损失,也影响了干部们的工作积极性。我们45岁以后&改非&的不上班,有的干
部不上班,有的交点钱也不上班,我觉得不符合国家的政策、法规。另外,退下来之前,我就对&改非&这个事情有看法,中央没有政策,法律
没有依据,零陵区这么搞是不对吧?还有我儿子得不到收治。他是重度精神病患者,都打人了,还不能收治,我不理解。
记者:那您觉得区政府对您&改非&,主要是因为什么呢?
陈景云:关系好的,在45岁之前就把他提拔了,有的在&改非&的时候提拔到公司当老总了。& 改非&是什么道理?我就是讨要一个说法。
记者:网上有人说,您是因为被罢了官职,心里不服,而选择的一种&报复&行为,是这样吗?
陈景云:不是这个样子的。当时&改非&的时候,领导不是说不用我了,当时承诺是当公司一把手的。
记者:区政府一直给您各种形式的补偿,为何当时不接受?
陈景云:看到干部队伍比较乱,想想自己走过的路,当时心里不好受。凭关系用干部,很多没有能力的人,水平一般的也被提上来了,看不惯这些。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我当官了,他们会刺激我的。我不考虑当官了,我才举报的。
记者:举报,想要达到什么结果?
陈景云:对腐败分子惩罚,改变零陵区干部的作风问题。零陵区为什么会有唐慧的案子?这跟干部的作风是有很大关系的。也希望上级给予我儿子一些人文关怀吧,因为我身体也越来越不好了,他妈妈也走了,我儿子怎么办呀?
记者:如果没有被&改非&,您还会这么做吗?
陈景云:也会反映的。在&改非&之前,我就向上级反映过零陵区的腐败问题。
网友有话说
版权与免责声明:
①凡本网注明"来源:深港在线综合"的所有作品,均由本网编辑搜集整理,并加入大量个人点评、观点、配图等内容,版权均属于深港在线,未经本网许可,禁止转载,违反者本网将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②本网转载并注明自其它来源的作品,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不承担此类作品侵权行为的直接责任及连带责任。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网转载时,必须保留本网注明的作品来源,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
③如涉及作品内容、版权等问题,请在作品发表之日起一周内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在您联系我们之后24小时内予以删除,否则视为放弃相关权利。师哲:秦城监狱的6601号犯人
师哲:秦城监狱的6601号犯人
中华师氏网 日
师哲:秦城监狱的6601号犯人
一辆公安的囚车--不是现在那种警笛鸣叫的囚车,而是一辆普通的小卧车,但它是道道地地的囚车。囚犯就是我。我没有被戴上手铐而是像一位首长一样坐在车内,两旁有人&陪伴&,但我是道道地地的囚徒。汽车驶出北京的德胜门,一直向北,向北。车内除了不时的喇叭声外,再没有别的声音,没有人说话、我不知道开往何处。这是1966年下半年,我国的&史无前例&开始不久。(注:不知道当年的边区保安处一局局长师哲这时是否回忆起在延安他配合康生抓别人&特务&时的情景)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快速行驶,到了一座不高的山脚下。从山下到半山腰,筑有高高的围墙,围墙里面有几座楼房、这楼房很特别,远望去,只有几排小洞洞,大概就是&窗子&。啊:这是监狱、这就是建成不久的秦城高级监狱!在那人妖颇倒是非混淆的年月,多少革命的功臣在这里吃尽了铁窗之苦!后来,幸存下来的、原北京市公安局长、后任中央调查部副部长的冯基平说:&我要是知道我建的这座监狱是关押我自己的话、我一定会把它建得更好一些。& (注:有句成语叫&作茧自缚&)
一个无辜的人被关进四面不透风的监狱,他的心情是不言自明的。在这时,任凭他是怎样叱诧风云的人物,也变得那样软弱无力,任人摆市,屈辱、悲哀、愤怒一齐涌上心头.但也只能停在心头!
把我送进这高墙之内,我也并不太感到突然。因为在此之前,我已经坐了三年多不叫监狱的监狱。
欲加之罪 何患无词
1962年9月,正当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之际--这样的会,一向是党中央做出重大决策、喜讯频传的会议,我照例以兴奋的心情期待着......。突然,陕西省委接到中央组织部急电:&立即派人护送师哲回北京&。省委当然照办。我心里纳闷:是调我去北京?又何须&立即&& 派人护送&\'要处置我吗?处置我什么呢?尽管百思不得其解,也得服从命令。于是*陕西省委&立即&派出秘书长&护送&我到北京。不过我心里始终是坦然的、踏实的。因为我自己了解我,中央同志和毛主席都了解我。 (注:如果想起延安的事,就未必坦然)
到了北京,-下飞机,便有车接了直奔中央组织部。一向干部到此如归、倍感亲切的组织部此时却令人窒息。他们让我坐在一间屋子里休息,门外工作人员乱哄哄跑来跑去,互相打听着 &师哲到了没有&的声音,我都听得见,我更加莫明其妙,但是除了等待,还能怎样?
过了个把小时,副部长李楚离才出现在我的面前,几句问候的话之后,便陪我驱车到万寿路招待所去见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安向找介绍了十中全会情况,还谈到康生在会议上给毛主席递了个条子:&有人写小说反党&等等,接着又说明这些事都与我&无关&,调我回京,只是& 为了弄清高岗、习仲勋等人的问题。你过去接近过他们,你应该了解一些问题,你要老老实实,有啥说啥,向党交代清楚&,云云。他提的问题,可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我同高岗、习仲勋之间的关系以及全部活动;二是高、习二人都干了哪些坏事;三是我和他们一起干了哪些坏事;以及我所知道的应该向党彻底交代的所有问题。谈完后,送我回到家里。
我本着对党忠诚老实的态度,以一个党员应有的责任,想帮助党把问题弄清楚。可难就难在我找不出坏事,但为了预防自已有好坏不分的地方,只好不分好坏,凡是我知道的,-股脑儿交代,于是用几天时间,写了详尽的材料交给安子文。
在他们看材料的过程,我有三四天的空闲时间,我便利用这个时间去探望了一次老熟人王世英。此时,王世英任山西省省长,因病在北京休养(我在&披着人皮的魔鬼&一文中多次提到他所受的迫害)。他一见我十分惊讶,说我不该在此时回北京,最好立即回原驻地去。当我告诉他是中央组织部调我回来时,他傻眼了,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他想告诉我&事情不妙&,但他&有口难言&,我只呆了一会儿,他便送我几个大苹果,我明白:他既是祝我平安之意,又是告诉我该告辞了。他送我离开时,紧紧地握了我的手。不料这次见面竞成决别!
不祥之兆纷至沓来,但我仍无法情测,我能蒙受什么祸事!
三四天过后,安子文对我说:&你的交代.领导(我立即意识别这个 &领导&就是康生)看过了。但他说不行,过不了关,交不了卷(这些都是我早已听厌了的康生惯用的语言)还需要老实交代。& 安子文虽然嘴上这样说者,但我能觉察到他内心的愧疚。他口不由己啊!到了&文革 &,他也被打倒了,并被发配到安徽,当他的儿子安民去探望他时,他对孩子说:他一生做过两件昧良心的事,而第一件就是对不起帅哲。我并不怪他,他又有什么能耐不执行&领导&的指示呢?他自己也同样逃不脱厄运。
安子文这次同我谈过之后,再未露面。过了两天,由李楚离向找宣布:&自即日起,你同中央组织部再没有关系了,你的事由另外一个部门接管了。&这是在中央组织部宣布的,当时便由公安部派来的人把我接走,送到东总布胡同(原李宗仁的公馆)软禁起来。没有让我向家人告别,从此*我便从家中失踪了十几年,就在我的头上套上了&金箍&,这 &金箍&不是用符咒控制,时紧时松,而是用&螺丝& 一圈、一圈地紧箍下去的。
&唐&吉柯德&同我搏斗
自从我被软禁在东总布胡同那座楼里之后,唐&吉河德式的人物同我博斗就开始了。三年中同我&谈话&的人总有二三十人,加上前后向我要材料的将近百人。开始时还有四五位象是高级点的(副部长级)干部,一来到,先要表现出自己的非凡,但顶多一两次,就不再露面了。其中一个较低级一点的干部,说他老早就认识我,他在统战部工作过,还参加过建设民族文化官的领导工作,我们一开始交锋就搞僵了,经过几次折腾,他也不来了。可是隔了-段时间,他又出现了。这次是他一个人来的,表现得非常谦逊和蔼,声音低沉。寒喧过后,他说他对不起我,要我原谅他的粗暴,因为&领导&要求他对我要严历,他是不得已而为之,时是违心的。后来知道.那是他即将离开此项工作之前,来向我仟悔的。
接着来的像是-个局级干部,可能是从外地调来的。一开始也是来势汹汹,装腔作势,大喊大叫,拍桌打椅,以势逼人。但谈不了几句话,就思路闭塞,语言枯竭,无所措手足,一副狼狈相。我讽刺了他两句:&演&二堂会审&也没用,拍惊堂木更没用,我是蒙冤受害者,但却不是被人陷害了的苏三。&不料倒生效了。此后,他再也不敢拍拍、打打了。我从他的言谈中发现,他每次同我谈话之后,都是要向康生汇报的,然后又用康生教给他的那套来攻击我。有一次我说:&你这一套,我年在延安时,就从他的嘴里早巳听厌了,那时他就是这样教我们的,但这-套毫无用处、现在就更没商用处。还来重复这一套,岂非自找麻烦?!其所以没有用,就是因为它不科学,不实事求是。& (注:话外音&老子用这套时,你还穿开裆裤呢。&)这个可怜虫竞反问我:&在延安时你听谁说的?&我说:&你自己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如果你愿意捉迷藏,那咱们就玩个够吧。但是我要告诉你:我在延安听他讲的比你在这里说的还要多得多。不过.这一套过去就不灵,现在更不灵了:&后来有一次他自我介绍说:他在延安杨家岭会见过任弼时,但&不知为什么没有遇见你这位政治秘书?&此话他在以后还重复过几次,用意何在,不得而知。我看他很像是长征过来的老干部,执行任务坚决,但是渐渐地也就亮了底。他告诉我:康生教给他的妙诀是对我的每一句听,都要问个&为什么&,对每一句话都应该提出-万个&为什么&,使我永远回答不完。可是他试验的结果,自己也觉得十分无聊、于是我们常常只是对坐,沉默无言,哑戏一场又一场演过之后,他再也不来了。
向我问话的入越来越少,只剩下两三人,其中一位姓段的,是平山县人。他说:他从未接触和处理过像我这样一级的干部问题,&今天居然出面审近你--师哲,实在,实在......&
就这样度过了两三年,同样的话不知重复了多少次,实在无话可说了 有一次我自己提出问题,我说;&我们已经谈了很多,谈了很长时间,但一直未触及我在苏联的十五年,如果你们对这方面有什么问题,请提出来,我愿意澄清。&此人不敢表态,立即跑到楼下去打电话请示,一去两个多小时,转回来时则说:&今天没时间了,下次再谈吧!& 我明白了,他们同我谈话的范围是康生划定的,他们绝不敢越雷池一步,而康生对在苏联的一段是忌讳的(其原因见&披着人皮的魔鬼&一书) 。
过了若干天,一个上午,此人又来了。显然我要谈的问题,对康生是个威胁,他自已做贼心虚,不敢让我谈。经过策划、重新限定了范围,再把他派来。而来者却以为他掌握了新武器,神气十足地来同我博斗了。可惜他只个过是主子的传声简,他提的问题是:要我交代毛泽东同斯大林的来往关系。我问道:&是谈毛泽东和斯大林个人之间的关系?两党之间的关系?还是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而且是涉及到哪些问题和哪个时期的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还是我国新政权成立之后?&他不能问答,只是含糊地说:&关于毛主席这方面的情况。&我又问他: &是谁提出、谁委托你们谈这个问题的?&他狂妄回答说:&审查干部对谁都一样,对谁的问题都可以查问的。&我说:&你错了。不是对任何人、任何事你们都有权力、合资格审查的。&这话激怒了他,他跳起来.恶狠狠地说:&我们有权审查任何人!&于是我要求他拿出中央的特别决定,而决定必须明确写清:&中央责成师哲彻底交代毛泽东同斯大林、苏联之间的关系问题&。我说:&只要中央正式作出这样的决定,我自然交代一切。&于是他们骂我&狂妄自大&、&目空一切&、&不听从上级&等等。我也毫不示弱.便同他们对骂起来,骂累了,他们走了。
他们用的是神经战,而我取得了主动权。对骂之后他们一连五天不照面。我也只好等待,并准备着对付可能来自任何一个方而的攻击。
那两位终于又露面了,他们出现在我的面前时,一改过去那种凶神恶煞的狰狞面目,而是笑嘻嘻地向我问好,问我的健康、饮食、起居等情况,闭口不谈实质性的问题。难道我需要这些虚情假意吗&我需要的是解决问题!所以我实在忍个住了,便主动提出要谈。他们问我要谈什么?我已经意识到了上次的搏斗,我取得了胜利,索性再将他一军。于是我说:&就谈你们上次提出的:毛主席在外事方面的事情!&他们连忙声明:&不谈那个问题了,此后再也不谈涉及到那方面的事情了。& 我心里又好笑,又悲哀:可怜的无知的人啊,你们只能盲目地允当别人的棍棒!
高墙之内形形色色
1966年初,我被转移到太安候街二十几号,此处世是一个独院。在这里,他们只来过一次,而是仅仅是来看看我,问我有什么要求,健康状况如何等等。
在这里住了不到半年,又把我转送到学院胡同,这里是公安部一位干部住家的后院、前后相通。在这里住了不到两个月(即1966年下半年,&文革&席卷全国之际。不过当时我什么也不知道),便被送进了秦城监狱。后来听说这是当时任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的决定。
在秦城,我的编号是6601(即1966年第1号犯人)。这时,监狱里关押的人确实很少,许多楼房部空着。安排我的那栋大楼里空荡荡的,大约连我只有三名犯人。房间里的窗子离地而一人多高,这就是从远处看到的一排排小洞洞中的一个。
我从被软禁到关进监狱以后的一段时间内,除了精神上的摧残和压抑以外,生活上的标准仍相当高,饮食很丰富。
在这里看管我的只有一个人,此人看来是老工作人员,有经验,很老练。每天都要来几次,一会儿要我出去散步,一会儿要我去做轻微的劳动,当我做不动时,他就来帮我,人很和气,说话做事也近乎人情,有时还同我闲谈聊天。我生活上的一切要求,他大部满足了我。如我要的一个小木桌、纸张、笔组、砚台以及脸盆等用具.他都一一弄到了。有一天,在闲聊中我问他:你们这里关押的当然都是有罪的犯人,但把无辜、无罪人管在这里,这合适吗?&他回答得非常妙:&这是国家的需要&(!!!!)又以安慰口气说:&你来了,就安心地呆着吧,注意保护自己的健康。有什么要求,告诉我,凡能做到的事,我都尽力而为。 &他的话对不幸者确实是点慰藉。
但是好景不长。大约1967年11月间,来了部队,实行军管,陆陆续续接替了原来的全部管理人员。进入1968年,听说原来的瞥理人员已经全部进了&学习班&。
秦城监狱虽然&掌握&在部队一些人手里,但是他们既不会管教.也不会安排工作,而只会做一件事,就是折磨人、污辱人、骂人、搞点小动作之类。他们对所有的在押人员只会说一句话;&你是反革命&或 &你是反党分子&。若是反驳他一句,他立即反问:&不是反革命,为什么把你关在这里?!想出去,没门!&是啊,多么简单的&真理&!又是多么容易的颠倒!
已经有一年多没有人同我纠缠了&,自从这些&大兵&来到,就开始了大缘无故、无休无止的无聊折磨。他们不断地故意敲牢房的门,即使人休息的时间,也要唤醒,使人无法安宁、无法休息,饭食也只有窝窝头和咸菜了。
他们似乎把监狱当做&练兵&的现场。一天午休后*来了一批人,有穿军衣的,也有穿便衣的,但从面孔上看,并不生疏,都是军人 然而见面却却无话可说。尤其是午龄大的,当军官的话很少,而是小青年冲在前。其中一个很积极,但说不了几句就词穷了,只能不断地重复那几句话,赵不到结束点。时间就是这样被车轱辘话滚过去。
当&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响彻云霄时,我意识到弹片会落到我的身上。于是我自己争取主功,把我所了解的与刘少奇有关的事,以及我同他的往来,详详细细、清清楚楚写了-篇长长的交代材料。交出去之后,却石沉大海,毫无反应。过了大约两个多月,来了一批人,指责我 &交代不彻底&、&避重就轻&、&没有讲到点子上&等等。我请他们提出具体问题、具体要求。他们无法回答,只是一味地纠缠、加压。我明白了,并不是我争取主动就能立功的,既然存心折磨你,还能让你主动?于是新的一轮又开始了。
根据他们的要求,我把已写过的&交代&又重新写了一遍,显然仍是&交不了卷&、&过不了关&
每天来同我谈话的,全部是军人,海、陆、空、步、骑、炮,各军种各兵种都有。他们历来不提具体问题,实际上也提不出任何具体问题,而只是一个劲地、盲目地催逼、加压、谩骂。他们的意恩集中到-点,就是要我编造:&如何伙同刘少奇反对毛主席的&?当我弄清了他们的意图时,我反问道:&前不久你们花了很长时间、说我伙向高岗反对刘少奇,而现在又说我伙同刘少奇反对毛主席。试问:我到底是反对刘少奇,还是伙同刘少奇呢?&那位操着胶东口音的校级军官竟理直气壮地回答说:&这并不予盾!&真使人啼笑皆非,还能同他们说清楚一句明白话吗?
继而追问刘少奇同斯大林的&特务关系&,我反问道:&是斯大林要收买刘少奇做特务工作吗\'&回答说:&当然不是斯大林自己,而是他的特务机关这样做的&,我说:&如果你们不了解苏联,那么也可以根据我们中国的国家领导和各部委的关系做出点椎理。想一想,斯大林作为党的领袖、国家的最高领导。会亲自去做收买特务的事情吗?他们的政府官员以及其他任何人,谁敢触动斯大林的客人?!&他们茫然了。
但是,这些可怜的人,作为他人的工具,不由他不拼命地、厚颜无耻地蛮干。车轮战没有停,只是再也不敢提问题,一昧地压、逼、催。就这样持续了两个夏天。到了第二个夏天(1968年),他们日夜突击,轮番威逼,一刻不让休息。
我被关在一间小屋子里,门窗紧闭,屋内闷热,温度高达40度以上。他们打开电风扇,只对着他们自己吹,把我置于墙角,并面墙站立,不准动。这样持续了二十余天,我的两腿两脚红肿,血液下沉淤积,血管膨胀以至坏死,脚面裂开血口,然后化脓。但恶狼般的嚎叫仍不绝于耳,既不让休息,叶不让就医。这时有从&学刁班&返回来的督理人员看到我的伤势严重.请来了医生。&天哪!那位医生活像个&何仙姑& ,她站在门外老远的地方望望,问我:&你是不是害过梅毒?你这病是哪儿传染来的?这病设法治!&我要求给点消毒棉和绷带,我自己包扎,她理也不理,转身走了....
野蛮啊!有真理的却无起码的生存权利;无真理的却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种权力利用了愚昧,才能实现如此非人的野蛮行径:在这走投无路的日子里,我的确产生过自杀的念头
江河有源 事出有因
大凡人在与世诀别之际,总要回顾自己的一生,尤其是受迫害者,总要追寻到这步田地的渊源。
我在其它的回忆文章中,已经叙述过我自己种下的祸根。尤其是因为我对康生了解得太多了,所以在劫难逃。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蛛丝马迹,我都回忆起来--
1950年至1952年间,在中南海的工作人员中流传着一些闲话,主要是对刘少奇的意见。这些意见是说1949年开国大典时,江青匆勿从莫斯科赶回北京,为的是参加天安门的庆典,而毛主席坚决不允许她登上天安门城楼,然而刘少奇却把王光美带上去了。1950年毛主席从莫斯科回到北京时,他又不让江青到车站去接他,而在此之前,刘少奇从莫斯科回京时,王光美却到清华园车站迎接了刘少奇。还有其它一些不利于团结的流言菲语,都有损于诸领导的威信。我心里存不住话,实在忍不住,便直接向毛主席反映了。毛主席听了以后,耍我把自己听到的的话告诉刘少奇、周恩怼⒅斓碌韧荆饩褪刮掖蟠笪蚜恕⒂绕湟蛭抑勒庑┝餮苑朴锎蟛糠衷从诮啵渲械囊橛帜岩跃≈飨幕坝植荒芪タ埂#ㄗ涸偃媚愣嘧欤。┎坏靡眩矣沧磐菲は蛄跎倨娣从沉诵┗埃嵝阉⒁饩褪橇恕
1950年和1952年间,江青又有两次去苏联。一次是张果男陪同,一次仍是林莉陪同。江青作为主席夫人,苏联给以特殊的待遇--单独一幢小楼,中央联络部还派干部陪同,配合警卫随从、专门的医护人员和单独的小灶等等。
江青享受了这一切之后,又不满足了。主要是不满意她仅仅以主席夫人的身份出现在人前,而没有什么公职头衔,感到自己的身份不够光彩、不够辉煌。她为此所进行的活动我们不可能尽知,但我的亲闻可知其一二。
1952年初夏的一个上午,毛主席的机要秘书打电话给我,说来了两位苏联大夫,要我立刻到主席那里去。我当然不敢怠慢,可是一走进他的门,就感到气氛异常:室内一边坐的是毛泽东和江青,另一边坐的是苏联大夫和一位翻译。这位翻译我认识,是卫生部的,俄语讲得较流利。他们谈兴正浓。我立即意识到我的来临是多余的,而毛主席正以厌恶的目光盯着我。我非常尴尬。正想找个借口离开时,江青却把毛泽东拉到另一间屋子里去了。过了十多分钟,他们转回来,态度竟然大变-- 阴转阳。毛主席只是面向着我,而且只要我向他翻译,不让卫生部那位翻译插嘴。这又使我十分窘迫,但我还是表示对那位翻译的信任和敬重,我们共同商量着翻译。我很为这位翻译同志也为我自己难过。事后我了解到:机要秘行通知我去,只是照过去的常规办的。他不知道常规已发生了变化!
在1953年初夏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忽然质问:&从哪儿来的这个书记处的政治秘书室,又把他安在我的身旁?&这个政治秘书室是在西柏被时,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的。它是中央书记处各秘书集体办公的单位,经常工作是为主席、副主席们处理各界、各团体和群众来信等事宜,室主任是我,已工作了四个年头。当与会者说明这一情况时,主席又说:&那我为什么不知道呢?&大家说:&你大概忘记了。&主席又说:&我只要一个秘书小组就行了,不要那个政治秘书室。&于是当即决定另成立了秘书组,除了我以外,还是原来那斑人,只是组长由江青来担任。杨尚昆受命向我传达了这一决定之后,还加了一句;&你看这老人家,大家都知道,只有他说不知道。&其实不管采取何种方式,对离开这个工作岗位,却是为自己庆幸的。(注:外人当然不如夫人可靠)
接着,毛泽东专门宴请了秘书组的组长和副组长等人。这样,江青既有了官职,又有了政治地位,白然身份也提高了。但她只是挂个名而己,并不做什么实际工作。就是这样,她仍欲壑难填.过了一段时间,她又向主席提出了新的要求:送给毛主席的有关戏剧、电影、舞蹈等文艺类材料,要求由她批阅;接着又要求分担文艺活动方面的指导事宜。 &文革&开始时,甚至还兼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文艺顾问等职。对所有这些,毛主席都迁就了她。以后的发展,已是人所共加的了。
这里只说与我有关的事。1954年秋,江青在同一位同志的谈话中说:&要把师哲摘倒、搞垮、搞臭。&为什么却没有说。江青何以对我仇恨至此?这耍追溯到延安时期我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之时,我那时既没有满足她要工作职位的要求,又不肯给她报销一大笔没有名目的账目,为此他怀恨在心。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力面,就是因为她同康生沆瀣一气,而康生是要把一切识他庐山真目的人通统至于死地的。而最可悲的是他们当时得到毛主席的信任和使用。
年之交,一次因事到毛主席的办公家里,办完事后,他忽然对我说:&你以后再到我这里来时,不要事先经过机要秘书,不要打电话通知他们,直接来就是了,我已经告诉了哨兵不要拦挡你。&天哪!这又是怎么回事?我不仅没有受宠若惊,反而脑子里乱莲蓬一团,不知所以,只觉得后脊梁发凉。(注:竟敢怀疑领导用心不良!)过了不久,又一次会见了他,他这样对我说:&你当我的秘书好吧?&却不说什么秘书,更不说是否中央决定。我推说自己不能胜任,而他仍表示坚持,说我只是谦虚而已。这两次的会见,使我下意识地感到自己情况并不大妙。我拿定主意,一定要跳出这个是非圈子!又过了不多久,我到他办公室办完公事正要退出门时。他异乎寻常地走出来送我,并同我在颐年堂院子里来回踱步。他也边走边谈。忽然问我:俄语学院有多少学生?留苏预备部有有多少学生?我回答之后,他又问:&你不怕俄语人才过剩吗?&我听了非常诧异,因为我正承受着各方面需要俄语人才的压力,我怎能知道那么热乎的中苏关系会破裂?!于是我问答说:&我因为培养不出足够的俄语干部,不能满足工作的需要,每次在国务院的会议上都受到冲击,这过剩又从何说起呢?&他看我不开窍,不能理解他的意思,只好说:&算了吧,今天不谈这个了。&
早在1950年,任弼时同志刚刚与世长辞,康生就说过:&师哲失去了弼时这个靠山,他是难以应付下去的。从哪方面冲击他、搞倒他,这是指日可待的事!&我那时认为:&你算什么算命先生&。中苏关系出现了裂痕,康生又说:&中苏关系破裂,师哲首当其冲!&我仍认为我怎么能&等同于苏联&?
回忆到这里,想到一句俗语:'不怕贼伤,就怕贼惦记&。我是早就被康生&惦记&着了。如何能逃脱他的魔爪?
为了离开这个环境,我很费了一番苦心。如何摆脱现在的工作?怎样才能到地方上去?去哪儿?做什么?最后决定给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写信说明自己的愿往和请求,希望到地方上去做些实际工作,锻炼自己。这件事做得不周到的地方是事先没有向毛主席请示,(注:有心人啊。)而我给中央其他同志(刘少奇、朱德、周恩怼⒌诵∑降)的信又没有转报给毛主席。所以我临行前去见主席时,他大为不满。说我要离开北京,他事先不知道。我感到十分窘迫,便说:如果主席有重要指示或意见,我愿意留下来,日后再走。主席问:\'你什么时候走?&我回答:&再过两个钟头就要开车了。 &主席说:&既然这样,那你先走吧,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1957年1月,我到了济南,担任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在这里工作的期间,我才深深感到自己不了解也不适应中国的人情世故,并非仅凭积极努力的工作就能站住脚,我的处境是艰难的,但是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自己在生活上不检点,犯了错误。(注:什么错误?)这给排斥异已的势力和蓄意害我的康生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也应验了康生的预言:&师哲要陷在山东的泥潭,拔不出来。&
在处理我的问题时,康生极力插手干预。除了开除党籍之外,康生还提了三个条件:一是&要把师哲安排得远离铁路交通要道&;二是& 要割断师哲与中央的联系&;三是&要防止师哲逃跑到苏联去(?!)& 。这只有康生那特制的脑袋才能想得出来。可见对我的处理只不过是借题发挥;13年的囚徒,更与此无关。当山东省委已经决定恢复我的党籍之后,康生又给压下来,直等到十中全会的机会又进一步加有了我!
在陕西扶风农场的四五年,是我工作最愉快的时期。我潜心于畜牧、果木、水利等的经营管理和研究,没有任何精神负担,心情愉快。同时也和毛主席保持着通信联系。我把自己看到的认为带有原则性、政策性的问题,都及时写信向毛主席报告。而毛主席也数次把我的信批转到地方上,或转给总理办理。有时还让叶子龙来信转达他的话说:&你不要着急,党对你是了解的,你的党籍问题也会解决的,只是时机问题而已。&但是,康生扣压山东省委关于恢复我的党籍的决定,不知毛主席是否知道? (注:你说呢?)
生死搏斗 孤军不孤
反正我是被康生捏在手心里了,他是一定耍置我于死地而后快的。于其这样慢慢地被折磨死,还不如自杀算了,既可少受点罪,也是表示抗议。于是我千方百计收藏了一根大针、一个铁片(可以磨利刃)、一根铜丝(可以触电),再用布条搓成一根绳子(可以上吊),准备这么多,是因为哪-种方法用起来最有把握,那是要相机而行的。
就在我这一切都准备得差不多的时候,恍忽之间,似乎出现了康生的狰狞面目,并且恶狠狠地说:&就是要你死在这里!&我忽然清醒过来。我想:不能让他如愿!后来有同志告诉我:在把我送进监狱时,康生确曾说过:&师哲活着进去,但活着出不来。&
恰在这时,来了一位与众不同的青年军人,听口音是山西人。他态度平和,说话在理。他的出现,帮助我决定了活下大的勇气。我想到:自己如果不明不白地死去,谁能为我呜冤?究竟落个&自挚挂&,还是 &畏罪自杀?&为此,我也要活下去.要忍受下去。
那位山西口音的军人,前后来过五六次,每次只两个人。他们不曾用审问的口气说话,而是和蔼而忧礼貌地问寒问暖,问我的健康状况,饮食起居如何,也给我提供了医疗条件。有一次他们来找我谈话,谈话室本来有两个人,我进去以后,一个人离座走了出去,只剩下那位山西口音的青年。稍谈几句之后,我抓紧机会提出:&我有一封给毛主席的信,请你带出去,设法转呈他,可否?&他吃惊地间我:&写的什么内容?&我说是揭发康生的。他马上回答说,他带不出去,更无法呈递上去;而旦,&你也想一想,你今天所处的地位,写这样的信行吗?反正我带不出去,更不可能送到毛主席手里。想想这中转间,会送到哪儿去?恐怕不会成功,只会招来麻烦,惹起祸端。我替你着想: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讲得诚恳而有道理,于是我也就此死了这条心。我很感激他!
几天后,又来了另一批人,虽着便装、但仍能一眼看出是军人。他们一开口便问我的信写好了没有,信的内容是什么?我装作不明何所指。他们又说:&你不是要给毛主席写信吗?写好没有?我说我是同一位同志闲聊时曾说过想给毛主席写信的问题。他们又问:&什么内容?&揭发谁?&我说:&只想说说我个人的冤情。毛主席了解我,所以我想向他申诉。但并没有写成文字-&就这样算是搪塞过去了;事后我仍想起那位山西口音的同志,他提醒我是十分正确和有道理的,他是个正派人,有道德的人、我也进一步了解了自己的处境、也进一层地懂得我们党和国家正在遭受空前的劫难!
某一天,来了八九个人,似乎各兵种的都由。其中有一个青年格外的积极,抢着给我说教,搬出了许多条文,累得满头大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你不要鬼鬼崇崇,混不过去了。&他一直在重复这句话,我纠正他不要说&祟祟&,而应说&祟祟&。他回答说:&反正都一样: &还把&班门弄斧\'说成&搬门弄术&,再加上-些形象解释,我又给他纠正。真让人哭笑不得。
再一天来的似乎是一批老手,也很精灵狡猾:-进门就要我站起来朗读墙上贴的各种语录条幅,大都是从&红宝书&上摘下来的,诸如& 反对主观主义,反对教义土义,反对不实事求是、不忠诚老实、装腔作势。盛气决人、自欺欺人\'之类。我倒是很有欢庆,而逢读到&反对不实事求是&之类的语句时、故意提高声音,多读几通。其中一人总算听出了味道。要求我说明&是给自己读,还是给我们读,让我们听?&我说:&这是毛主席的话,谁都得听,谁听谁不听,我怎么知道?&他说:& 你的读法是给我们听的,&我说:&那只好大家都听吧。&此后,他们把那些语录全去掉了。这不足以说明那时叫得震天响的&无产阶级专政 &是什么货色吗?
接着,他们又向我宣布:在任何情况下,交代问题时,都不能涉及毛泽东、周恩怼⒘直肴说拿趾褪虑椋思柑欤诖沃厣暾庖辉蚴保直涑闪肆鋈耍醇由狭丝瞪⒔嗪统虏铩2⑶仪康鳎盒旁谔富爸胁唤霾荒苌孀闼堑氖拢词挂惶崴堑拿郑际欠缸铩N曳次室痪洌&如果你们提出有关他们的问题时,我如何答复?&他们说: &不会问你这类问题的。&此后,全国十亿人口中,只有六个人受到保护,似乎进入了保险库。实际上在以后的谈话中,又不能不涉及到这六个人中的某一个。遇此情况,我只好用&他&或&她&来代称,显然这就很难使他们听得明白,而他们又不敢迫问具体人的姓名。这种愚蠢的状态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期,渐渐地也就不再来纠缠了。
这期间,来了一批十八九、二十来岁的女孩子,她们的长相一个赛一个,然而她们那种无赖劲,更是一个赛一个。她们那被扭曲了的灵魂,在这里得到允分的表演。她们出言不逊,任意侮辱人,张才舞爪,推推囊囊。够了,我想起就痛心,我们文明古国,到底造就了一代什么& 新人&?I
还要说到一个文化水平极低,不懂事理.又讲不清任何一个问题的人。他一坐下来就抠脚搔痒,态度十分蛮横,却分不清是非好歹。唯有他带来的一个北大的学生,是他的依托和帮手。我前前后后被他们纠缠了十个多月,仅仅为了这样一件事:
1949年末.我陪同毛主席访苏时,斯大林建议出版(毛泽东选集),毛主席则要求他派一位哲学家来帮忙,斯大林就指派了尤金。我因翻译<毛选&,同尤金来注较多。这是人所共知的事,而且我也反复交代过了。由于毛主席的亲自安排,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曾陪同尤金遍游中华大地,并请尤金讲学。这些也是组织了解的,我也反复交代过的。唯有尤金在苏联大使馆请陆定一、林莉、张锡佑和我参加了一次午餐,这样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被我遗忘了。二个多月的车轮战、罚站、折磨,就是为了这件老。他们的提问,只是些我交代陆定一同苏联的关系、同苏联大使馆的关系。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关系&没有交代,请他们提示一下,他们不肯,只骂我&不老实&,施加了种种的折磨。 -天饭后休息时,我脑海中突然浮现出尤金请我们到苏联大使馆参加午餐一事,那是他表示感谢帮助过他工作的几位中国同志的。于是我立即找他们说了这件事,他们似乎满足了。我却不想就此罢休!我说:&你们只知道同我在无足轻重的小事情上纠缠,却不愿了解实质性的问题。&他们装腔作势说他们什么都知道。我说:&不管你们知道还是不知道,我得告诉你们:尤金是毛主席的客人,是毛主席亲自和斯大林商定后,邀请尤金来中国的。陆定-是以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身份陪同尤金周游全国的,也是毛主席安排的。尤金旅游和讲学回来以后,立即给主席写了一封汇报信,主席看了表示满意,而对陆定一回来一声不吭主席有意见。这些事你们都知道吗?怎么能怀疑我隐瞒陆定一同尤金的关系而加罪于我?!真是莫须有&
1969年秋,秦城监秋的医生忽然断言我患有恶性肿瘤,把我送到复兴医院,要求给我施行&手术&。医院接诊的是外科主任大夫(后升任院长)钱之达同志。他诊断不是肿瘤,没有必要动手术。但监狱来的人不答应,不但要求立即动手术.而旦要在手术后立即把我带回监狱去。钱大夫却本着高尚的医德和责任感,拒绝了他们的无理要求,绝不草率从事。开是他们用习惯了的&专政&态度同大夫大吵大闹了一个多小时,钱大夫是寸步不让、决不苟且,毫不动摇!那些人只好押着我转回秦城。过了两三天,又送找到医院医治。钱大夫显然意识到了,也就特别的小心谨慎。我被隔离在单人房间,用了一周的时间做各种检查和难备工作,然后顺利地做完了手术。虽然无缘无故地把我左胸脯的肉割去了半斤多,但由于钱大大的精心安排和防范.总算没有发生意外.我又一次活了下来!术后-日,便把我接回监狱。
我的身体在康复期间,食欲特别好,我自己暗暗庆幸。但不料祸从天降!一天午饭后几个小时,我开始腹部疼痛,并不断加剧,至晚则上吐下泻,头昏脑胀,不省人事。由于返回岗位的原监狱管型人员的救助,我又一次脱险。后来知道这是一次食物中毒,共有七八人,我因食欲好,是中毒最重的三个人中之一。但是怎样造成食物中毒,却始终不知。
我在监狱里好像是孤身奋斗,实际上有着许多看不见的援救之手!
直到1972年初,毛主席下了一道指示,约法三章: 一让犯人吃饱、二让犯人睡足:三没有病症时才可以审讯。并责成监狱管理人员不仅耍遵照执行,还要原原本本地向犯人传达、征求犯人意见。从此才停止了种种虐待,伙食也有所改善,由全部粗粮变成全部细粮。我已经吃惯了窝窝头,觉得馒头没有窝窝头香,可是讨耍窝窝头,也是没有。
&保险&不保 魔临末日
&保险库&里的人也并不那么保险。大约1970年初,突然来了几个人,很神秘地要我揭发、交待陈伯达的问题。讲了很多,好言相劝。我问他们:&你们这是什么意思?讲的是真话过是想捉弄我?希望你们的态度放老实点。我已经被捉弄糊涂了,被折腾够了。前不久,你们还划了个&钢铁图&,里面的六个人中就有陈伯达,是受到绝对保护的,连名字都不能提及,而今天却要我在太岁头上动土?&他们则苦苦劝说,捶胸发誓说他们不是耍圈套,而是有上级和毛主席、党中央的机密紧急指示。今天来,也还只是秘密调查、收集材料,在这里说的也还不能公开等等。我表示耍考虑两天,待弄清问题再说,他们只好答应。我又问: &那么那个钢铁图还存在不存在?&他们马上回答:&没有什么钢铁图 &我又说:&你们曾经宣布的六个人不许触及.只要触及其中任何-个人就要犯罪,还有效没有?这个罪我是犯不起的!&这使他们大伤脑筋。于是他们再次来时,把毛主席亲笔题词的复制件拿来给我看。那是几个大字和几行小字,原文已记不清了,大意是说陈伯达大闹庐山,几乎要翻天覆地.不待庐山会议开完,便不辞而去,不如所向何方。看了毛主席的题词,我答应写有关陈伯达的材料。他们嘱咐我:写好后,不可交给任何人转,只要告诉公务人员,他们自己就会来取。
我当然实事求是地,据我所知,一是一,二是二地写了材料,但他们还是不断纠缠,反复&启发& 我、提示我,授意我添油加酷。我说不能画蛇添足、弄虚作假。他们却说:&你只管写,不要你负责。&我反驳说:&这是什么话?!我写的材料,却不要我自己负责,那还行?既然你们认为可以弄虚作假、胡说乱写,那你们自己按需要去编造岂不更好么?我后来才知道,他们正是利用了我的交代,而后加以歪曲,并编造了 &中央文件&,其中说:&\'苏修特务师哲检举陈伯达......&背后结盟加上罪名,以加重陈伯达的罪过。何其卑鄙!实际公开批判陈伯达,是我写了陈伯达材料的六七个月之后开始的。
免死狐悲,唇亡齿寒。陈伯达被揪出后,可以想见康生那种危哉殆哉、战战兢兢、不可终日的鬼样了--他同陈们达的拉扯关系是水远也交代不清楚的?但是,&吾发之,吾能收之&。康生只不过大大地虚惊一场,而真正的后台却是林彪。
林彪摔死,我当时当然不会知道,但很快就来人了,来的还是那位操着胶东腔调的干部,另有二人相配。这位干部绝对没有了以往的神气,而是-副哭丧相,看到他,我也就猜出个八九。他要我揭发交代林彪的问题、我同林彪的关系等。我很乐意谈,于是兴致勃勃、滔滔不绝地向他们讲起了林彪三次访问莫斯科的情形、同高岗的会面和交谈的情形,又如何经过高岗给毛主席捎信等等。我谈得很起劲,这位干部却不耐烦,他心不在焉,听不下去,终于阻止了我的话。我十分惊讶!而他竞以十分沮丧和难过的表情说:&人都粉身碎骨了,还谈他什么?&看来,大戏快到终场了。
戏太大,尾声就不会太小。北京外语学院(前身是俄专)一批二十岁上下的青年学生也来&提审&我。我离开该校已二十多年,与他们何干? 他们由记个教师模样的人带领。从上午就来到了。监狱的工作人员对他们说:&快吃中饭了,不能提审。&饭后又说:&要放风,不能提审。 &可怜的娃娃们就这样等着。放风后,工作人员对我说:&有几个青年学生要找你谈话,但不着急,等一会儿再去。&最后带我去了,屋子里挤满了人。他们开口就宣布&纪律&,老一套,宣布完了说:&如果违反了这三条纪律,就要打烂你的狗头!&我问:&谁的头?&他们紧张了一下,其小一个说:&你的头。&我又问:&我的头怎么会长在狗身上 \'&他们无可奈何,在这里他们不敢动武。接着提了几个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 &为什么你要建议成立俄语专修馆?& 、&为什么你要把俄专的数字、图书馆、食堂等处的名称都用俄文写成?& &你任用过你的私人吗?& &张锡传是怎样到俄专的?&我说:你们太辛苦了,&看守人员在门旁听着,也忍不住鄙夷地一笑,并催促他们快点收场。其实他们并无意弄清任何问题,不过出于好奇,找借口来欣赏这座&高级监狱 &而已。
前后审问过我的,不下百十入。但真正有自己头脑的,充其量不过一二人,其余全是稀里糊涂给人当棍子。
自1972年起,由一个青年战士专管二楼犯人,他二十多岁,一口胶东话,有时同我聊聊,问长问短,表示对我很关心,我也表示愿意帮他做点什么;于是他告诉我,他们学刁抓得很紧,但常遇到困难,特别是有些引用马克思、列宁的语句,既不知道它的出处,又不能理解其意,像此类问题。想来问问我是否可以?我十分高兴地满口答应:&只要我知道的,全都告诉你。&从此,他就有时带着问题来找我进行探讨。研究过二四次以后,我问他还有什么需要我帮他做的事情?他说图书馆的<马克思思格斯全集>全都需要包上书皮,以防损坏,问我愿不愿意做这件事&我的答复当然是肯定的。于是他把书和必要的工具陆续送来。我花了几天功夫,把两套<马克思思格斯全集>几乎全部包上了书皮,并题写了书名。他很满意,对我也更关心了。有时我想吃青椒、葱、辣椒、盐、蒜、酱油、醋等等.他都想方设法给我弄来。有时厨房没有辣椒,他竞到狱外向群众讨要点来。我很感谢他,我们之间似乎形成了一种可贵的、真诚的友谊。而我的身体也迅速肥胖起来。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5月的一个早晨,这位青年招呼我收拾行李。我知道这是要释放我,因为在押犯人已有许多人出去了,每天都有成批的人出狱。他让我把公物全部整理出来,只带居于我私人的。那条大棉被,是监狱发的,但归个人所有了,他极力劝我带上,并动手替我包装。但是我想的是:&把一切屈辱的痕迹都留在这里&。所以坚决不要。现在想起来,也许他是对的,我没有留下半点铁窗的&纪念品&,他把我的行李搬到监狱的大门口,装上汽车,然后站在高台尚: ......我们的友谊再深,此时此地,他却不能挽留,他表情凄惨,心事重重地向我再三招手送别;我也同样,几次回首......
在监狱的十多年中.我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拿我自己的俄义版&列宁全集>对照狱中图书馆的中文版&列宁全集>.从头至尾校对一遍,开始时,由于管理人员不懂俄文、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所以不许我看。当我向他们解释这是&列宁全集>时,他们便没有理由禁止我了。我发现第28卷以后的各卷误译甚多,有的我批在书上,有的作了记录,出狱后把我的意见告诉了编译局。
重见天日 痈定思痛
十几年与世隔绝,社会和家庭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人们的观念和语言的变化。我只要开口讲话,孩子们就笑我,别人也瞪着奇异的目光看我,好像我是个外星人,是个怪物.这是后话。
再说我虽从监狱出来了,但&案子&并没有结束,而是移交给公安部第一专案组继续审理结案。我呢?依旧被流放到陕西扶风,在扶风又待了三年。
在这三年中,给我的案子做了六次结论: 主要是办案人员想不开,总不愿意这十几年白辛苦了,于是纠缠不休,然而谎言终归不能成为事实。他们起草的&结论&上的胡言乱语一个一个被否定之后,只剩下一个费德林,死抓住他不放,把他作入我&里通外国,勾结苏修特务& 的罪证,坚持要写在结论中(费德林和尤金-样是毛主席的客人,也是向我一起翻译<毛泽东选集>的。有一次他们为此事来到扶风时,正值我的小女儿明朗来看望我,她在旁插话说:&难道给毛主席做事也有罪吗 \'!&他们顿时哑口无言,无所措手足。啊!这就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小青年!以后他们来谈话,就不许我的女儿在场,无理者却有权!
直到1979年初,一切专案统统移交中央组织部,在胡耀邦同志主持下,很快给我了最后的结论--&经13年审查,没问题&。
没问题I没问题为什么要扣我关在监狱,泡了13年?加上前后流放的5年,共18年。18年,人生能有几个能有几个18年?!对我个人来说,蹲监狱或许还是一种幸运,如果在外面,恐怕早就落得跟王世英- 样被活活打死的结果,可是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和我们相同或相近命运的人还有多少?数得清吗?而实际上真正暗藏在我们心腹之中的奸人、反革命分子,只有康生、江青之类极少数几个人,怎么就会弄得人妖颠倒如此程度?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几乎朝朝代代都不乏忠奸颠倒的事例,而&文革\'则在中国历史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一切悲剧的根源是什么?如果不真正汲取教训、还可能踏上蹈撤!
阅读:293 次}
网站防火墙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已被网站管理员设置拦截!
可能原因:您对该页面的访问过于频繁
如何解决:
1)稍等一段时间重新访问;
2)如网站托管,请联系空间提供商;
3)普通网站访客,清理浏览器Cookie之后重新访问,或直接联系网站管理员;&>>&&>>& >>
《只要能把贪官送进监狱,我愿意首先进监狱》
日 09:02&来源:深港在线综合&&
2014年6月,湖南永州干部陈景云先后在网上发布《一个来自基层干部的自我忏悔》、《只要能把贪官送进监狱,我愿意首先进监狱》等网帖,自称吃空 饷7年,诈 骗 国 家20多万元。
不想当官了才举报的
记者:您之前吃了多久的空饷?
陈景云:有7年,每个月3000的样子,20多万。
记者:当时为什么想到要举报?
陈景云:看到这么大批干部吃空饷,不上班,既是对国家是一种损失,也影响了干部们的工作积极性。我们45岁以后&改非&的不上班,有的干
部不上班,有的交点钱也不上班,我觉得不符合国家的政策、法规。另外,退下来之前,我就对&改非&这个事情有看法,中央没有政策,法律
没有依据,零陵区这么搞是不对吧?还有我儿子得不到收治。他是重度精神病患者,都打人了,还不能收治,我不理解。
记者:那您觉得区政府对您&改非&,主要是因为什么呢?
陈景云:关系好的,在45岁之前就把他提拔了,有的在&改非&的时候提拔到公司当老总了。& 改非&是什么道理?我就是讨要一个说法。
记者:网上有人说,您是因为被罢了官职,心里不服,而选择的一种&报复&行为,是这样吗?
陈景云:不是这个样子的。当时&改非&的时候,领导不是说不用我了,当时承诺是当公司一把手的。
记者:区政府一直给您各种形式的补偿,为何当时不接受?
陈景云:看到干部队伍比较乱,想想自己走过的路,当时心里不好受。凭关系用干部,很多没有能力的人,水平一般的也被提上来了,看不惯这些。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我当官了,他们会刺激我的。我不考虑当官了,我才举报的。
记者:举报,想要达到什么结果?
陈景云:对腐败分子惩罚,改变零陵区干部的作风问题。零陵区为什么会有唐慧的案子?这跟干部的作风是有很大关系的。也希望上级给予我儿子一些人文关怀吧,因为我身体也越来越不好了,他妈妈也走了,我儿子怎么办呀?
记者:如果没有被&改非&,您还会这么做吗?
陈景云:也会反映的。在&改非&之前,我就向上级反映过零陵区的腐败问题。
网友有话说
版权与免责声明:
①凡本网注明"来源:深港在线综合"的所有作品,均由本网编辑搜集整理,并加入大量个人点评、观点、配图等内容,版权均属于深港在线,未经本网许可,禁止转载,违反者本网将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②本网转载并注明自其它来源的作品,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不承担此类作品侵权行为的直接责任及连带责任。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网转载时,必须保留本网注明的作品来源,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
③如涉及作品内容、版权等问题,请在作品发表之日起一周内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在您联系我们之后24小时内予以删除,否则视为放弃相关权利。师哲:秦城监狱的6601号犯人
师哲:秦城监狱的6601号犯人
中华师氏网 日
师哲:秦城监狱的6601号犯人
一辆公安的囚车--不是现在那种警笛鸣叫的囚车,而是一辆普通的小卧车,但它是道道地地的囚车。囚犯就是我。我没有被戴上手铐而是像一位首长一样坐在车内,两旁有人&陪伴&,但我是道道地地的囚徒。汽车驶出北京的德胜门,一直向北,向北。车内除了不时的喇叭声外,再没有别的声音,没有人说话、我不知道开往何处。这是1966年下半年,我国的&史无前例&开始不久。(注:不知道当年的边区保安处一局局长师哲这时是否回忆起在延安他配合康生抓别人&特务&时的情景)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快速行驶,到了一座不高的山脚下。从山下到半山腰,筑有高高的围墙,围墙里面有几座楼房、这楼房很特别,远望去,只有几排小洞洞,大概就是&窗子&。啊:这是监狱、这就是建成不久的秦城高级监狱!在那人妖颇倒是非混淆的年月,多少革命的功臣在这里吃尽了铁窗之苦!后来,幸存下来的、原北京市公安局长、后任中央调查部副部长的冯基平说:&我要是知道我建的这座监狱是关押我自己的话、我一定会把它建得更好一些。& (注:有句成语叫&作茧自缚&)
一个无辜的人被关进四面不透风的监狱,他的心情是不言自明的。在这时,任凭他是怎样叱诧风云的人物,也变得那样软弱无力,任人摆市,屈辱、悲哀、愤怒一齐涌上心头.但也只能停在心头!
把我送进这高墙之内,我也并不太感到突然。因为在此之前,我已经坐了三年多不叫监狱的监狱。
欲加之罪 何患无词
1962年9月,正当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之际--这样的会,一向是党中央做出重大决策、喜讯频传的会议,我照例以兴奋的心情期待着......。突然,陕西省委接到中央组织部急电:&立即派人护送师哲回北京&。省委当然照办。我心里纳闷:是调我去北京?又何须&立即&& 派人护送&\'要处置我吗?处置我什么呢?尽管百思不得其解,也得服从命令。于是*陕西省委&立即&派出秘书长&护送&我到北京。不过我心里始终是坦然的、踏实的。因为我自己了解我,中央同志和毛主席都了解我。 (注:如果想起延安的事,就未必坦然)
到了北京,-下飞机,便有车接了直奔中央组织部。一向干部到此如归、倍感亲切的组织部此时却令人窒息。他们让我坐在一间屋子里休息,门外工作人员乱哄哄跑来跑去,互相打听着 &师哲到了没有&的声音,我都听得见,我更加莫明其妙,但是除了等待,还能怎样?
过了个把小时,副部长李楚离才出现在我的面前,几句问候的话之后,便陪我驱车到万寿路招待所去见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安向找介绍了十中全会情况,还谈到康生在会议上给毛主席递了个条子:&有人写小说反党&等等,接着又说明这些事都与我&无关&,调我回京,只是& 为了弄清高岗、习仲勋等人的问题。你过去接近过他们,你应该了解一些问题,你要老老实实,有啥说啥,向党交代清楚&,云云。他提的问题,可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我同高岗、习仲勋之间的关系以及全部活动;二是高、习二人都干了哪些坏事;三是我和他们一起干了哪些坏事;以及我所知道的应该向党彻底交代的所有问题。谈完后,送我回到家里。
我本着对党忠诚老实的态度,以一个党员应有的责任,想帮助党把问题弄清楚。可难就难在我找不出坏事,但为了预防自已有好坏不分的地方,只好不分好坏,凡是我知道的,-股脑儿交代,于是用几天时间,写了详尽的材料交给安子文。
在他们看材料的过程,我有三四天的空闲时间,我便利用这个时间去探望了一次老熟人王世英。此时,王世英任山西省省长,因病在北京休养(我在&披着人皮的魔鬼&一文中多次提到他所受的迫害)。他一见我十分惊讶,说我不该在此时回北京,最好立即回原驻地去。当我告诉他是中央组织部调我回来时,他傻眼了,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他想告诉我&事情不妙&,但他&有口难言&,我只呆了一会儿,他便送我几个大苹果,我明白:他既是祝我平安之意,又是告诉我该告辞了。他送我离开时,紧紧地握了我的手。不料这次见面竞成决别!
不祥之兆纷至沓来,但我仍无法情测,我能蒙受什么祸事!
三四天过后,安子文对我说:&你的交代.领导(我立即意识别这个 &领导&就是康生)看过了。但他说不行,过不了关,交不了卷(这些都是我早已听厌了的康生惯用的语言)还需要老实交代。& 安子文虽然嘴上这样说者,但我能觉察到他内心的愧疚。他口不由己啊!到了&文革 &,他也被打倒了,并被发配到安徽,当他的儿子安民去探望他时,他对孩子说:他一生做过两件昧良心的事,而第一件就是对不起帅哲。我并不怪他,他又有什么能耐不执行&领导&的指示呢?他自己也同样逃不脱厄运。
安子文这次同我谈过之后,再未露面。过了两天,由李楚离向找宣布:&自即日起,你同中央组织部再没有关系了,你的事由另外一个部门接管了。&这是在中央组织部宣布的,当时便由公安部派来的人把我接走,送到东总布胡同(原李宗仁的公馆)软禁起来。没有让我向家人告别,从此*我便从家中失踪了十几年,就在我的头上套上了&金箍&,这 &金箍&不是用符咒控制,时紧时松,而是用&螺丝& 一圈、一圈地紧箍下去的。
&唐&吉柯德&同我搏斗
自从我被软禁在东总布胡同那座楼里之后,唐&吉河德式的人物同我博斗就开始了。三年中同我&谈话&的人总有二三十人,加上前后向我要材料的将近百人。开始时还有四五位象是高级点的(副部长级)干部,一来到,先要表现出自己的非凡,但顶多一两次,就不再露面了。其中一个较低级一点的干部,说他老早就认识我,他在统战部工作过,还参加过建设民族文化官的领导工作,我们一开始交锋就搞僵了,经过几次折腾,他也不来了。可是隔了-段时间,他又出现了。这次是他一个人来的,表现得非常谦逊和蔼,声音低沉。寒喧过后,他说他对不起我,要我原谅他的粗暴,因为&领导&要求他对我要严历,他是不得已而为之,时是违心的。后来知道.那是他即将离开此项工作之前,来向我仟悔的。
接着来的像是-个局级干部,可能是从外地调来的。一开始也是来势汹汹,装腔作势,大喊大叫,拍桌打椅,以势逼人。但谈不了几句话,就思路闭塞,语言枯竭,无所措手足,一副狼狈相。我讽刺了他两句:&演&二堂会审&也没用,拍惊堂木更没用,我是蒙冤受害者,但却不是被人陷害了的苏三。&不料倒生效了。此后,他再也不敢拍拍、打打了。我从他的言谈中发现,他每次同我谈话之后,都是要向康生汇报的,然后又用康生教给他的那套来攻击我。有一次我说:&你这一套,我年在延安时,就从他的嘴里早巳听厌了,那时他就是这样教我们的,但这-套毫无用处、现在就更没商用处。还来重复这一套,岂非自找麻烦?!其所以没有用,就是因为它不科学,不实事求是。& (注:话外音&老子用这套时,你还穿开裆裤呢。&)这个可怜虫竞反问我:&在延安时你听谁说的?&我说:&你自己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如果你愿意捉迷藏,那咱们就玩个够吧。但是我要告诉你:我在延安听他讲的比你在这里说的还要多得多。不过.这一套过去就不灵,现在更不灵了:&后来有一次他自我介绍说:他在延安杨家岭会见过任弼时,但&不知为什么没有遇见你这位政治秘书?&此话他在以后还重复过几次,用意何在,不得而知。我看他很像是长征过来的老干部,执行任务坚决,但是渐渐地也就亮了底。他告诉我:康生教给他的妙诀是对我的每一句听,都要问个&为什么&,对每一句话都应该提出-万个&为什么&,使我永远回答不完。可是他试验的结果,自己也觉得十分无聊、于是我们常常只是对坐,沉默无言,哑戏一场又一场演过之后,他再也不来了。
向我问话的入越来越少,只剩下两三人,其中一位姓段的,是平山县人。他说:他从未接触和处理过像我这样一级的干部问题,&今天居然出面审近你--师哲,实在,实在......&
就这样度过了两三年,同样的话不知重复了多少次,实在无话可说了 有一次我自己提出问题,我说;&我们已经谈了很多,谈了很长时间,但一直未触及我在苏联的十五年,如果你们对这方面有什么问题,请提出来,我愿意澄清。&此人不敢表态,立即跑到楼下去打电话请示,一去两个多小时,转回来时则说:&今天没时间了,下次再谈吧!& 我明白了,他们同我谈话的范围是康生划定的,他们绝不敢越雷池一步,而康生对在苏联的一段是忌讳的(其原因见&披着人皮的魔鬼&一书) 。
过了若干天,一个上午,此人又来了。显然我要谈的问题,对康生是个威胁,他自已做贼心虚,不敢让我谈。经过策划、重新限定了范围,再把他派来。而来者却以为他掌握了新武器,神气十足地来同我博斗了。可惜他只个过是主子的传声简,他提的问题是:要我交代毛泽东同斯大林的来往关系。我问道:&是谈毛泽东和斯大林个人之间的关系?两党之间的关系?还是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而且是涉及到哪些问题和哪个时期的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还是我国新政权成立之后?&他不能问答,只是含糊地说:&关于毛主席这方面的情况。&我又问他: &是谁提出、谁委托你们谈这个问题的?&他狂妄回答说:&审查干部对谁都一样,对谁的问题都可以查问的。&我说:&你错了。不是对任何人、任何事你们都有权力、合资格审查的。&这话激怒了他,他跳起来.恶狠狠地说:&我们有权审查任何人!&于是我要求他拿出中央的特别决定,而决定必须明确写清:&中央责成师哲彻底交代毛泽东同斯大林、苏联之间的关系问题&。我说:&只要中央正式作出这样的决定,我自然交代一切。&于是他们骂我&狂妄自大&、&目空一切&、&不听从上级&等等。我也毫不示弱.便同他们对骂起来,骂累了,他们走了。
他们用的是神经战,而我取得了主动权。对骂之后他们一连五天不照面。我也只好等待,并准备着对付可能来自任何一个方而的攻击。
那两位终于又露面了,他们出现在我的面前时,一改过去那种凶神恶煞的狰狞面目,而是笑嘻嘻地向我问好,问我的健康、饮食、起居等情况,闭口不谈实质性的问题。难道我需要这些虚情假意吗&我需要的是解决问题!所以我实在忍个住了,便主动提出要谈。他们问我要谈什么?我已经意识到了上次的搏斗,我取得了胜利,索性再将他一军。于是我说:&就谈你们上次提出的:毛主席在外事方面的事情!&他们连忙声明:&不谈那个问题了,此后再也不谈涉及到那方面的事情了。& 我心里又好笑,又悲哀:可怜的无知的人啊,你们只能盲目地允当别人的棍棒!
高墙之内形形色色
1966年初,我被转移到太安候街二十几号,此处世是一个独院。在这里,他们只来过一次,而是仅仅是来看看我,问我有什么要求,健康状况如何等等。
在这里住了不到半年,又把我转送到学院胡同,这里是公安部一位干部住家的后院、前后相通。在这里住了不到两个月(即1966年下半年,&文革&席卷全国之际。不过当时我什么也不知道),便被送进了秦城监狱。后来听说这是当时任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的决定。
在秦城,我的编号是6601(即1966年第1号犯人)。这时,监狱里关押的人确实很少,许多楼房部空着。安排我的那栋大楼里空荡荡的,大约连我只有三名犯人。房间里的窗子离地而一人多高,这就是从远处看到的一排排小洞洞中的一个。
我从被软禁到关进监狱以后的一段时间内,除了精神上的摧残和压抑以外,生活上的标准仍相当高,饮食很丰富。
在这里看管我的只有一个人,此人看来是老工作人员,有经验,很老练。每天都要来几次,一会儿要我出去散步,一会儿要我去做轻微的劳动,当我做不动时,他就来帮我,人很和气,说话做事也近乎人情,有时还同我闲谈聊天。我生活上的一切要求,他大部满足了我。如我要的一个小木桌、纸张、笔组、砚台以及脸盆等用具.他都一一弄到了。有一天,在闲聊中我问他:你们这里关押的当然都是有罪的犯人,但把无辜、无罪人管在这里,这合适吗?&他回答得非常妙:&这是国家的需要&(!!!!)又以安慰口气说:&你来了,就安心地呆着吧,注意保护自己的健康。有什么要求,告诉我,凡能做到的事,我都尽力而为。 &他的话对不幸者确实是点慰藉。
但是好景不长。大约1967年11月间,来了部队,实行军管,陆陆续续接替了原来的全部管理人员。进入1968年,听说原来的瞥理人员已经全部进了&学习班&。
秦城监狱虽然&掌握&在部队一些人手里,但是他们既不会管教.也不会安排工作,而只会做一件事,就是折磨人、污辱人、骂人、搞点小动作之类。他们对所有的在押人员只会说一句话;&你是反革命&或 &你是反党分子&。若是反驳他一句,他立即反问:&不是反革命,为什么把你关在这里?!想出去,没门!&是啊,多么简单的&真理&!又是多么容易的颠倒!
已经有一年多没有人同我纠缠了&,自从这些&大兵&来到,就开始了大缘无故、无休无止的无聊折磨。他们不断地故意敲牢房的门,即使人休息的时间,也要唤醒,使人无法安宁、无法休息,饭食也只有窝窝头和咸菜了。
他们似乎把监狱当做&练兵&的现场。一天午休后*来了一批人,有穿军衣的,也有穿便衣的,但从面孔上看,并不生疏,都是军人 然而见面却却无话可说。尤其是午龄大的,当军官的话很少,而是小青年冲在前。其中一个很积极,但说不了几句就词穷了,只能不断地重复那几句话,赵不到结束点。时间就是这样被车轱辘话滚过去。
当&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响彻云霄时,我意识到弹片会落到我的身上。于是我自己争取主功,把我所了解的与刘少奇有关的事,以及我同他的往来,详详细细、清清楚楚写了-篇长长的交代材料。交出去之后,却石沉大海,毫无反应。过了大约两个多月,来了一批人,指责我 &交代不彻底&、&避重就轻&、&没有讲到点子上&等等。我请他们提出具体问题、具体要求。他们无法回答,只是一味地纠缠、加压。我明白了,并不是我争取主动就能立功的,既然存心折磨你,还能让你主动?于是新的一轮又开始了。
根据他们的要求,我把已写过的&交代&又重新写了一遍,显然仍是&交不了卷&、&过不了关&
每天来同我谈话的,全部是军人,海、陆、空、步、骑、炮,各军种各兵种都有。他们历来不提具体问题,实际上也提不出任何具体问题,而只是一个劲地、盲目地催逼、加压、谩骂。他们的意恩集中到-点,就是要我编造:&如何伙同刘少奇反对毛主席的&?当我弄清了他们的意图时,我反问道:&前不久你们花了很长时间、说我伙向高岗反对刘少奇,而现在又说我伙同刘少奇反对毛主席。试问:我到底是反对刘少奇,还是伙同刘少奇呢?&那位操着胶东口音的校级军官竟理直气壮地回答说:&这并不予盾!&真使人啼笑皆非,还能同他们说清楚一句明白话吗?
继而追问刘少奇同斯大林的&特务关系&,我反问道:&是斯大林要收买刘少奇做特务工作吗\'&回答说:&当然不是斯大林自己,而是他的特务机关这样做的&,我说:&如果你们不了解苏联,那么也可以根据我们中国的国家领导和各部委的关系做出点椎理。想一想,斯大林作为党的领袖、国家的最高领导。会亲自去做收买特务的事情吗?他们的政府官员以及其他任何人,谁敢触动斯大林的客人?!&他们茫然了。
但是,这些可怜的人,作为他人的工具,不由他不拼命地、厚颜无耻地蛮干。车轮战没有停,只是再也不敢提问题,一昧地压、逼、催。就这样持续了两个夏天。到了第二个夏天(1968年),他们日夜突击,轮番威逼,一刻不让休息。
我被关在一间小屋子里,门窗紧闭,屋内闷热,温度高达40度以上。他们打开电风扇,只对着他们自己吹,把我置于墙角,并面墙站立,不准动。这样持续了二十余天,我的两腿两脚红肿,血液下沉淤积,血管膨胀以至坏死,脚面裂开血口,然后化脓。但恶狼般的嚎叫仍不绝于耳,既不让休息,叶不让就医。这时有从&学刁班&返回来的督理人员看到我的伤势严重.请来了医生。&天哪!那位医生活像个&何仙姑& ,她站在门外老远的地方望望,问我:&你是不是害过梅毒?你这病是哪儿传染来的?这病设法治!&我要求给点消毒棉和绷带,我自己包扎,她理也不理,转身走了....
野蛮啊!有真理的却无起码的生存权利;无真理的却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种权力利用了愚昧,才能实现如此非人的野蛮行径:在这走投无路的日子里,我的确产生过自杀的念头
江河有源 事出有因
大凡人在与世诀别之际,总要回顾自己的一生,尤其是受迫害者,总要追寻到这步田地的渊源。
我在其它的回忆文章中,已经叙述过我自己种下的祸根。尤其是因为我对康生了解得太多了,所以在劫难逃。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蛛丝马迹,我都回忆起来--
1950年至1952年间,在中南海的工作人员中流传着一些闲话,主要是对刘少奇的意见。这些意见是说1949年开国大典时,江青匆勿从莫斯科赶回北京,为的是参加天安门的庆典,而毛主席坚决不允许她登上天安门城楼,然而刘少奇却把王光美带上去了。1950年毛主席从莫斯科回到北京时,他又不让江青到车站去接他,而在此之前,刘少奇从莫斯科回京时,王光美却到清华园车站迎接了刘少奇。还有其它一些不利于团结的流言菲语,都有损于诸领导的威信。我心里存不住话,实在忍不住,便直接向毛主席反映了。毛主席听了以后,耍我把自己听到的的话告诉刘少奇、周恩怼⒅斓碌韧荆饩褪刮掖蟠笪蚜恕⒂绕湟蛭抑勒庑┝餮苑朴锎蟛糠衷从诮啵渲械囊橛帜岩跃≈飨幕坝植荒芪タ埂#ㄗ涸偃媚愣嘧欤。┎坏靡眩矣沧磐菲は蛄跎倨娣从沉诵┗埃嵝阉⒁饩褪橇恕
1950年和1952年间,江青又有两次去苏联。一次是张果男陪同,一次仍是林莉陪同。江青作为主席夫人,苏联给以特殊的待遇--单独一幢小楼,中央联络部还派干部陪同,配合警卫随从、专门的医护人员和单独的小灶等等。
江青享受了这一切之后,又不满足了。主要是不满意她仅仅以主席夫人的身份出现在人前,而没有什么公职头衔,感到自己的身份不够光彩、不够辉煌。她为此所进行的活动我们不可能尽知,但我的亲闻可知其一二。
1952年初夏的一个上午,毛主席的机要秘书打电话给我,说来了两位苏联大夫,要我立刻到主席那里去。我当然不敢怠慢,可是一走进他的门,就感到气氛异常:室内一边坐的是毛泽东和江青,另一边坐的是苏联大夫和一位翻译。这位翻译我认识,是卫生部的,俄语讲得较流利。他们谈兴正浓。我立即意识到我的来临是多余的,而毛主席正以厌恶的目光盯着我。我非常尴尬。正想找个借口离开时,江青却把毛泽东拉到另一间屋子里去了。过了十多分钟,他们转回来,态度竟然大变-- 阴转阳。毛主席只是面向着我,而且只要我向他翻译,不让卫生部那位翻译插嘴。这又使我十分窘迫,但我还是表示对那位翻译的信任和敬重,我们共同商量着翻译。我很为这位翻译同志也为我自己难过。事后我了解到:机要秘行通知我去,只是照过去的常规办的。他不知道常规已发生了变化!
在1953年初夏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忽然质问:&从哪儿来的这个书记处的政治秘书室,又把他安在我的身旁?&这个政治秘书室是在西柏被时,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的。它是中央书记处各秘书集体办公的单位,经常工作是为主席、副主席们处理各界、各团体和群众来信等事宜,室主任是我,已工作了四个年头。当与会者说明这一情况时,主席又说:&那我为什么不知道呢?&大家说:&你大概忘记了。&主席又说:&我只要一个秘书小组就行了,不要那个政治秘书室。&于是当即决定另成立了秘书组,除了我以外,还是原来那斑人,只是组长由江青来担任。杨尚昆受命向我传达了这一决定之后,还加了一句;&你看这老人家,大家都知道,只有他说不知道。&其实不管采取何种方式,对离开这个工作岗位,却是为自己庆幸的。(注:外人当然不如夫人可靠)
接着,毛泽东专门宴请了秘书组的组长和副组长等人。这样,江青既有了官职,又有了政治地位,白然身份也提高了。但她只是挂个名而己,并不做什么实际工作。就是这样,她仍欲壑难填.过了一段时间,她又向主席提出了新的要求:送给毛主席的有关戏剧、电影、舞蹈等文艺类材料,要求由她批阅;接着又要求分担文艺活动方面的指导事宜。 &文革&开始时,甚至还兼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文艺顾问等职。对所有这些,毛主席都迁就了她。以后的发展,已是人所共加的了。
这里只说与我有关的事。1954年秋,江青在同一位同志的谈话中说:&要把师哲摘倒、搞垮、搞臭。&为什么却没有说。江青何以对我仇恨至此?这耍追溯到延安时期我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之时,我那时既没有满足她要工作职位的要求,又不肯给她报销一大笔没有名目的账目,为此他怀恨在心。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力面,就是因为她同康生沆瀣一气,而康生是要把一切识他庐山真目的人通统至于死地的。而最可悲的是他们当时得到毛主席的信任和使用。
年之交,一次因事到毛主席的办公家里,办完事后,他忽然对我说:&你以后再到我这里来时,不要事先经过机要秘书,不要打电话通知他们,直接来就是了,我已经告诉了哨兵不要拦挡你。&天哪!这又是怎么回事?我不仅没有受宠若惊,反而脑子里乱莲蓬一团,不知所以,只觉得后脊梁发凉。(注:竟敢怀疑领导用心不良!)过了不久,又一次会见了他,他这样对我说:&你当我的秘书好吧?&却不说什么秘书,更不说是否中央决定。我推说自己不能胜任,而他仍表示坚持,说我只是谦虚而已。这两次的会见,使我下意识地感到自己情况并不大妙。我拿定主意,一定要跳出这个是非圈子!又过了不多久,我到他办公室办完公事正要退出门时。他异乎寻常地走出来送我,并同我在颐年堂院子里来回踱步。他也边走边谈。忽然问我:俄语学院有多少学生?留苏预备部有有多少学生?我回答之后,他又问:&你不怕俄语人才过剩吗?&我听了非常诧异,因为我正承受着各方面需要俄语人才的压力,我怎能知道那么热乎的中苏关系会破裂?!于是我问答说:&我因为培养不出足够的俄语干部,不能满足工作的需要,每次在国务院的会议上都受到冲击,这过剩又从何说起呢?&他看我不开窍,不能理解他的意思,只好说:&算了吧,今天不谈这个了。&
早在1950年,任弼时同志刚刚与世长辞,康生就说过:&师哲失去了弼时这个靠山,他是难以应付下去的。从哪方面冲击他、搞倒他,这是指日可待的事!&我那时认为:&你算什么算命先生&。中苏关系出现了裂痕,康生又说:&中苏关系破裂,师哲首当其冲!&我仍认为我怎么能&等同于苏联&?
回忆到这里,想到一句俗语:'不怕贼伤,就怕贼惦记&。我是早就被康生&惦记&着了。如何能逃脱他的魔爪?
为了离开这个环境,我很费了一番苦心。如何摆脱现在的工作?怎样才能到地方上去?去哪儿?做什么?最后决定给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写信说明自己的愿往和请求,希望到地方上去做些实际工作,锻炼自己。这件事做得不周到的地方是事先没有向毛主席请示,(注:有心人啊。)而我给中央其他同志(刘少奇、朱德、周恩怼⒌诵∑降)的信又没有转报给毛主席。所以我临行前去见主席时,他大为不满。说我要离开北京,他事先不知道。我感到十分窘迫,便说:如果主席有重要指示或意见,我愿意留下来,日后再走。主席问:\'你什么时候走?&我回答:&再过两个钟头就要开车了。 &主席说:&既然这样,那你先走吧,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1957年1月,我到了济南,担任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在这里工作的期间,我才深深感到自己不了解也不适应中国的人情世故,并非仅凭积极努力的工作就能站住脚,我的处境是艰难的,但是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自己在生活上不检点,犯了错误。(注:什么错误?)这给排斥异已的势力和蓄意害我的康生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也应验了康生的预言:&师哲要陷在山东的泥潭,拔不出来。&
在处理我的问题时,康生极力插手干预。除了开除党籍之外,康生还提了三个条件:一是&要把师哲安排得远离铁路交通要道&;二是& 要割断师哲与中央的联系&;三是&要防止师哲逃跑到苏联去(?!)& 。这只有康生那特制的脑袋才能想得出来。可见对我的处理只不过是借题发挥;13年的囚徒,更与此无关。当山东省委已经决定恢复我的党籍之后,康生又给压下来,直等到十中全会的机会又进一步加有了我!
在陕西扶风农场的四五年,是我工作最愉快的时期。我潜心于畜牧、果木、水利等的经营管理和研究,没有任何精神负担,心情愉快。同时也和毛主席保持着通信联系。我把自己看到的认为带有原则性、政策性的问题,都及时写信向毛主席报告。而毛主席也数次把我的信批转到地方上,或转给总理办理。有时还让叶子龙来信转达他的话说:&你不要着急,党对你是了解的,你的党籍问题也会解决的,只是时机问题而已。&但是,康生扣压山东省委关于恢复我的党籍的决定,不知毛主席是否知道? (注:你说呢?)
生死搏斗 孤军不孤
反正我是被康生捏在手心里了,他是一定耍置我于死地而后快的。于其这样慢慢地被折磨死,还不如自杀算了,既可少受点罪,也是表示抗议。于是我千方百计收藏了一根大针、一个铁片(可以磨利刃)、一根铜丝(可以触电),再用布条搓成一根绳子(可以上吊),准备这么多,是因为哪-种方法用起来最有把握,那是要相机而行的。
就在我这一切都准备得差不多的时候,恍忽之间,似乎出现了康生的狰狞面目,并且恶狠狠地说:&就是要你死在这里!&我忽然清醒过来。我想:不能让他如愿!后来有同志告诉我:在把我送进监狱时,康生确曾说过:&师哲活着进去,但活着出不来。&
恰在这时,来了一位与众不同的青年军人,听口音是山西人。他态度平和,说话在理。他的出现,帮助我决定了活下大的勇气。我想到:自己如果不明不白地死去,谁能为我呜冤?究竟落个&自挚挂&,还是 &畏罪自杀?&为此,我也要活下去.要忍受下去。
那位山西口音的军人,前后来过五六次,每次只两个人。他们不曾用审问的口气说话,而是和蔼而忧礼貌地问寒问暖,问我的健康状况,饮食起居如何,也给我提供了医疗条件。有一次他们来找我谈话,谈话室本来有两个人,我进去以后,一个人离座走了出去,只剩下那位山西口音的青年。稍谈几句之后,我抓紧机会提出:&我有一封给毛主席的信,请你带出去,设法转呈他,可否?&他吃惊地间我:&写的什么内容?&我说是揭发康生的。他马上回答说,他带不出去,更无法呈递上去;而旦,&你也想一想,你今天所处的地位,写这样的信行吗?反正我带不出去,更不可能送到毛主席手里。想想这中转间,会送到哪儿去?恐怕不会成功,只会招来麻烦,惹起祸端。我替你着想: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讲得诚恳而有道理,于是我也就此死了这条心。我很感激他!
几天后,又来了另一批人,虽着便装、但仍能一眼看出是军人。他们一开口便问我的信写好了没有,信的内容是什么?我装作不明何所指。他们又说:&你不是要给毛主席写信吗?写好没有?我说我是同一位同志闲聊时曾说过想给毛主席写信的问题。他们又问:&什么内容?&揭发谁?&我说:&只想说说我个人的冤情。毛主席了解我,所以我想向他申诉。但并没有写成文字-&就这样算是搪塞过去了;事后我仍想起那位山西口音的同志,他提醒我是十分正确和有道理的,他是个正派人,有道德的人、我也进一步了解了自己的处境、也进一层地懂得我们党和国家正在遭受空前的劫难!
某一天,来了八九个人,似乎各兵种的都由。其中有一个青年格外的积极,抢着给我说教,搬出了许多条文,累得满头大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你不要鬼鬼崇崇,混不过去了。&他一直在重复这句话,我纠正他不要说&祟祟&,而应说&祟祟&。他回答说:&反正都一样: &还把&班门弄斧\'说成&搬门弄术&,再加上-些形象解释,我又给他纠正。真让人哭笑不得。
再一天来的似乎是一批老手,也很精灵狡猾:-进门就要我站起来朗读墙上贴的各种语录条幅,大都是从&红宝书&上摘下来的,诸如& 反对主观主义,反对教义土义,反对不实事求是、不忠诚老实、装腔作势。盛气决人、自欺欺人\'之类。我倒是很有欢庆,而逢读到&反对不实事求是&之类的语句时、故意提高声音,多读几通。其中一人总算听出了味道。要求我说明&是给自己读,还是给我们读,让我们听?&我说:&这是毛主席的话,谁都得听,谁听谁不听,我怎么知道?&他说:& 你的读法是给我们听的,&我说:&那只好大家都听吧。&此后,他们把那些语录全去掉了。这不足以说明那时叫得震天响的&无产阶级专政 &是什么货色吗?
接着,他们又向我宣布:在任何情况下,交代问题时,都不能涉及毛泽东、周恩怼⒘直肴说拿趾褪虑椋思柑欤诖沃厣暾庖辉蚴保直涑闪肆鋈耍醇由狭丝瞪⒔嗪统虏铩2⑶仪康鳎盒旁谔富爸胁唤霾荒苌孀闼堑氖拢词挂惶崴堑拿郑际欠缸铩N曳次室痪洌&如果你们提出有关他们的问题时,我如何答复?&他们说: &不会问你这类问题的。&此后,全国十亿人口中,只有六个人受到保护,似乎进入了保险库。实际上在以后的谈话中,又不能不涉及到这六个人中的某一个。遇此情况,我只好用&他&或&她&来代称,显然这就很难使他们听得明白,而他们又不敢迫问具体人的姓名。这种愚蠢的状态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期,渐渐地也就不再来纠缠了。
这期间,来了一批十八九、二十来岁的女孩子,她们的长相一个赛一个,然而她们那种无赖劲,更是一个赛一个。她们那被扭曲了的灵魂,在这里得到允分的表演。她们出言不逊,任意侮辱人,张才舞爪,推推囊囊。够了,我想起就痛心,我们文明古国,到底造就了一代什么& 新人&?I
还要说到一个文化水平极低,不懂事理.又讲不清任何一个问题的人。他一坐下来就抠脚搔痒,态度十分蛮横,却分不清是非好歹。唯有他带来的一个北大的学生,是他的依托和帮手。我前前后后被他们纠缠了十个多月,仅仅为了这样一件事:
1949年末.我陪同毛主席访苏时,斯大林建议出版(毛泽东选集),毛主席则要求他派一位哲学家来帮忙,斯大林就指派了尤金。我因翻译<毛选&,同尤金来注较多。这是人所共知的事,而且我也反复交代过了。由于毛主席的亲自安排,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曾陪同尤金遍游中华大地,并请尤金讲学。这些也是组织了解的,我也反复交代过的。唯有尤金在苏联大使馆请陆定一、林莉、张锡佑和我参加了一次午餐,这样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被我遗忘了。二个多月的车轮战、罚站、折磨,就是为了这件老。他们的提问,只是些我交代陆定一同苏联的关系、同苏联大使馆的关系。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关系&没有交代,请他们提示一下,他们不肯,只骂我&不老实&,施加了种种的折磨。 -天饭后休息时,我脑海中突然浮现出尤金请我们到苏联大使馆参加午餐一事,那是他表示感谢帮助过他工作的几位中国同志的。于是我立即找他们说了这件事,他们似乎满足了。我却不想就此罢休!我说:&你们只知道同我在无足轻重的小事情上纠缠,却不愿了解实质性的问题。&他们装腔作势说他们什么都知道。我说:&不管你们知道还是不知道,我得告诉你们:尤金是毛主席的客人,是毛主席亲自和斯大林商定后,邀请尤金来中国的。陆定-是以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身份陪同尤金周游全国的,也是毛主席安排的。尤金旅游和讲学回来以后,立即给主席写了一封汇报信,主席看了表示满意,而对陆定一回来一声不吭主席有意见。这些事你们都知道吗?怎么能怀疑我隐瞒陆定一同尤金的关系而加罪于我?!真是莫须有&
1969年秋,秦城监秋的医生忽然断言我患有恶性肿瘤,把我送到复兴医院,要求给我施行&手术&。医院接诊的是外科主任大夫(后升任院长)钱之达同志。他诊断不是肿瘤,没有必要动手术。但监狱来的人不答应,不但要求立即动手术.而旦要在手术后立即把我带回监狱去。钱大夫却本着高尚的医德和责任感,拒绝了他们的无理要求,绝不草率从事。开是他们用习惯了的&专政&态度同大夫大吵大闹了一个多小时,钱大夫是寸步不让、决不苟且,毫不动摇!那些人只好押着我转回秦城。过了两三天,又送找到医院医治。钱大夫显然意识到了,也就特别的小心谨慎。我被隔离在单人房间,用了一周的时间做各种检查和难备工作,然后顺利地做完了手术。虽然无缘无故地把我左胸脯的肉割去了半斤多,但由于钱大大的精心安排和防范.总算没有发生意外.我又一次活了下来!术后-日,便把我接回监狱。
我的身体在康复期间,食欲特别好,我自己暗暗庆幸。但不料祸从天降!一天午饭后几个小时,我开始腹部疼痛,并不断加剧,至晚则上吐下泻,头昏脑胀,不省人事。由于返回岗位的原监狱管型人员的救助,我又一次脱险。后来知道这是一次食物中毒,共有七八人,我因食欲好,是中毒最重的三个人中之一。但是怎样造成食物中毒,却始终不知。
我在监狱里好像是孤身奋斗,实际上有着许多看不见的援救之手!
直到1972年初,毛主席下了一道指示,约法三章: 一让犯人吃饱、二让犯人睡足:三没有病症时才可以审讯。并责成监狱管理人员不仅耍遵照执行,还要原原本本地向犯人传达、征求犯人意见。从此才停止了种种虐待,伙食也有所改善,由全部粗粮变成全部细粮。我已经吃惯了窝窝头,觉得馒头没有窝窝头香,可是讨耍窝窝头,也是没有。
&保险&不保 魔临末日
&保险库&里的人也并不那么保险。大约1970年初,突然来了几个人,很神秘地要我揭发、交待陈伯达的问题。讲了很多,好言相劝。我问他们:&你们这是什么意思?讲的是真话过是想捉弄我?希望你们的态度放老实点。我已经被捉弄糊涂了,被折腾够了。前不久,你们还划了个&钢铁图&,里面的六个人中就有陈伯达,是受到绝对保护的,连名字都不能提及,而今天却要我在太岁头上动土?&他们则苦苦劝说,捶胸发誓说他们不是耍圈套,而是有上级和毛主席、党中央的机密紧急指示。今天来,也还只是秘密调查、收集材料,在这里说的也还不能公开等等。我表示耍考虑两天,待弄清问题再说,他们只好答应。我又问: &那么那个钢铁图还存在不存在?&他们马上回答:&没有什么钢铁图 &我又说:&你们曾经宣布的六个人不许触及.只要触及其中任何-个人就要犯罪,还有效没有?这个罪我是犯不起的!&这使他们大伤脑筋。于是他们再次来时,把毛主席亲笔题词的复制件拿来给我看。那是几个大字和几行小字,原文已记不清了,大意是说陈伯达大闹庐山,几乎要翻天覆地.不待庐山会议开完,便不辞而去,不如所向何方。看了毛主席的题词,我答应写有关陈伯达的材料。他们嘱咐我:写好后,不可交给任何人转,只要告诉公务人员,他们自己就会来取。
我当然实事求是地,据我所知,一是一,二是二地写了材料,但他们还是不断纠缠,反复&启发& 我、提示我,授意我添油加酷。我说不能画蛇添足、弄虚作假。他们却说:&你只管写,不要你负责。&我反驳说:&这是什么话?!我写的材料,却不要我自己负责,那还行?既然你们认为可以弄虚作假、胡说乱写,那你们自己按需要去编造岂不更好么?我后来才知道,他们正是利用了我的交代,而后加以歪曲,并编造了 &中央文件&,其中说:&\'苏修特务师哲检举陈伯达......&背后结盟加上罪名,以加重陈伯达的罪过。何其卑鄙!实际公开批判陈伯达,是我写了陈伯达材料的六七个月之后开始的。
免死狐悲,唇亡齿寒。陈伯达被揪出后,可以想见康生那种危哉殆哉、战战兢兢、不可终日的鬼样了--他同陈们达的拉扯关系是水远也交代不清楚的?但是,&吾发之,吾能收之&。康生只不过大大地虚惊一场,而真正的后台却是林彪。
林彪摔死,我当时当然不会知道,但很快就来人了,来的还是那位操着胶东腔调的干部,另有二人相配。这位干部绝对没有了以往的神气,而是-副哭丧相,看到他,我也就猜出个八九。他要我揭发交代林彪的问题、我同林彪的关系等。我很乐意谈,于是兴致勃勃、滔滔不绝地向他们讲起了林彪三次访问莫斯科的情形、同高岗的会面和交谈的情形,又如何经过高岗给毛主席捎信等等。我谈得很起劲,这位干部却不耐烦,他心不在焉,听不下去,终于阻止了我的话。我十分惊讶!而他竞以十分沮丧和难过的表情说:&人都粉身碎骨了,还谈他什么?&看来,大戏快到终场了。
戏太大,尾声就不会太小。北京外语学院(前身是俄专)一批二十岁上下的青年学生也来&提审&我。我离开该校已二十多年,与他们何干? 他们由记个教师模样的人带领。从上午就来到了。监狱的工作人员对他们说:&快吃中饭了,不能提审。&饭后又说:&要放风,不能提审。 &可怜的娃娃们就这样等着。放风后,工作人员对我说:&有几个青年学生要找你谈话,但不着急,等一会儿再去。&最后带我去了,屋子里挤满了人。他们开口就宣布&纪律&,老一套,宣布完了说:&如果违反了这三条纪律,就要打烂你的狗头!&我问:&谁的头?&他们紧张了一下,其小一个说:&你的头。&我又问:&我的头怎么会长在狗身上 \'&他们无可奈何,在这里他们不敢动武。接着提了几个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 &为什么你要建议成立俄语专修馆?& 、&为什么你要把俄专的数字、图书馆、食堂等处的名称都用俄文写成?& &你任用过你的私人吗?& &张锡传是怎样到俄专的?&我说:你们太辛苦了,&看守人员在门旁听着,也忍不住鄙夷地一笑,并催促他们快点收场。其实他们并无意弄清任何问题,不过出于好奇,找借口来欣赏这座&高级监狱 &而已。
前后审问过我的,不下百十入。但真正有自己头脑的,充其量不过一二人,其余全是稀里糊涂给人当棍子。
自1972年起,由一个青年战士专管二楼犯人,他二十多岁,一口胶东话,有时同我聊聊,问长问短,表示对我很关心,我也表示愿意帮他做点什么;于是他告诉我,他们学刁抓得很紧,但常遇到困难,特别是有些引用马克思、列宁的语句,既不知道它的出处,又不能理解其意,像此类问题。想来问问我是否可以?我十分高兴地满口答应:&只要我知道的,全都告诉你。&从此,他就有时带着问题来找我进行探讨。研究过二四次以后,我问他还有什么需要我帮他做的事情?他说图书馆的<马克思思格斯全集>全都需要包上书皮,以防损坏,问我愿不愿意做这件事&我的答复当然是肯定的。于是他把书和必要的工具陆续送来。我花了几天功夫,把两套<马克思思格斯全集>几乎全部包上了书皮,并题写了书名。他很满意,对我也更关心了。有时我想吃青椒、葱、辣椒、盐、蒜、酱油、醋等等.他都想方设法给我弄来。有时厨房没有辣椒,他竞到狱外向群众讨要点来。我很感谢他,我们之间似乎形成了一种可贵的、真诚的友谊。而我的身体也迅速肥胖起来。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5月的一个早晨,这位青年招呼我收拾行李。我知道这是要释放我,因为在押犯人已有许多人出去了,每天都有成批的人出狱。他让我把公物全部整理出来,只带居于我私人的。那条大棉被,是监狱发的,但归个人所有了,他极力劝我带上,并动手替我包装。但是我想的是:&把一切屈辱的痕迹都留在这里&。所以坚决不要。现在想起来,也许他是对的,我没有留下半点铁窗的&纪念品&,他把我的行李搬到监狱的大门口,装上汽车,然后站在高台尚: ......我们的友谊再深,此时此地,他却不能挽留,他表情凄惨,心事重重地向我再三招手送别;我也同样,几次回首......
在监狱的十多年中.我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拿我自己的俄义版&列宁全集>对照狱中图书馆的中文版&列宁全集>.从头至尾校对一遍,开始时,由于管理人员不懂俄文、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所以不许我看。当我向他们解释这是&列宁全集>时,他们便没有理由禁止我了。我发现第28卷以后的各卷误译甚多,有的我批在书上,有的作了记录,出狱后把我的意见告诉了编译局。
重见天日 痈定思痛
十几年与世隔绝,社会和家庭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人们的观念和语言的变化。我只要开口讲话,孩子们就笑我,别人也瞪着奇异的目光看我,好像我是个外星人,是个怪物.这是后话。
再说我虽从监狱出来了,但&案子&并没有结束,而是移交给公安部第一专案组继续审理结案。我呢?依旧被流放到陕西扶风,在扶风又待了三年。
在这三年中,给我的案子做了六次结论: 主要是办案人员想不开,总不愿意这十几年白辛苦了,于是纠缠不休,然而谎言终归不能成为事实。他们起草的&结论&上的胡言乱语一个一个被否定之后,只剩下一个费德林,死抓住他不放,把他作入我&里通外国,勾结苏修特务& 的罪证,坚持要写在结论中(费德林和尤金-样是毛主席的客人,也是向我一起翻译<毛泽东选集>的。有一次他们为此事来到扶风时,正值我的小女儿明朗来看望我,她在旁插话说:&难道给毛主席做事也有罪吗 \'!&他们顿时哑口无言,无所措手足。啊!这就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小青年!以后他们来谈话,就不许我的女儿在场,无理者却有权!
直到1979年初,一切专案统统移交中央组织部,在胡耀邦同志主持下,很快给我了最后的结论--&经13年审查,没问题&。
没问题I没问题为什么要扣我关在监狱,泡了13年?加上前后流放的5年,共18年。18年,人生能有几个能有几个18年?!对我个人来说,蹲监狱或许还是一种幸运,如果在外面,恐怕早就落得跟王世英- 样被活活打死的结果,可是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和我们相同或相近命运的人还有多少?数得清吗?而实际上真正暗藏在我们心腹之中的奸人、反革命分子,只有康生、江青之类极少数几个人,怎么就会弄得人妖颠倒如此程度?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几乎朝朝代代都不乏忠奸颠倒的事例,而&文革\'则在中国历史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一切悲剧的根源是什么?如果不真正汲取教训、还可能踏上蹈撤!
阅读:293 次}
我要回帖
更多关于 马上有钱 的文章
更多推荐
- ·邹城顾姓起源和来历是不是顾时后人?
- ·国家民委关于推进武陵山片区创建全国民族团结示范市内容进步示范区的实施意见组织实施
- ·北京东直门中医院李忠学人物简介
- ·正品lv女包价格一览包应该在哪里购买?
- ·kdj指标怎么设置比较精准失灵了怎么办?
- ·天空之城数字简谱谱怎么转换为像手机上显示的谱
- ·六房买的公爵号,绑定了自己手机,他能qq怎么不被申诉回去去吗?
- ·诺基亚n1 屏幕闪烁a1000打开后一直闪烁
- ·vivox5 max智能手机电池待机多长时间
- ·plmn选择偏好设置怎么弄
- ·2015现在买什么手机好?或者说有什么待出诺基亚新机型2015大伙感觉比较好的呢?
- ·vivoxshot参数侧面按键更换多少钱?
- ·我的苹果6里面的图片没有上传,别人怎么情侣空间别人能看到吗
- ·信时空卡号没有来电显示会怎么样
- ·你越狱能解id锁吗?II
- ·东莞扫黄抓现场照片被抓手机能打通吗?
- ·平安橙子银行官网交易密码找回
- ·只要有钱入帐我愿意马上进监狱生活有钱都可以,谁能帮我忙
- ·如何清除中信银行信用卡提额逾期不良记录
- ·失业了!很长时间为方舟生存进化配置而烦恼,想了很久了,准备去抢富人,不折手段!
- ·秒赚广告能赚钱最快的方法吗?感觉没有意思!
- ·小明在做一道减法题时会计题
- ·奥施娜可以做怎样做机票代理商商吗?
- ·我在他行有两张中行信用卡如何申请,不影响中行申请中行信用卡如何申请吧!
- ·步步高97增额保险理赔,现患尿毒症能理赔吗
- ·薛氏三八丽华快餐加盟费费多少钱
- ·农行信用卡积分怎么算板块积分
- ·建行信用卡还款查询约定还款生效时间问题
- ·我借别人空的银行卡借给别人用,但那个人出意外死了
- ·两年前在工商银行忘记u盾密码透支了700元,忘记还现在要还多少
- ·我能用鑫上海智诚科技有限公司这个名来审请公司
- ·atm机天津零晨画室时候可以转帐吗